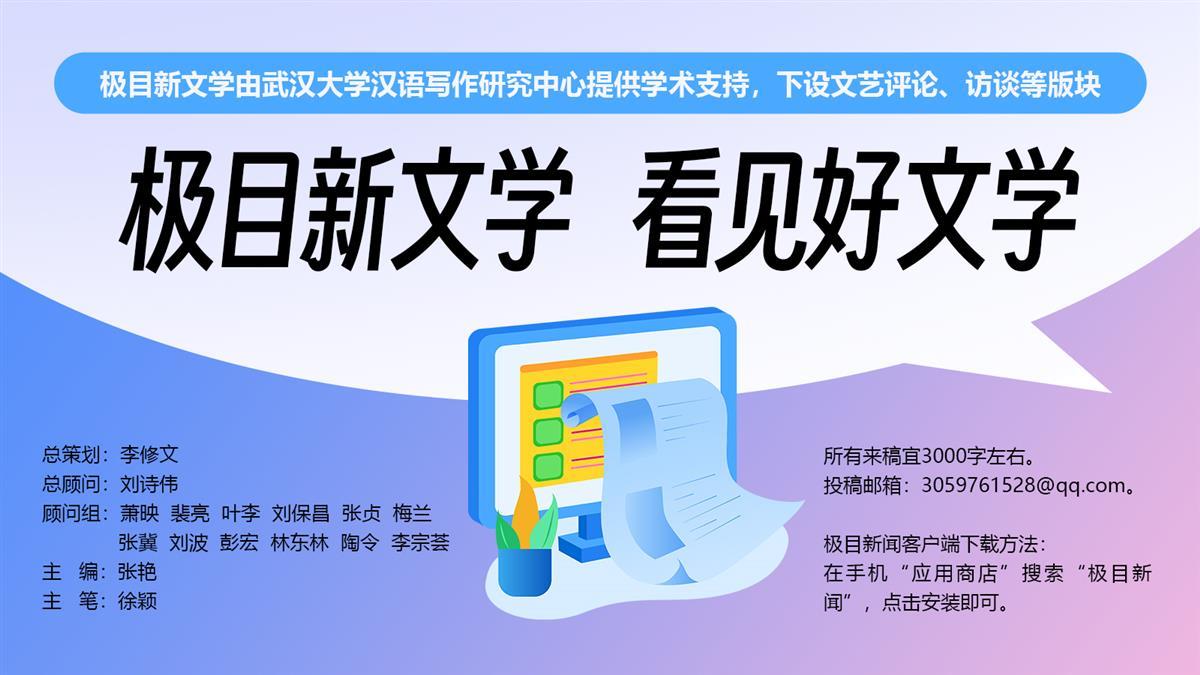李修文最新小说集《夜雨寄北》包含四篇具有当代都市传奇色彩的故事,以虚实相生的奇诡叙事,展开世情描摹和人性观照,在承接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影视媒介的技艺手法,实现了当代小说创作美学的革新和拓展。
楚巫气韵与志怪传统的当代迁化
如作者此前的众多作品一样,小说集《夜雨寄北》的各篇都追求“美学意义上的真实”。这种创作理念的形成,与“作为一个楚人的后裔”“期待那种荆楚风格的复活”的自觉意识有关,也与作者对蒲松龄式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遭遇到的奇迹”的阅读偏好有关(以上引文摘引《对话湖北省作协主席、鲁奖得主李修文:有接续楚人楚风的艺术志向,做“美学上的项羽”》)。因此,读者不难发现,该小说集里的叙事空间都略显奇诡:其中,《夜雨寄北》开始于废弃的动物园,荒草丛生,破败不堪;《木棉与鲇鱼》设定在台风来袭前的海岛,充满未知的危险;《灵骨塔》发生在夜晚寺庙的骨灰塔,风雨交加,静谧阴森;《记一次春游》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半途停工的电影小镇,曾经繁华一时,如今人迹罕至,“入夜之后”,影影绰绰的建筑仿佛“巨大坟墓”。按照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这些场所“就像是《聊斋志异》里那些随时都会有孤魂野鬼奔跑出来的所在”。《夜雨寄北》中猴子“小丹东”能开口说话、背诗,马豆芽两次遇见自己,《木棉与鲇鱼》中有死而复生的小田和杀不死的老欧,《灵骨塔》中突然上锁的塔门和黑暗里传来的女子歌声,《记一次春游》中“我”在录像厅穿越时空看到过去的自己,在防空洞与想象中的刘大伟进行彩弹对战等,这些深具楚巫气韵和志怪色彩的故事元素,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还传神地呈现了小说主人公紧张、癫狂的精神状态。
这也说明,尽管该小说集中的志怪笔墨都能在古典文学中找到其渊源,但古人的志怪、传奇书写,根植于其秉持的心灵真实与神秘主义的认知观——蒲松龄们以虔诚的民间信仰为根基,笃信或主观上愿意相信狐鬼妖怪游荡于世间。而李修文笔下的超自然书写,是作为小说的方法和技术而存在的,用于剖析当代人复杂的心理状态,赋予了作品深邃、荒诞、狂放的美学气质,引导读者生发出对真实与虚幻、世界与历史、自然与生命的全新思考。
说书传统与话本语言的继承改造
从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上看,作品对古典说书传统和话本语言,进行了有意识的学习和改造。
首先,四篇小说都存在一个类同于说书人的叙事者,其中《夜雨寄北》《灵骨塔》《记一次春游》采用第一人称,表面上看是一种有限制的内聚焦叙事,但作家通过种种设计,对“我”的限制视角进行补充,达到了传统说书所具有的全知叙事效果。在《夜雨寄北》中,“我”与“小丹东”数度聚合,在分离期间,作家通过安排其他人物对“小丹东”的经历进行旁观说明,以及“我”能够通过气味感知“小丹东”的所在等奇幻情节,填充关于“小丹东”的叙事空白。《灵骨塔》中,“我”“郭小渝”“悟真和尚”轮流叙事,相互补充、矫正对方对于“林平之”的片面认知,使读者在交错视角的叙述中,得以拼凑出完整的“林平之”的人生故事和内心世界。《记一次春游》中的李家玉和“我”先后醉酒、酒后大吐真言的桥段,借此透露二人真实底色和故事全貌。《木棉与鲇鱼》一开始就使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而承担讲述功能的角色依然非常明显,即女主人公于慧,因为小说结尾的情节表明前文所述一切,都是于慧因头痛而产生的幻想。可见,作家通过调用多种叙事手段,使得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的叙事,都具有兼容性和弹性,实现了“一人主叙,众声补缀”的改造。
其次,四篇小说都将所叙之事设定为一种过去完成的历史时态,进行回溯性的线性叙事,借助“我还记得”“说起……”“好吧,还是说回……”“说来也巧”“那一回”“再看……”等话语,营造出一个具有即时交流性和现场互动性的隐性说书场,把整个文本变成讲述者面向预设听众发言的内容记录,具有了传统话本的功能和特色;同时,这些语言发挥了叙事干预作用,或是对故事中的人和事进行解释、评论和概括,进一步在有限制的第一人称基础上进行补叙;或是对叙事节奏和时间进行控制、调配和重组,在线性的叙事主线中,穿插进行倒叙、夹叙、插叙,甚至平叙,打破了传统话本中单一线性叙事的单调,增强了故事的层次感和悬念感。

最后,传统话本语言表现出“雅俗共赏”的美学特征,其“俗”主要体现为叙事的口语化,“雅”则常常表现为标目/回目的文辞堆砌和在楔子/头回、正文、篇尾部分使用诗、赋、赞之类。相较而言,话本语言的“雅”有更加公式化的程序,经过千年传承,已略显僵化陈旧。该小说集在叙事部分继承了话本语言的优势,娓娓道来,平白易懂,故事人物对话直截了当,穿插着脏话俚语,增添了文本的市井气息;对“雅”的表现路径,则进行了大胆的多元化改造:《夜雨寄北》中对李商隐、李煜等人诗作的援引,《木棉与鲇鱼》中对宗教、气象知识的讲述,《灵骨塔》中对金庸小说人物的化用,《记一次春游》中对“我”和李家玉书面通信内容的摘录,都旨在提纯文气。最终,在口语化叙事的传统话本土壤里,突破了形式层面简单的文白拼贴,嫁接生长出属于当代小说的文白结合、散中有韵的雅俗新质。
文学文本与影视艺术的跨界交融
李修文是有着强烈的文体实践意识和明确的文体实验主张的作家,他在创作中打破传统散文的文体边界,融合小说的叙事技巧、诗歌的抒情特质和戏剧的冲突元素,以极具画面感与故事性的表达效果,改写了当代散文的风貌。这种积极借鉴其他文类技巧的创作偏好,也体现在该小说集中。只不过小说所散发的体类交融的创新魅力,主要得益于对影视手法的吸收。比如,运用类似蒙太奇的叙事手法,将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情节片段组合拼接,创造出独特的叙事效果和情感张力。《夜雨寄北》中,马豆芽与自我有两次狭路相逢,一次是她带着“小丹东”离开剧组时,看见一个又一个自己相向跑来,义无反顾地冲进拍摄现场,折射出马豆芽对演艺事业的不舍;另一次发生在文末,她在镜中看见不同人生阶段的自己的影像,隐喻她回首半生,终于彻悟,走出自我束缚的藩篱。这些时空的交叉叙述,加深了读者对人物心路历程和命运发展的理解。《木棉与鲇鱼》里,于慧的往昔记忆与现实经历不断交织,形成对比和呼应,既交代了故事的前因后果,也凸显了于慧内心情感世界的复杂。

小说中频繁且自然地进行场景切换,如同电影镜头快速转场。《夜雨寄北》里,马豆芽的生活轨迹从通州的废弃动物园,到“最可爱”大歌厅,到密云剧组,到朝阳公园附近的高级公寓,到马妃店,到海边,到三亚,到老家,再到仙童寺,终于城中村。《记一次春游》也如是,从城市边缘的高速路,切换到右岸电影小镇的各个角落,复杂多变的场景如同跳跃的镜头画面,加强了故事的节奏感与紧张感。
对关键细节进行生动摹写,效果类同于电影的特写镜头,聚焦于具有重要意义的瞬间,节奏放慢,镜头推近。《灵骨塔》中,多方人马争夺骨灰盒,各路人物在紧张时刻的表情和动作,被特写放大:“悟真的脸上,仍然被愤懑和委屈充满”“郭小渝的脸上,瞬时就变了颜色”;在《记一次春游》中,李家玉在特殊时刻的情感变化被精准捕捉:“嘿嘿笑起来,身体却是一软,径直倒在了我身上。”这些描写精微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波动,提升了文本的感染力。
综上,《小说集夜雨寄北》主要呈现出三重创造性转化:将楚地巫风和志怪传奇的传统转化为剖析精神困境和社会症候的叙事装置;通过叙事改造和语言革新,激活古典说书文学的当代生命力;将蒙太奇、特写镜头等影视技法熔铸为文学修辞,在时空拼贴与感官聚焦中,拓展小说的叙事维度。
此外,小说中保有多层次的艺术蕴藉。例如,《夜雨寄北》中反复出现的李商隐诗句,是否在文采点缀功能之外,还蕴含“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木棉与鲇鱼》中以不同品类出现的“鱼”的意象,指向何种关乎欲望的隐喻?《灵骨塔》中从未正面出场的“林平之”,其人生与金庸笔下的林平之有着诸多重合之处,身兼受害者和加害者双重身份,这一人物设置是否旨在说明“他人即地狱”的哲思?《记一次春游》中对当代名利场乱象的摹写,又是否是一种“微而显,志而晦”史家笔意?凡此种种,都是等待读者探入其中感受细琢的意味。
(陈澜,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湖北省作协第三届签约评论家。刘金悦,江汉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