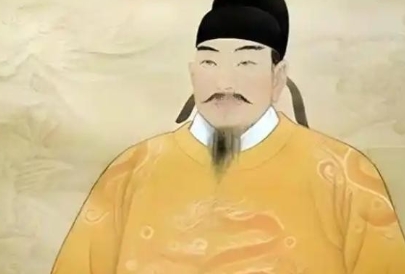649年,李世民自觉时日不多,把太子李治叫来:“朕走后,有一人,朕恐怕你将来会管不住他。所以,你现在传朕令,贬他离京。半年后,你再召他入京。”李治懵了,此人是谁?李世民说:“他是李勣,但如果他不从令,你就把他砍了!”
李勣(原名徐世勣)的人生堪称隋唐传奇,出身山东豪族的他,17岁投奔瓦岗军,以智取黎阳仓、歼灭宇文化及等战绩崭露头角。
归唐后,他助李世民扫平窦建德、王世充,又大破突厥、薛延陀,成为《旧唐书》载“出将入相,功勋卓著”的栋梁之材,李世民曾剪下胡须为其配药,更在宴会上解衣覆其身,称“朕以太子托卿”。如此殊荣背后,却暗藏君臣间的微妙张力。
玄武门之变时,手握重兵的李勣选择中立;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中,他亦不置一词,这种“只效忠李唐,不站队任何人”的姿态,既保全性命,也让李世民始终留着一分忌惮。
李世民临终前三个月突然发难,实为精密算计,叠州(今甘肃迭部)距长安仅四日马程,既非边陲绝地,又足够远离权力中心,这道看似贬谪的任命,实为三重考验:
政治站队:李勣时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掌控东宫六率精锐,贬其出京既能削权,又可观察山东军系动向;
年龄博弈:59岁的李勣比辅政大臣长孙无忌年轻6岁,正值将领黄金期。李世民曾暗忖:“若使勣辅政十年,治儿可安坐朝堂”;
人性实验:据《资治通鉴》载,李勣接诏后“即日离京,家财封存府库”,甚至绕道昭陵跪拜,以行动宣示忠诚。
这场测试的凶险程度,从李世民对李治的叮嘱可见一斑。若李勣稍有犹豫,等候他的将是刀斧而非官印,而李勣的果决反应,不仅保住性命,更为后续崛起埋下伏笔——赴任53天便击退吐蕃袭扰,用战功证明价值。
永徽元年(650年)正月初一,李治改元大赦,同时恢复李勣“开府仪同三司”待遇,这番操作堪称帝王术典范:既遵循父亲遗命,又通过吉日施恩彰显仁德,此后十余年,李勣以尚书左仆射之职成军方支柱,却主动辞去实权,仅以虚衔“同中书门下三品”参政,成功避开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的党争。
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立后风波掀起巨浪,当长孙无忌等人以死相谏时,李勣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既成全李治心意,又避免卷入政治漩涡,这种“知进退、明得失”的智慧,让他在武后掌权后仍得善终,而反对派重臣多遭清洗。
总章元年(668年),74岁的李勣完成人生最后一战——率军攻灭高句丽,实现李世民未竟之志,《新唐书》记载其“俘王族二百人,收一百七十六城”,唐高宗亲制《大唐平辽碑》以彰其功,次年病逝时,李治辍朝七日,追赠太尉,谥号“贞武”,极尽哀荣。
然而历史总爱开玩笑,684年徐敬业反武失败,武则天下令剖棺毁尸,这位三朝元老竟遭“斫棺焚骨”之辱,直至神龙政变后,唐中宗才重修其墓,一代名将的身后遭遇,恰似大唐盛世转向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