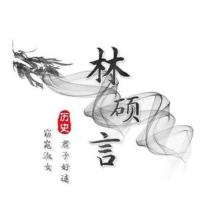1959年,陈长捷出狱后,傅作义在北京西单请他吃饭,陈长捷故意迟到,大摇大摆地走进去,瞪着眼撇着嘴直言:“要是放在以前,今天我绝对不会前来!”
陈长捷和傅作义的交集,可以追溯到保定军官学校时期。那时的他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是军中最有前途的青年才俊之一。
傅作义为人刚毅稳重,颇具谋略;而陈长捷则豪爽果敢,行事雷厉风行。两人因性格互补,很快结为莫逆。
毕业后,他们不约而同投奔阎锡山,成为晋系军阀的重要骨干。
在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均屡立战功,傅作义驰骋绥远战场,击退日军有功,陈长捷则以铁血军纪整饬部队,威震三晋。
阎锡山虽表面倚重二人,内心却深忌这两个羽翼渐丰的“猛虎”,担心其威胁己权,终日防范。久而久之,陈、傅二人逐渐对晋系心生不满,选择各自分道扬镳。
1949年初,国共内战已进入尾声,解放军势如破竹,华北战局日趋紧张。
此时傅作义为北平“剿总”司令,名义上统领华北各地守军,实则已心生去意。天津作为华北门户,是傅作义手中最关键的一张牌,其防务由陈长捷担任。
战前,杜建时、林伟俦、刘云瀚等人都看清形势,纷纷劝陈长捷撤兵保命。
但陈长捷坚持己见,怒吼道:“如天津防守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你们若不为傅总司令、蒋委员长负责,我只有自杀!”
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忠肝义胆。但他未曾想到,傅作义此时已经暗中与中共接触,意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北平,留名史册。
1949年1月15日天津战役骤然打响。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天津,猛烈炮火轰击之下,整座城市仿佛在颤抖。
陈长捷身着整齐的将军制服,站在司令部的观测窗前,神情凝重。他早已料到这一战是生死存亡,却没想到傅作义竟真的“袖手旁观”,没有任何增援动作。
他心中燃起的不只是愤怒,还有一种撕裂的失望。
部下纷纷来报,东门失守,南门告急,电台联络频频中断。陈长捷沉默片刻,走到地图前重重一拳砸下:“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敌我力量悬殊,天津守军孤立无援,节节败退。城破之际,枪声渐息,烟尘未散,陈长捷踉跄走出指挥部。
他脸色苍白如纸,却挺直脊背,面对蜂拥而至的解放军战士,仍怒目而视,高声喊道:“我陈长捷,宁死不降!”话音未落,被战士当场制服。
这一刻,他没有选择饮弹自尽,也没有选择变节,只是默默地被押往功德林——那是专为国民党战犯设立的“再教育营”。
天津失守后,傅作义成功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成为新中国“和平起义”的象征人物,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水利部长,成为少数保有官职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
而陈长捷,却在功德林经历十年铁窗生涯。
1959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宽大处理战犯,陈长捷获释。消息传来,傅作义十分感慨,主动安排在北京西单请他吃饭,希望借此一聚,也表一表心意。
这顿饭成了两人多年情谊的一次“清算”。
陈长捷故意迟到,穿着一身老旧的中山装,大摇大摆走进包间,眼神锋利如刀。
他冷冷盯着傅作义,一字一句地说:“要是放在以前,今天我绝对不会前来!”
傅作义听后面露愧色,端起酒杯说:“老弟,当年之事,我有难言之隐……”陈长捷冷笑一声:“我看是难以启齿吧?”
那顿饭,气氛压抑如霜,杯酒未干,话已如寒冰。昔日同窗、战场兄弟,终因政治选择与命运捉弄,形同陌路。
陈长捷晚年生活拮据,靠政府接济度日。他一生忠诚于蒋介石,自认为是“国家栋梁”,却因战败沦为囚徒。
他曾对人说:“我若当初一走了之,也能像某些人一样当上部长,可我不愿苟且偷生!”
傅作义虽高位在身,但对陈长捷一事,始终心存愧疚。有人私下问他:“你为何不救陈将军?”他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当时救北平,是大局……至于老陈,我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