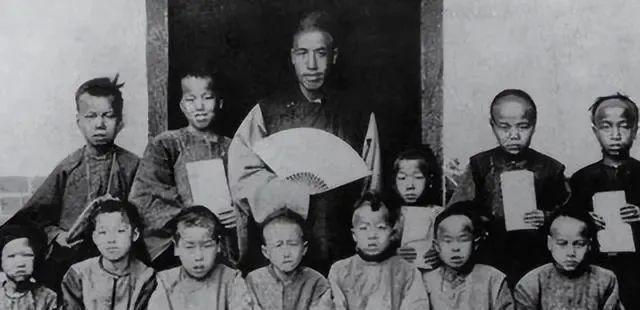1904年,通房丫李氏,站着侍奉丈夫与正妻长达33年。这日,她正在盛饭。谁知,管家突然冲进来高喊了一句,她手一歪,啪地一声碗摔落地面碎了一地。正妻刚打算开口斥责,丈夫却开怀大笑:“坐下,一同用膳!” 光绪三十年春寒料峭的早晨,湖南茶陵谭家大宅的后厨里飘着米粥香气。 三十三岁的李氏端着黄杨木托盘穿过游廊,青布鞋底踩着青砖地发出细碎声响。 这是她当通房丫鬟的第三十三个年头,日复一日伺候老爷夫人用早膳的差事早已刻进骨头里。 正厅八仙桌上摆着四碟八碗,李氏垂手立在檀木椅背后,眼睛盯着老爷碗里见底的粳米粥。 她手里攥着长柄木勺,指节被热气蒸得发白。 大夫人今早特意吩咐厨房熬的莲子羹在瓷盅里冒着热气,说是要给老爷败火,这话里有话的机锋,李氏这些年早就听惯了。 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管家连滚带爬冲进门槛,后脑勺的辫子都跑散了。 李氏手腕一抖,盛满热粥的青花瓷碗砸在地上,碎瓷片混着米汤溅上裙角。 大夫人柳眉倒竖正要发作,却见管家举着张盖着红印的文书,嗓门扯得能掀房梁:"中了!三少爷会试第七名!" 谭老爷手里的象牙筷当啷掉在桌上,这个素日里讲究"食不言寝不语"的举人老爷,此刻竟撩起袍子就往祠堂跑。 李氏望着满地狼藉怔在原地,膝盖还保持着半蹲收拾的姿势。 大夫人冷眼扫过她沾着米粒的裙摆,鼻子里哼出个气音,终究没说出那句憋了三十三年的"赔钱胚子"。 这事得从同治十年说起,那年谭家老太爷过世,十六岁的李氏从灶房丫头被抬了通房。 说是半个主子,实则连姨娘的名分都没挣上。 大夫人防她跟防贼似的,晨昏定省比正房太太的规矩还严。 偏生她肚子争气,连着生下三子一女,倒叫那些等着看笑话的碎嘴婆子闭了嘴。 可生了孩子也没见多金贵,月子里照样得站着伺候老爷用膳,孩子刚满月就被抱到正房教养。 三少爷延闿开蒙那年,李氏偷偷把攒了半年的体己钱塞给教书先生,求人家多照应些。 这事被大夫人知道,罚她在祠堂跪了整宿,膝盖落下毛病,如今阴雨天还隐隐作痛。 谭延闿确实是个读书种子,十二岁考中童生,十五岁中秀才,二十岁那年秋闱放榜,名字赫然写在桂榜前头。 谭家上下张灯结彩那日,李氏缩在后院浆洗衣裳,听着前头爆竹声震天响,手指在冷水里泡得通红。 转眼到了光绪二十九年春,京城传来废科举的消息。谭延闿连夜收拾书箱要赴日本留学,大夫人摔了茶盏说这是数典忘祖。 最后还是谭老爷拍板,把祖传的田产典当两处,凑足三百两雪花银。 李氏把贴身戴了二十年的银镯子褪下来,趁着送行的当口塞进儿子包袱。 谁承想转年开春,朝廷又开了恩科。谭延闿人在武昌两湖书院,接到消息时离考期只剩月余。 从武汉到北京两千多里旱路,寻常人要走四十天,他带着书童雇了骡车昼夜兼程。路上遇着劫道的,把盘缠抢去大半,硬是啃着硬馍馍撑到顺天府。 放榜那日,前门大街挤得水泄不通。谭延闿挤在人群里找自己名字,从巳时找到未时,终于在南墙根看见"谭延闿"三个字。 后来听同科的说,他的文章本该点进前五,主考官嫌他字迹太过张扬,生生压到第七。 这话传到谭老爷耳朵里,倒成了光耀门楣的喜事,毕竟整个湖南道,这科也就中了六个进士。 捷报传回谭府那日,灶房王妈看得真真儿的。 老爷攥着捷报在祖宗牌位前又哭又笑,大夫人扶着门框脸色发青,李氏蹲在地上捡碎瓷片的手直打颤。 最稀奇是老爷亲自搀起李氏,当着满屋子下人的面说:"往后用膳坐着吧。" 这话听着轻巧,落在深宅大院里可比圣旨还管用。次日早饭时辰,管家特意在八仙桌旁添了张圆凳。 李氏摸着滑溜溜的凳面,屁股挨着边沿虚坐了半刻钟。大夫人舀汤的银勺碰着碗沿叮当响,一顿饭吃得鸦雀无声。 日子流水似的过,三少爷外放做了翰林院编修,后来又当上湖南谘议局议长。 宣统三年武昌城头换了大旗,谭延闿跟着孙先生闹革命,竟成了国民政府的大员。 这些事李氏不懂,她只记得儿子每回省亲,总要先来后院给她磕头。 有回带来盒西洋糕点,说是叫什么"朱古力",她舍不得吃,藏在枕匣里化了形,倒招来一窝蚂蚁。 民国五年冬,李氏在睡梦里去了。灵堂设在谭家老宅正厅,三个儿子披麻戴孝摔盆打幡。 出殡那日,长沙城万人空巷,青石板上铺了三里长的纸钱。 抬棺的十六个杠夫清一色穿着新制呢子军装,那是谭延闿特意从广州调来的卫队。路祭的百姓交头接耳,都说没见过小妾的丧事这般风光。 说来也怪,自打李氏入了土,谭家大宅渐渐就败落了。 先是西厢房走了水,烧掉半拉院子;后来谭老爷中风瘫在床上,大小便都要人伺候。 大夫人信了洋教的姑子劝,把祖宗牌位送进教堂改的学堂,换回本烫金封皮的《圣经》。 唯有后厨那套缺了口的青花碗,王妈擦灶台时还常念叨:"当年三少爷中举,就是摔的这个花色。" 信息来源: 谭延闿生平-《民国人物传记》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湖南通史·近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