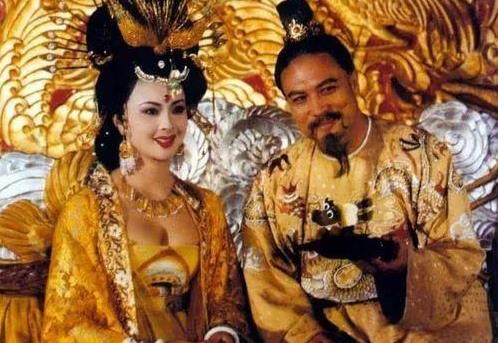公元762年5月,78岁的李隆基绝食三日,怒摔玉碗,咬牙切齿地说:“告诉三郎,我在黄泉路上等他。”两周不到,唐肃宗李亨也吐血而亡,父子之间的斗争,竟以这般悲怆收场。盛唐的气象,也彻底断裂了。 大明宫长生殿内,李隆基枯瘦如柴,布满老年斑的手指死死攥着青玉碗,指节泛白,似要将这碗捏碎。 自被尊为太上皇,幽居兴庆宫,李隆基的生活已与昔日的帝王尊荣天差地别,尤其是在高力士等人被赶走后,他身边的太监、宫女都是由李辅国指派的,名为照顾,实为眼线,晚年的李隆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内心很是苦闷。 当宦官颤抖着将李亨送来的汤药递过来时,李隆基凹陷的眼窝里骤然燃起骇人的火光:“这汤药,可是要送朕早日归西?当年马嵬坡,他与陈玄礼联手逼朕时,怎么不送碗毒药来?” 未等宦官回应,李隆基突然暴起,青玉碗砸向金砖地面:“告诉三郎!朕在黄泉路上等他!” 宦官扑通跪倒,声音带着哭腔:“太上皇息怒!陛下他日日为您祈福,盼着您龙体安康啊。” “祈福?” 李隆基猛地挥袖打翻案上《霓裳羽衣》曲谱,“他若真为朕祈福,为何要把朕的侍卫换成他的人?为何连高将军求见都要阻拦?” 李隆基抓起案头的书本狠狠摔在地上,气冲冲的说:“当年他在灵武称帝,撕碎朕最后一道勤王诏书时,可曾为朕祈福?” 记忆如潮水般回溯到多年前,东宫偏殿内,年轻的李亨跪坐在蒲团上,指尖反复摩挲着《礼记》的边角。 门外传来宦官的通报:“李林甫大人求见太子殿下。” 李亨深吸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说:“让他进来。” 宰相李林甫迈着方步踏入,手中把玩着白玉扳指:“太子殿下近日研读的《礼记》,可悟出‘君君臣臣’的道理?陛下听闻殿下与皇甫惟明将军过从甚密,特让臣来询问。” 李亨强压下心头惊怒,说:“李大人说笑了,我不过是与皇甫将军探讨兵法。” 话音未落,殿外突然传来瓷器碎裂声,是太子妃韦氏失手摔了茶盏。 李林甫意味深长地瞥了眼内室,躬身告退。当夜,韦氏便被以 “失德” 之名废黜,而李亨跪在大明宫前,额头磕出血痕,才换得李隆基一句 “下不为例”。 次日清晨,大明宫宣政殿。李隆基把玩着手中的玄铁令牌,目光扫过阶下噤若寒蝉的群臣:“太子近日行事乖张,诸位以为如何?” 李林甫心领神会,出列奏道:“太子与边将往来频繁,恐有不臣之心。陛下圣明,当早做决断。” 李隆基猛地将令牌砸在地上:“去东宫抄查,若有谋反证据,严惩不贷!” 禁军涌入东宫时,李亨看着被翻得一片狼藉的书房,终于明白,在父亲眼中,他永远是那个觊觎皇位的威胁。 安史之乱的烽烟中,让隐忍的李亨有了机会。 当逃亡队伍行至马嵬驿时发生兵变,陈玄礼带着几个将领跪在李隆基面前,眼神中却透着冷静:“陛下,杨国忠罪大恶极,已被诛杀,杨玉环惑乱君心,为了大唐社稷,还请下旨赐死。” 李隆基怒不可遏:“陈将军,你跟随朕四十年,如今也要反了?” 陈玄礼重重叩首,声音带着哭腔:“陛下,臣等别无他意,只是为了平息军心。太子殿下已应允收拢残部,北上平叛。” 李隆基见军队已不听他的,颓然的坐下,最终,杨玉环白绫悬于梨树下。 之后李亨带两千禁军北上,到了灵武后,被一众将领拥戴称帝,李隆基不得不接受成为“太上皇”的事实。 当李亨在灵武城头接过郭子仪递来的兵符时,一名黑衣密探悄然来报:“陛下,太上皇派人联络朔方节度使,欲夺回兵权。” 李亨冷笑出声:“回复太上皇,待收复长安,自当负荆请罪。” 兴庆宫内,李隆基望着勤政楼外空荡荡的街道,突然想起开元盛世时,自己在这里接见各国使臣的盛景。 “高力士,取朕的玉笛来。” 李隆基吹奏起《紫云回》,苍凉的笛声惊起檐下寒鸦。 第二日,李亨以 “惊扰百姓” 为由,封闭了兴庆宫所有临街门窗。 三日后,太极宫甘露殿。李亨咳着血批阅奏章,忽见一份密报:“太上皇暗中联络旧部,欲复位。” 李亨将奏章撕成碎片,高喊:“传李辅国!” 李辅国快步而入,眼中闪过一丝阴鸷:“陛下有何吩咐?” 李亨说:“去兴庆宫, 将太上皇迁居甘露殿。” 当夜,兴庆宫一片肃杀,李辅国带着禁军闯入,强行带走了李隆基。跟随李隆基数十年的高力士,被赶出了长安,流放于巫州,陈玄礼也被勒令致仕。至此,李隆基身边再无可靠之人,形同软禁。 宝应元年四月甲寅日(762年5月3日),李隆基在绝食三日后死去。 消息传来,在病榻上的李亨心情复杂。十三天后,张皇后欲诛杀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事泄后,反被手握禁军的李辅国、程元振反杀。 病重的李亨,眼睁睁看着李辅国当着他的面,将张皇后带走,当夜,李亨惊吓而死。 流放途中的高力士,在得知李隆基的死讯后,呕血而亡。 李隆基、李亨这对父子间跨越数十年的权力博弈,最终以两具冰冷的帝王尸身,为辉煌的盛唐画上了血色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