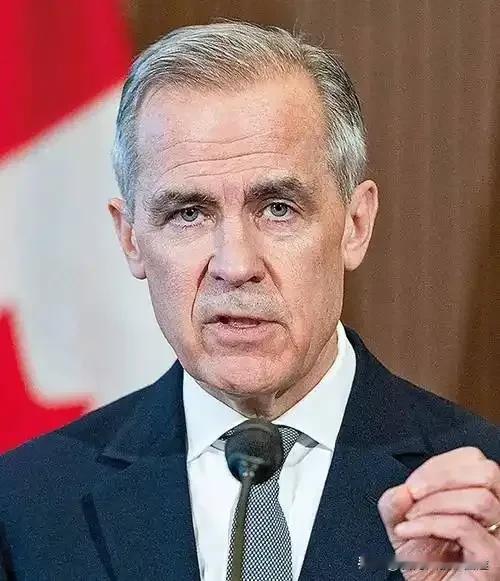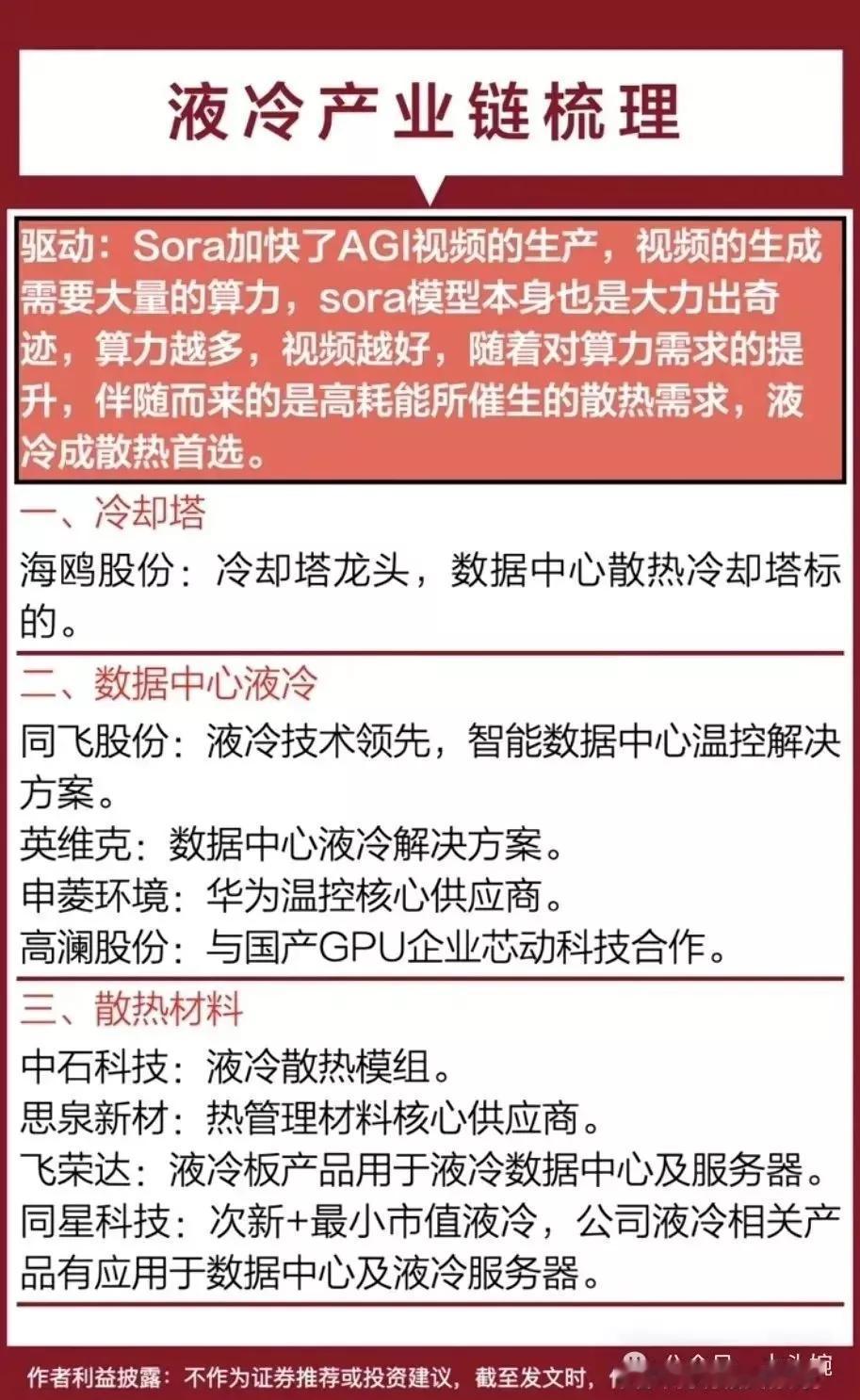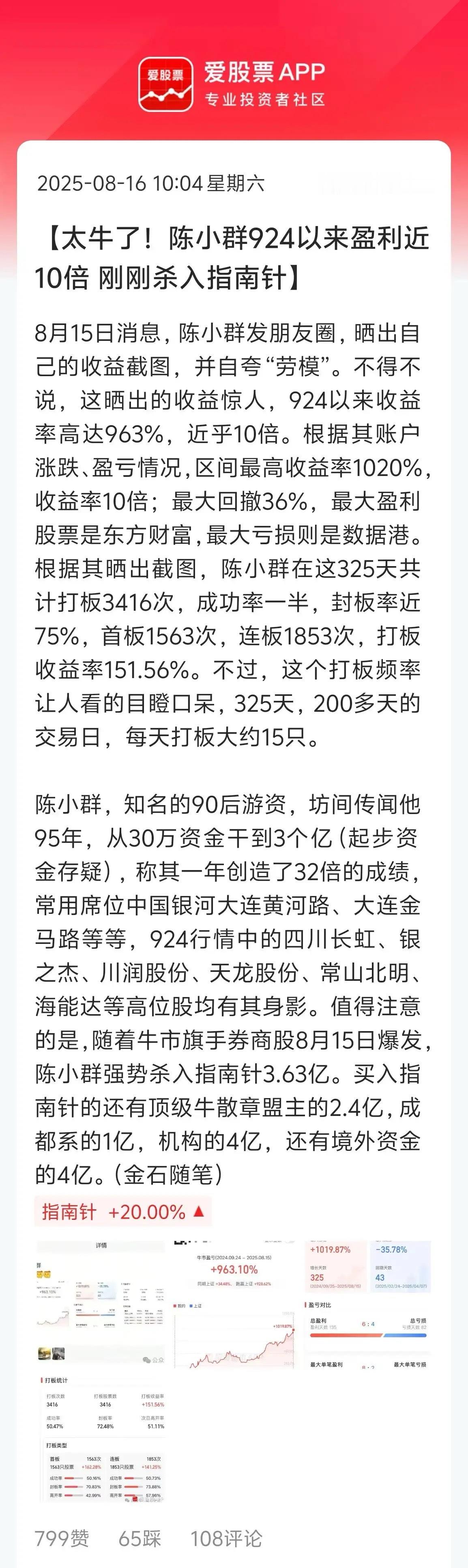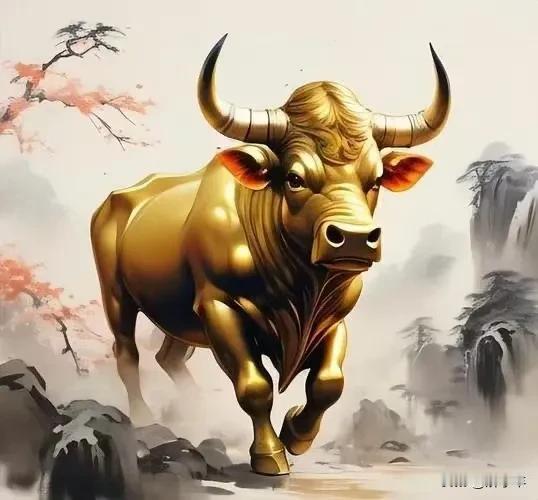一年狂赚上亿外汇,3元一瓶的风油精,靠“拿捏”非洲人逆袭。 1976年,风油精一上市,立马卖疯了,短短两年,年销量冲到800万瓶,十年后更是飙到1700万瓶,成了止痒药里的“国民明星”。可国内市场没热多久,上海家化的六神花露水冒了出来,靠着更温和的味道和多功能定位,抢了不少风头。后来驱蚊贴、电子驱蚊器也冒出来,风油精在国内渐渐不香了。 就在国内市场遇冷的时候,非洲却成了风油精的“救命稻草”。1980年代,非洲大陆蚊虫泛滥,疟疾害人不浅。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每年有60多万非洲人死于疟疾,芒果蝇、硫酸蚁这些毒虫更是让人抓狂,被咬一口,红肿大包痒得要命,恢复慢得让人崩溃。 风油精的清凉效果正好对症下药,涂上几滴,瘙痒立马消,蚊子也躲着走。更厉害的是,这小瓶子还能治头痛、关节痛、晕车,简直是“万能药”。非洲本地压根没技术造这玩意儿,全靠从中国进口,稀缺性让风油精成了香饽饽。 最早把风油精带到非洲的,是些出国的中国人。他们把这小瓶子当礼物送给当地人,效果一传十十传百,风油精的名声在非洲炸开了锅。尼日利亚的集市上,商贩阿卜杜拉靠卖风油精发了家。他从中国商人那儿弄到货,转手卖双倍价,几天就清空库存。 肯尼亚的母亲们用它给发烧的孩子降温,加纳的护士拿它敷病人关节,南非的工人靠它提神。风油精不光是药,还成了社交硬通货。有人拿它当小费,有人用它换地毯、篮子,甚至搞定市场摊位。1987年,漳州香料厂接到乌干达60万瓶的大订单,工厂连夜赶工,出口额很快突破2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上亿,硬是让这3块钱一瓶的小玩意儿成了外汇大户。 风油精的火爆,离不开它的实用性和非洲的刚需。非洲气候热,蚊虫多,疟疾、登革热防不胜防。风油精的配方简单,樟脑、薄荷脑、桉油这些成分,成本低但效果杠杠的。涂上后清凉感立马生效,止痒快,气味还能驱虫,非洲人一试就爱上了。相比西方的驱蚊产品,风油精便宜又好用,3块钱的成本在非洲能卖出好几倍的价格。一些非洲青年靠倒卖风油精混出了名堂,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布拉欣,用几十瓶风油精换来市场摊位,还把地毯生意做到欧洲,赚得盆满钵满。 风油精的成功,也带动了其他中国产品的热潮。云南白药治跌打损伤,六神花露水防蚊又清香,川贝枇杷膏治咳嗽,传音手机便宜耐用,凤凰牌自行车结实好骑,这些中国货在非洲集市上摆得满满当当。1980年代末,中国制造靠着质优价廉,在非洲站稳了脚跟。风油精的出口额节节攀升,1989年达到峰值,直接为国家创下巨额外汇收入。这不光是商业上的胜利,还拉近了中非之间的距离,成了两国交流的纽带。 可非洲市场也不是一帆风顺。一些本地商人眼红风油精的利润,试着仿制,但技术不过关,做出来的东西要么气味呛人,要么压根没效果,砸了招牌。水仙牌靠着过硬质量,愣是守住了市场。漳州香料厂也没闲着,专门为非洲推出大容量包装,方便一家人用。1990年代,西方品牌的驱蚊产品开始涌入,价格高但宣传猛,非洲本地也冒出些低端仿制品,风油精的压力不小。 国内市场更不好过。六神花露水靠着清新味道和多功能用途,抢走不少消费者。驱蚊贴、喷雾这些新玩意儿也层出不穷,风油精在中国的销量一路下滑。如今,风油精还是非洲集市的常客,绿色小瓶子在摊位上闪着光,依然是很多人离不开的“神药”。



![如果你的孩子17岁,给你买了个300块钱的小黄金,你会吵着闹着去退吗?[汗]](http://image.uczzd.cn/8907306216160463471.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