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人有一种蜜汁自信: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人只关注朝堂争斗,而忽略经济民生。剑桥大学还专门写过一部中国经济通史。当时剑桥大学声称中国人没写自己的经济通史,所以只有靠他们来写了。咱们中国人的确没写出自己的经济通史,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早在春秋时代就诞生了十八世纪以前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念比之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都并不显得落伍过时。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此人并非一位端坐书斋坐而论道的纯粹的经济学家,而是一名求真务实的实践者:他亲手推动了春秋战国时代第一位真正的霸主横空出世——这个人就是管仲。齐桓公拜管仲为相时曾询问富国强兵之道。管仲的回答归纳起来就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要想国家强大先得人民富裕。齐桓公又询问富民之策,管仲答:“重在发展国民经济,而不单单是增加国家财政。国民经济发达了,国家财政自然增收”。

在那个年代管仲率先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国家、团体或是个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用管仲自己的话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那个年代是农业社会,因此农业被管仲放在绝对重要的第一位。管仲对于农业的论述十分高深:土地的成色、灌溉的构成等等绝对技术的东西都说得清清楚楚。

管仲研究农业的水准绝对是大学教授级别的。齐国有多少种土壤?什么土壤适合种植什么样的作物?什么样的季节该进行怎样的农业活动?管仲对这些问题全都能说得一清二楚。管仲认为农业生产是要依靠天时的,所以每年的收成是固定的,但打起仗来就会一下子需要很多粮食。这时农民就难以承受。因此国家要有足以应对战乱的粮食储备,同时还要尽量少打仗以积攒国力。

管仲认为国家的税收不能靠农业,因此要减免农业税、在政策上要向农业倾斜。当然他不会想到三千多年后的中国已全面废除农业税,但在当时几乎全国百姓都是农民的年代率先提出减免农业税绝对是超前的先进思想。这点管仲甩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两千多年。管仲将自己的税收政策解释为“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所谓“相地而衰征”就是指根据土质的好坏美恶确定对土地征收赋税的多少。

具体的征收办法是:“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不税”。这不仅考虑到了土地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了年景,所以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的年份税率百分之三十,也就是年税率百分之十五。收成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收成不好的百分之十,灾年不征税。除了税收政策上的倾斜之外管仲还有一个鼓励人们垦荒的大招——包产到户。西周时期配合政治上的分封制在经济上推行的是井田制。

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因为形状像“井”字,所以称做“井田”。全天下所有井田归周天子所有,但在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周天子的政令难以推行全天下,于是周天子就分封诸侯去各地建立国家。分封的土地依然归属于天子,诸侯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受封的各路诸侯又把自己国内的土地分封给自己国内的贵族。所有受封的贵族都是周天子的臣民:他们对封地只享有租税收入,但土地本身的所有权不归他们。

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过这只是理论上而已。西周王朝就像一家大型的跨国上市公司:内部股权的分散导致实际经营业务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势,于是所谓的强势管理层和弱势股东的现象就出现了。实际占有并组织人力耕种土地的是当地贵族,而非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周天子。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时代是没有农民的,有的是被禁锢在贵族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奴。

农奴辛勤耕作的成果是自己所无法支配的,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过是主子的私有财产而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大量原来不适宜开发的土地被开发出来。因此就出现了所谓的公田与私田之争:所谓公田其实也是私有,只不过是由贵族世家占有。私田则是由一家家小农户占有。因为贵族们掌握了话语权就称自己的为公。按当时的井田制规定:由九块田地组成的井字形中间最好的那块必须是公田,边角的田地才能是耕种农户的私田。

结果中间那块土质最好的土地往往是产量最差的,因为在耕种那块土地时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这样一来贵族们要保证自己的收入要么没收私田强迫农奴为自己耕种,要么在承认私田合法化的基础上自己收取私田的租税。管仲的做法是开辟出以前田地上的封疆阡陌,承认人们对自己所开垦土地的所有权,国家只从收成中收取固定比例的租税以维持财政。这实际上起到了和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农业改革中包产到户异曲同工的作用。

《管子·乘马第五》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这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包产到户后老百姓就会自己抓紧农事。

包产到户后老百姓就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不知疲倦地辛勤耕作。不包产到户的坏处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得过且过,磨磨蹭蹭。如今包产到户了,大家分成了,税率也是公开固定的,收成多就得到的多,百姓必然全力去耕作,兄弟父子都会互相督促了。管仲认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而五害之首就是水患。管子专门任命了水官负责国家的水利建设和防洪抗灾。

齐国的水利建设是春秋各国中最完善的。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管仲还积极扶持副业生产。管仲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还通过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百姓种麻。管仲主政期间齐国还将境内杂草丛生不适合粮食生长的洼地开辟成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后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

管仲在那个时代就意识到了植树造林对保持水土和土地肥力的重要性。这一时期齐国的农、林、牧、渔业都因此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齐国利用自己濒海的地理特征大力发展渔业、盐业。管仲知道民间疾苦,知道国家最需要做的是什么,能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管仲在面见齐桓公时说的三句话“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国理念。

在管仲眼里普通百姓和朝廷官员都是人,是人就免不了人性的弱点:比如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话虽是汉朝的司马迁所说,但其实春秋时代的管仲早就看清了这点,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强调道德,也不迷信强权,而是一心务实。

管仲改革的本质是将人性的弱点变成劳动的动力:集大家之私成社会之公。华夏先民造字时“公”字的一半正好对应“私”字的一半。这不正说明古人想告诉我们“合众人之私即为公”。管仲施政不压抑人们的逐利之心,而是正确引导这种逐利之心。这种施政理念是把国家的富强建立在每个国民生活幸福的基础上。管仲改革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战”:对内方面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对外方面就是用扩大对外贸易来制衡战争。

管仲的思路是让各国发动战争的代价大于终止贸易的代价!因此他又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但管仲却将“工商”与“士农”并排。同时管仲又重视调节贫富差距。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那是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其实是对立的。

儒家弟子看不到这世界丑恶的一面,而法家弟子则看不到世间还有美和爱的存在,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认为“善”和“恶”都不是绝对的,但“私”和“贪”却是永在的,自私和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进而想办法使之得到满足。管仲利用人们的逐利之心最终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这与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

私营经济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齐桓公曾要求将国家资源由政府垄断经营,但管仲却说:“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政府不能独占资源,而是应当放手让民众去经营,政府只要征收30%的所得税即可。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金融概念的人:他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管仲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从而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管仲认为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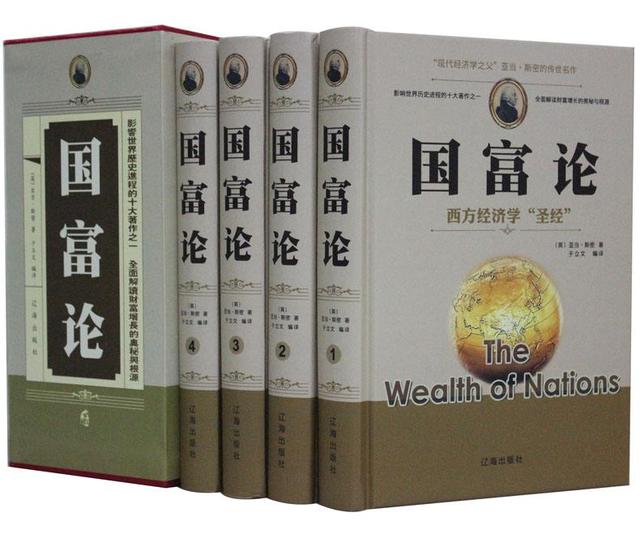
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管仲是第一个强调国家贸易的人:他大开国门欢迎各国商人。关键是管仲掌握了对外贸易中最微妙的技巧: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就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

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反之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管仲的经济思想涉及农业、商业、货币发行等方方面面。管仲对理性经济人概念的阐述比西方世界领先两千多年。管仲已意识到投资、消费、出口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跟凯恩斯经济学遥相呼应,但管仲的理论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其实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货币战争”的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