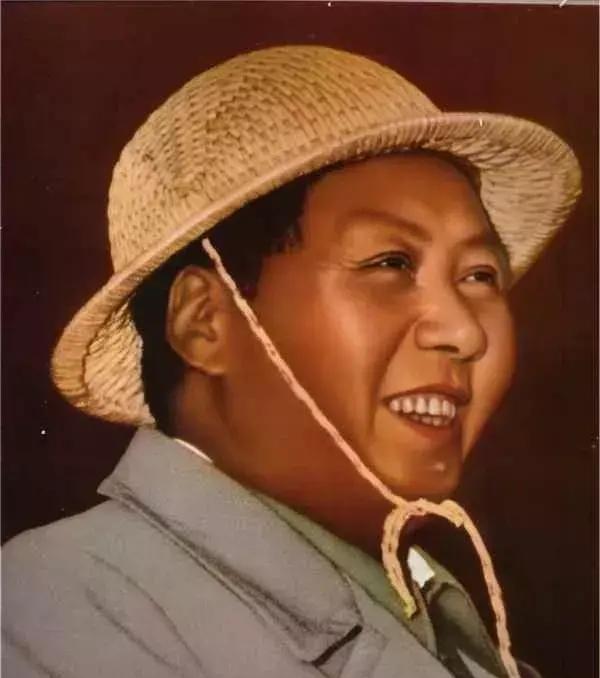1956年,部队在云南原始森林深处,发现一群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男男女女,经过调查发现他们人数众多,而且生活的环境十分落后,常年生活在幽暗的森林中,身上的衣服都快要衣不蔽体,日常大多依靠野果打猎生活,犹如一群原始人在森林中生活。 当年,解放军部队开进云南那片遮天蔽日的原始丛林时,他们的任务是"清边理民",说白了就是要摸清那些盘踞在边境线上的残匪、土司和没上户籍的"山野之民"。 谁曾想他们竟撞见了一群活脱脱从石器时代走出来的"野人",这群人衣不遮体,老幼相携,在阴暗潮湿的密林里靠摘野果、打野兽过活,眼神里透着惊恐,活像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 可他们哪里是什么与世隔绝的"野人"?翻开泛黄的史册,早在几百年前就记载着他们的族名——"锅挫蛮"、"古宗",这些带着歧视的称呼,正是他们苦难的见证。 他们是苦聪人,一个世代被踩在脚下的族群,历朝历代的反动统治者把他们当牲口使唤,稍有不从,轻则抓壮丁,重则一把火烧光整个寨子,一次次血的教训,逼得他们只能拖儿带女躲进深山老林,从此再不敢踏出山林半步,对他们而言山外的世界不是文明曙光,而是索命的阎王帖! 在不见天日的密林深处,苦聪人的日子过得比野兽还艰难,种地全凭一把砍刀点火烧荒,连件像样的农具都没有,衣裳更是金贵只能拿树皮、兽皮胡乱缠身。 雨季一来,湿漉漉的兽皮紧贴在身上,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吃食时有时无,娃娃们个个面黄肌瘦,他们用树枝搭的窝棚四面透风,害了病没药医,只能晒日头、嚼苦草根死扛。 为了活命,每个苦聪人都弓弩不离手,见着生人就像惊弓之鸟,遇上猛兽眨眼间就能隐入密林,这份恐惧早就刻进了他们的血脉里。 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让整个族群像被施了咒似的,人口始终稀稀拉拉,仿佛永远困在了蛮荒时代,他们宁愿忍饥挨饿也绝不下山,就因为吃过的亏太惨痛。 面对这样一群惊弓之鸟,解放军最初的寻找工作屡屡碰壁,之前的几次进山都无功而返,1956年这支队伍立下誓言非要把这群苦命的百姓救出来,战士们白天开路,晚上轮流守夜防野兽,却依然躲不过蚊虫的叮咬。 队伍在林子里转了许久,干粮都快吃完了,仍不见半点人烟,就在大家准备撤退时,一个小战士突然指着一棵二十多米高的大树惊呼起来,树上,一个身影正飞快地攀爬。 众人心头一喜,可那汉子回头瞄了一眼,身子一猫就钻进了密林深处,战士们扯着嗓子在后头喊:"老乡!别跑啊老乡",回答他们的只有山谷里荡来荡去的回声...... 这次失败让带队领导意识到,硬找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们调整了策略,不仅带来粮食、盐巴和布料,还请了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当向导,解放军发现苦聪人会固定到一些野果林采食,便悄悄在树下放上大米和盐,再躲到远处观察。 后来战士们干脆有样学样,跟着苦聪人蹲在林子里摘野果,再慢慢把果子递到孩子们脏兮兮的小手里,这招还真灵,换来了娃娃们几个怯生生的笑脸。 可当工作队说起"分田到户"的好政策时,苦聪人却满脸懵懂,对他们来说能在深山老林里保住性命就是菩萨保佑了,什么户口本、土地证,那都是天边外的事。 要真正打开这把心锁,单靠解放军的努力还不够,还得靠人心,生活在同一片大山里的其他少数民族,谁没吃过旧社会的苦,他们最懂苦聪人的怕与痛,也因此成了最关键的“破冰人”。 一个带动一个,苦聪人紧闭的心门终于开了一道缝,晚上大家围着火塘,民族工作组的同志给他们讲山外新中国发生的事,有的人听得眼泪直流,感慨这辈子从没想过锅里还能冒热气。 工作组又请来傣族、哈尼族的村寨代表,当面承诺:只要下山,就分地分牛,不收税,更不抓人,这些实在的保证一点点击碎了他们心中最后一块冰。 当苦聪人第一次走出大山时,那场景让人动容,他们肩上扛着全部家当,连赖以生存的弓弩,也小心翼翼地拆成了三截背在身上,这个动作意味着,他们选择放下武器,告别过去。 可走出森林只是第一步,融入新生活才是更大的挑战,政府的“温饱工程”紧随其后,在金平县,破旧的草棚被崭新的砖瓦房取代,孩子们走进了学校,寨子里通了广播,山外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进来,政府还分发耕牛,派专人教他们组建生产队,学习现代耕作技术。 就这样苦聪人从阴冷的山脚搬到了平坦的公路边,他们的孩子也学会了对客人喊“老师”,学会了用自家种的大米去换盐巴和布匹,许多老猎手放下弓弩后,再也没回过那片既给了他们庇护也带给他们无尽苦难的森林,他们把新的家园命名为“新安寨”,寓意安安稳稳地开始新生活。 信源:央视网——《国家记忆》 20191009 跨越千年的民族 拉祜族苦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