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俞飞鸿问金星:“做变性手术之前,碰过女人没?”金星回答:“没有,但娶过老婆。”接着她问俞飞鸿:“为啥都50多了还不结婚?” 金星从小时候起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表面看是个男孩子,可心里总觉得该是个姑娘。 这种别扭的感觉像鞋子总穿错脚,走路都不自在。 好在老天给了她舞蹈这根救命稻草,音乐一响,她就活过来了,在练功房镜子前比谁都精神。 九岁那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来招生,老师捏着她细长的脚背直点头:"天生跳芭蕾的料!" 可当小金星瞅着录取通知书上"男学员"仨字,心里像塞了团湿棉花。 舞蹈这条路她走得比谁都狠。 十二岁进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每天四点就摸黑起床练功。 同屋男孩还打呼噜呢,她已把腿架在暖气片上压得骨头咯咯响。 有回排练《红色娘子军》,她死活要跳吴琼花,教官指着她板寸头直瞪眼:"胡闹!你见过带喉结的娘子军?" 那天夜里她躲在被窝掉眼泪,眼泪珠子把军绿枕巾浸出深色地图。 十年后真熬成了角儿。 1988年拿全额奖学金去纽约学现代舞,白皮肤蓝眼睛的同行都竖大拇指。 可每次卸完妆,镜子里那个肌肉虬结的身体总让她发怔。 有回在布鲁克林旧公寓,她望着晚霞突然把口红抹满下巴。 镜面映出带胡茬的怪诞女郎,手里的粉饼盒咣当砸在水泥地。 1993年冬天,北京友谊医院的走廊冷得像冰窖。 母亲攥着她刚签的《自愿手术书》,眼泪在皱纹里淌成小河:"儿啊,这手术要摘肋骨锯盆骨,比你跳十场舞都疼。" 二十七岁的金星把母亲长满茧子的手捂在胸口:"妈,不疼这遭,我骨头缝里都透着冷。" 她第一次手术选了隆胸,全麻醒来摸到胸口柔软弧度,笑得扯痛刀口。 第二次除毛囊才要人命。 医生拿着通电镊子逐个拔胡须根,麻药没打够地方,电流烫得她指甲抠裂手术台。 最险是第三次生殖器重建,十六小时手术中腿神经受损,护士发现时她小腿硬得像冻肉。 医生摇着头交代后事:"保命要紧,跳舞别想了。" 谁曾想这姑娘咬牙复健九个月,硬是拄着拐蹭进排练厅,汗珠从下巴滴答砸在把杆上。 感情路上更是摔得鼻青脸肿。 早年在美国为绿卡登记假结婚,结婚证墨迹未干就和"丈夫"分道扬镳。 1995年在巴黎演出谢幕时,德国商人汉斯捧着鸢尾花冲进后台。 当金星抖着嘴唇坦白过往,汉斯却把花束塞进她汗湿的手心:"那年的男孩替我守护了现在的你,我该给他鞠个躬。" 后来《舞林大会》上评委席的她可真是块爆炭。 选手镶钻演出服刚晃上台,金句就跟着追光灯砸下来:"金箔纸裹根萝卜就想充金条?回去把基本功压够三百天!" 不过小演员们倒乐意挨她训。 之前有群街舞少年动作编排凌乱,反被她拉住自掏腰包请来北舞教授补课。 这档节目收视率总飘在榜首,电视台内部流传句调侃:"金老师嘴是手术刀,专给娱乐浮肿症开刀。" 五年前节目里遇到俞飞鸿,两位姐姐挽手说私房话。 俞飞鸿突然问:"做手术前真没碰过姑娘?" 金星指尖绕着茶盏沿打转:"婚书领过,床没沾过。" 没等对方回过神她又反问:"你都五十了,神仙似的脸往哪儿搁?" 俞飞鸿笑眼弯成月牙:"好妹妹,你挨过十六小时刀换来自在,我何必为个名分把自己劈两半?" 茶香氤氲里两只手攥在一处,演播厅顶棚的镁光灯暖得化开了心口冰碴。 眼下上海公馆里热闹得很。 收养的三个孩子在客厅追着折耳猫满屋跑,汉斯拿德语夹上海话吼:"小赤佬当心阿姐的奖杯!" 厨房飘出油焖笋香气,金星刚拆了舞剧《海上探戈》的巡演邀请函。 新剧本在桌上摊着,空白处有她钢笔批注:"第三幕群舞改单双人交替,让每个角色都成为自己的太阳。" 夜幕爬上窗棂时,电视正重播她年轻时的《半梦》。 荧幕上白衣舞者腾跃如鹤,落地窗倒影里穿真丝睡袍的女人屈膝轻哼旋律。 当年手术同意书上签的名字叫金星,如今这名字烫在文化部"突出贡献艺术家"的证书上。 这束光从练功房残破的镜子里出发,终究把暗室劈成了亮堂堂的天地。 对此您怎么看呢?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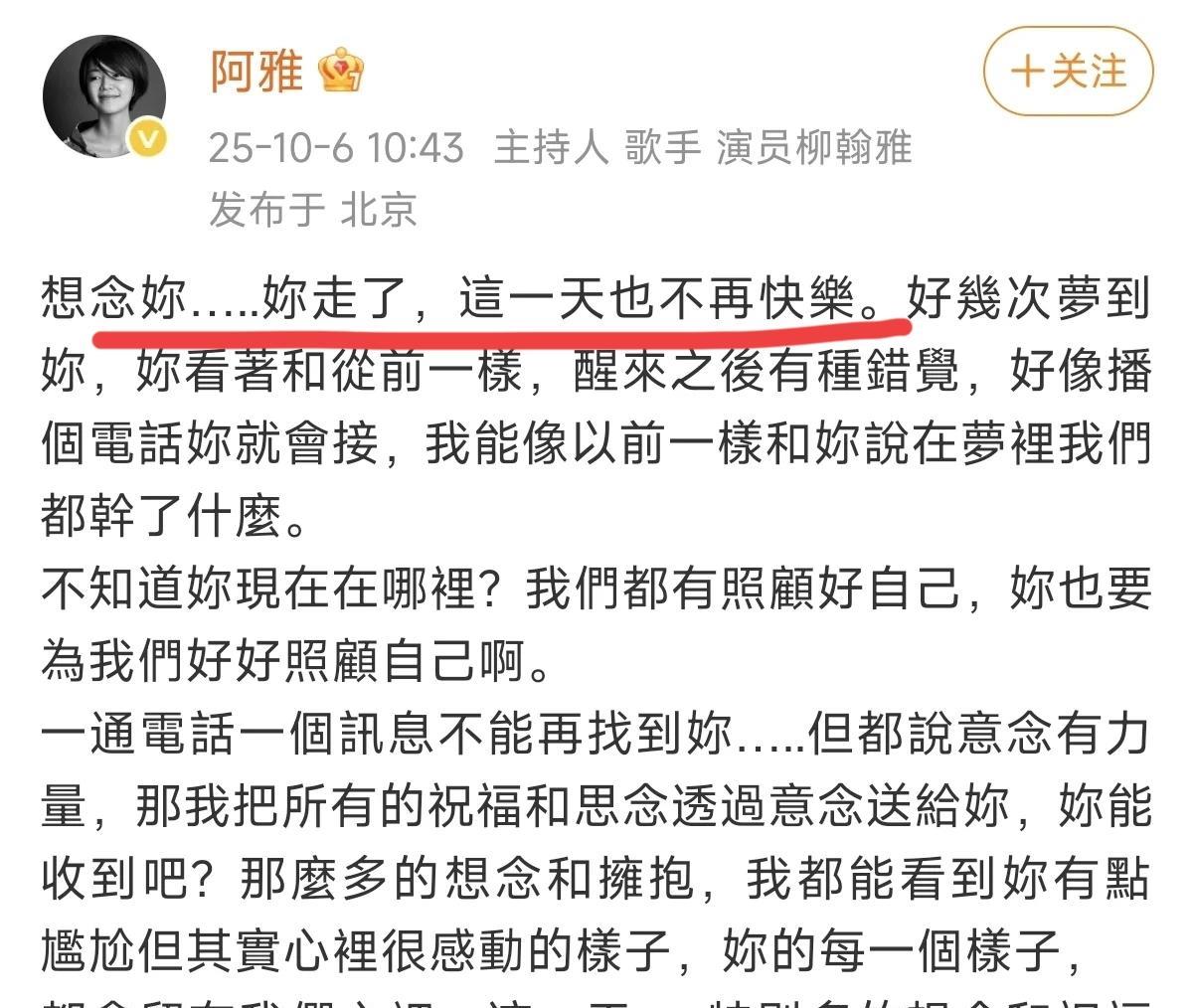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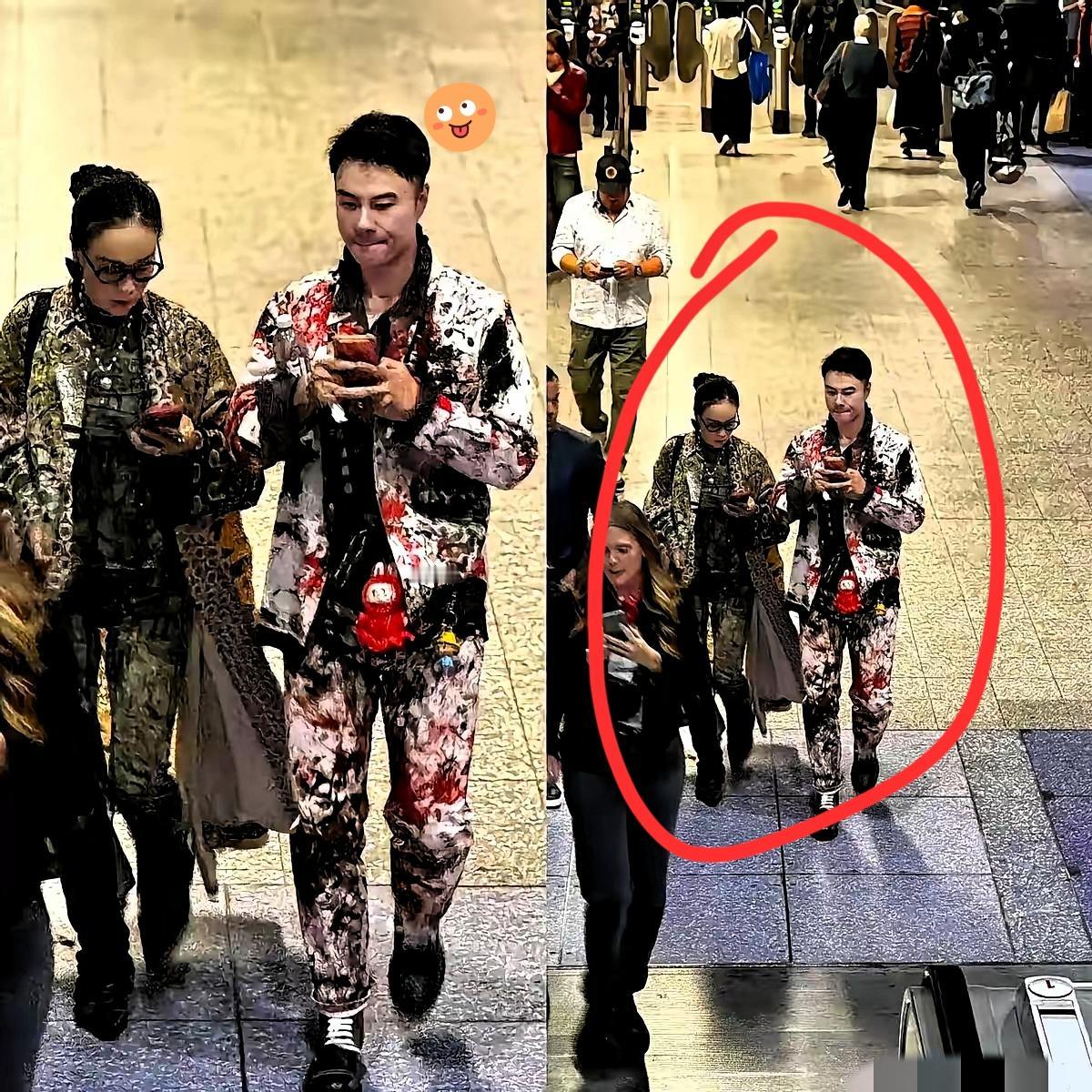


江山无限
😂
用户10xxx57
说白了这种人就是喜欢别人聚焦于祂,没人关注祂祂就会焦虑,就会恐慌,暴力倾向,严重的精神疾病
用户10xxx14
娶了老婆但是没碰女人,这个真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