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天,钱瑛受中央安排到甘肃考察,从张掖地区考察完毕,前往高台县的路上,司机迷路,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到了地方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夹边沟劳教场。
夹边沟处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当时是甘肃省的一个劳教场,距离酒泉三十余里。
而这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农场,就好是地图上刻意模糊的坐标。
当钱瑛的吉普车因司机迷路闯入这片禁区时,龟裂的盐碱地上正蜷缩着近三千名“右派”。
他们有的曾经是教师、工程师、或者地方干部,但是此刻却裹着破絮单衣,每日仅靠七两口粮维系生命。
当钱瑛的棉靴踩上冻土时发出碎裂声。
她看见墙根下晒着太阳的老汉,怀里紧抱冻硬的窝头,那窝头硬得能把牙给崩碎,即使是这样这没有人舍得啃食,只敢用体温慢慢焐软。
农场干部看到这搓着冻红的手解释“物资紧张”,但是话还没说完就便被钱瑛截断。
1948年大别山突围,我们杀战马给伤员煮汤时,没说过‘物资紧张’就该冻死人!
此时她年轻时在洪湖打游击的锐气此刻再度迸发,当即下令卸下吉普车上的干粮和毛毯。
而钱瑛出生在湖北咸宁的一个普通人家,谁也想不到这个女婴日后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监察部长。
她从小家境贫寒,但是他的父母却坚持让她读书,他们觉得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即使家里再穷再苦也不能哭苦了孩子。
就这样她白天学《女儿经》,晚上就着油灯做针线活补贴家用。
1924年考上省立女师后,她结识了董必武、陈潭秋和钱亦石这些进步人物。
他们的进步思想像火种一样,点燃了这个乡下姑娘的革命热情。
之后在1927年加入中共的钱瑛,曾在洪湖组建游击队,被百姓传说为“贺龙的妹妹”。
那时候的她带队员穿行芦苇荡,用土炮阻击白军船只,如今监察部长的旧棉袄下,还残留着南京监狱烙铁烫伤的疤痕。
当农场管教干部阻拦分发物资时,钱瑛的质问直刺要害,我在洪湖见过地主家的长工喝热粥,共产党的农场倒让人啃冻窝头?
只见她蹲身握住一位老教师皲裂的手,那手如枯枝般颤抖。
这让她想起1931年丈夫谭寿林就义雨花台前写给她的血书,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
此刻她闯的,是比监狱更森严的体制壁垒。
当晚钱瑛直抵兰州省委,此时的会议室暖气蒸腾,但是她却推开窗,让戈壁寒风灌入会场。
夹边沟的炊烟是焚尸烟!每天饿死的人用草席卷着埋,坟头白茅草像招魂幡!
她摔出记满数据的笔记本,2847人中已有432人死于浮肿病,幸存者因吞食草籽腹胀如鼓。
于是官僚机器的齿轮开始逆旋。
钱瑛亲自坐镇调度,酒泉地区所有公交车被征调转运人员。
她致电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里,夹着幸存者咳血的录音磁带。
十天后,首批800名劳教人员登车时,有人突然扑向钱瑛的吉普车嘶喊,告诉主席!我们能种麦子!
他们是农技专家,但是却在盐碱地里徒手拔草三年。
而这场救援成为钱瑛监察生涯的缩影。
早在武汉任中南局组织部长时,她曾彻查黄永胜亲戚冒名开设的烟馆。
任监察部长后更平反安徽李世农冤案,顶住压力否决“贪污一船盐”的荒唐指控。
在夹边沟,她发现农场账本记载“月供粮三十斤”,实际却被层层克扣至半。
当省委干部辩称“全国困难”时,钱瑛指着他腕上瑞士表冷笑,饿死人的地方,干部手表倒准时!
之后她将监察利剑插进灾荒腹地。
随后的调查报告催生19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甘肃省委班子改组,夹边沟农场次年关闭改建林场。
幸存者中后来走出中学校长、抗旱小麦育种专家,而他们珍藏的共同记忆是,戈壁夕阳下,那个裹旧棉袄的身影站在吉普车顶,目送车队驶向生路。
2010年,作家杨显惠在定西走访最后一批幸存者时,总有人颤巍巍翻开褪色笔记本,纸页间夹着干枯的骆驼草,旁注“钱部长给的粮票换的馍”。
此刻夹皮沟金矿正转型工业遗址,井下1500米坑道与戈壁林场遥相呼应,共同诠释着“金色国度”的双重含义,既是地底的黄金矿脉,更是人性不灭的光泽。
如果当时司机没有迷路,如果当时她没有深究这个事情,那2847个生命会是什么结果?
只是没有如果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意志,向铁面无私的女包公钱瑛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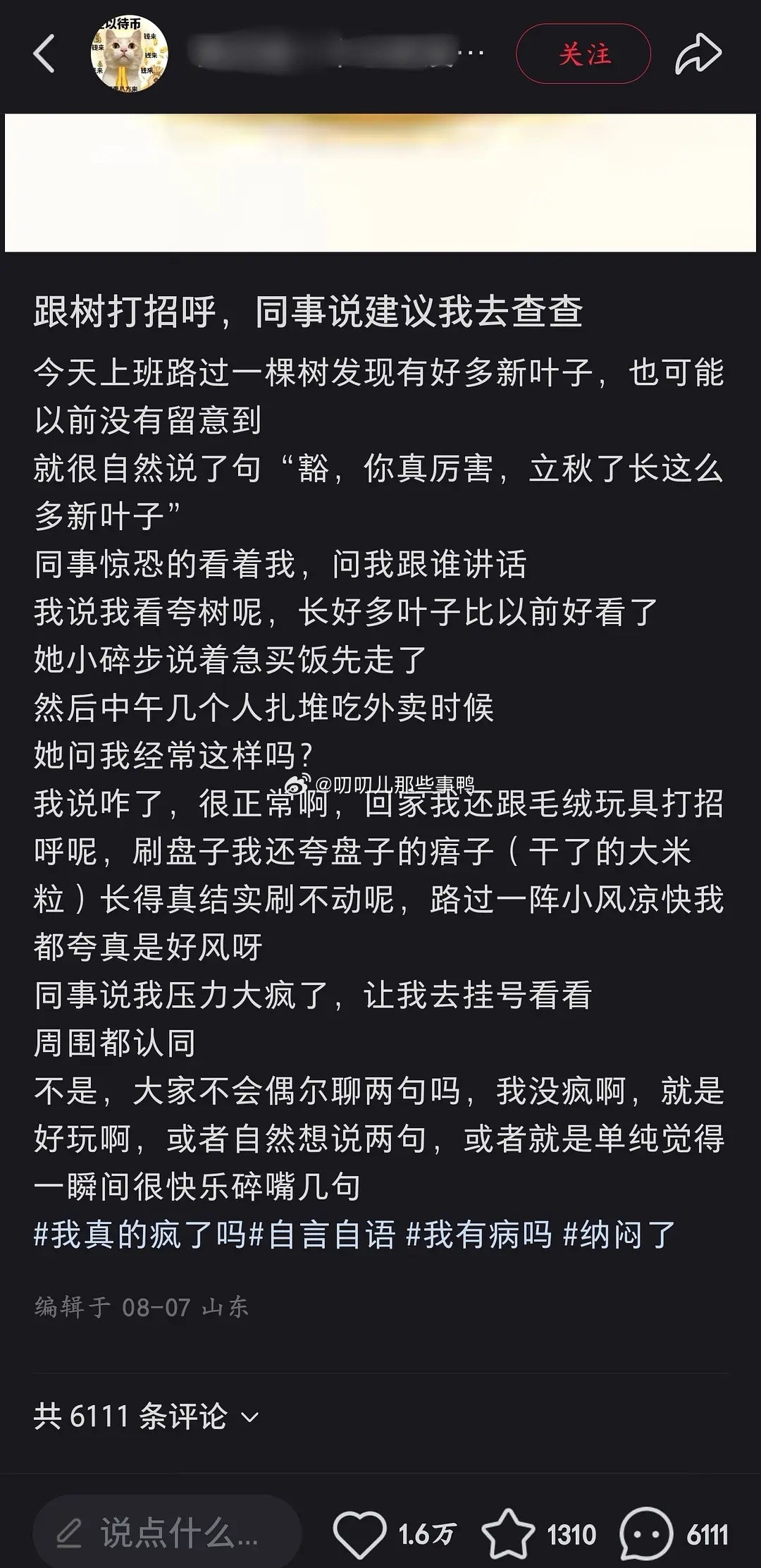








鑫龙
致敬共和国功臣!
用户10xxx10
毛主席时代的领导,没说的就是一个赞👍🏻!
青山绿水
这才是人民的公仆
菜籽发发飞房
在郑耀先哪里见过,好领导,巾帼英雄
菜籽发发飞房 回复 08-15 07:25
致敬
国粹老邹-专业卫浴20年 回复 08-17 05:48
看过潜伏的才知道,钱部长[赞][赞]
f feng shi
总有圣人卫中华,国家大幸!
洁净的空气
就像观世音经过
Arvin
致敬伟大英雄
七月流火
一身正气 为国为民[哭哭][哭哭]
冷风催
这么好的女干部今日才知道
哄哄
民族脊梁
用户29xxx55
点赞钱部长!
佳乐通讯
致敬
大汉伟东
这个应该拍电影,让后人永远记住,不让悲剧再现。
俞修刚 回复 08-15 13:55
有电视,葛优主演的,
老蔡 回复 08-23 19:32
电影表现不了的,去看看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吧!
用户10xxx25
国家应有多这样的干部,为人民谋幸福!
用户10xxx37
致敬人民的好领导
用户10xxx95
功不可没,功臣[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用户10xxx85
正宗国家卫士!
能希
她是一棵永远闪亮的启明星!!!
三脚猫道士七世
把公知台独放里面正好!
用户10xxx56
了不起的女英雄女豪杰
古道西风
现在喝不出小时候红薯粥的味儿了
用户10xxx42 回复 08-15 17:07
那是因为你好的东西吃得太多了!
一丝涟漪
只能说不管什么政策甘肃执行力度绝对到位,
孤霜冷月
巾帼英豪 一身正气
阳光灿烂
铁面无私的第一任监察部长!
原野
领导生前就是菩萨
西北风
1927年的老党员[点赞]
用户10xxx73
[大哭][大哭][大哭]
知味斋主人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用户10xxx28
赤子之心,光耀人间。
云姿无式
共和国初期的艰难,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
用户70xxx64
这就是毛主席时代的人民干部也叫人民公仆。
用户76xxx64
司机有功。
建武
[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用户10xxx16
国之栋梁,人民救星!
用户13xxx68
人民干部为人民,中国的脊梁
雨中的园
人性的光辉!更是共和国的好公仆!
顺风顺水
一身正气,共和国功臣,永垂不朽!
用户98xxx57
向钱老致敬!
走走停停
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共和国脊梁
用户97xxx98
伟大,致敬🫡🫡
用户98xxx18
致敬老革命家!
用户10xxx29
谭寿林是梧州市的革命历史人物
天高云淡
钱瑛还有另外一个人
随时
坚持真理,公平公正公开,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