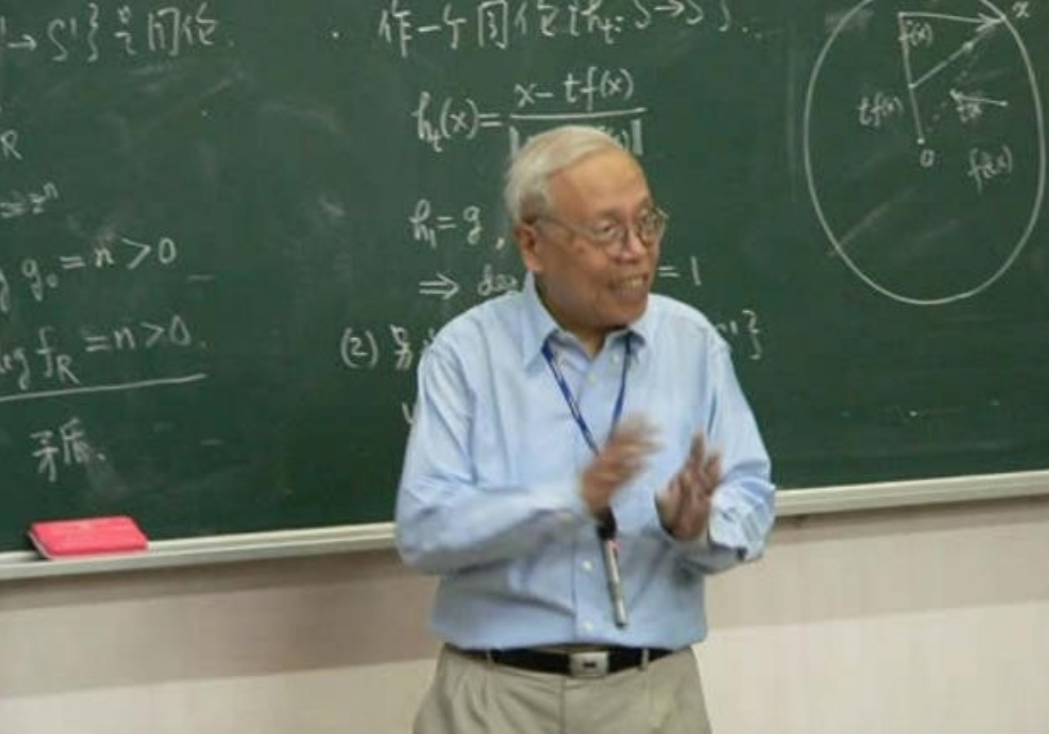语出惊人!87岁姜伯驹院士直言:“不是别人要卡我们的脖子,而是我们用教育卡住了自己的脖子!”中国每年毕业800余万大学生,但在数理化领域有建树的人却少之又少,谈得上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更是寥寥无几…… 这样的判断,出自一位将毕生精力投入数学研究与教育的泰斗之口,分量不言而喻。
姜伯驹院士作为中科院院士、我国拓扑学领域的权威,不仅在“低维流形”等前沿数学领域深耕数十年,更在北大讲台执教半个多世纪,亲眼见证了中国教育的变迁。
他的感慨,并非空泛的批评,而是基于对教育本质与人才成长规律的深刻洞察。 从数据看,中国教育的“规模”早已位居世界前列。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180万人,这一数字超过许多国家的人口总量。
但在姜老看来,数量的堆砌不等于质量的提升。他曾在一次教育论坛上直言:“我们的学生能快速掌握知识点、精准套用公式解题,可当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时,很多人就束手无策了。”
这直指当前教育的核心问题——过度聚焦“应试”,把教育变成了标准化生产“解题者”的流水线。 中学课堂里,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老师将数学题的多种解法归类为“高效得分法”“稳妥答题法”,明确告知学生“考试时用这种,别用那种”。
物理课上,学生提出课本外的解题思路,得到的回应往往是“步骤太复杂,考试会吃亏,按标准答案来”。
这种对“效率”和“分数”的极致追求,压缩了学生自主思考、探索未知的空间。
姜老曾翻看一位高中生的习题册,发现扉页上记满了“高频考点”“得分技巧”,却没有一处“我的疑问”或“新想法”,不禁扼腕:“教育不是培养‘考试机器’,而是要让学生敢想、敢试、敢犯错。” 对比姜伯驹院士的成长经历,这种教育导向的偏差更显突出。
16岁考入北大数学系时,他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模式:老师抛出“拓扑学基本概念”后,会留足时间让学生泡图书馆、组讨论组,甚至为一个定理的证明争得面红耳赤。
他的导师江泽涵先生常说:“知道‘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追问‘为什么’,甚至‘能不能不是这样’。”这种强调“悟”与“探”的氛围,让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对未知领域的敏感。 上世纪80年代,当国外“低维流形”研究已成为数学与物理交叉的前沿时,国内对此几乎空白。
当时已在微分几何领域颇有成就的姜伯驹,毅然停下自己驾轻就熟的研究,转而给本科生开设这门新课。
没有现成教材,他逐字翻译外文著作,将抽象理论转化为“用橡皮泥演示曲面变形”“折纸观察拓扑结构”等直观案例;课堂上,他从不直接给出结论,而是故意留下“证明漏洞”,引导学生上台补全。
他常对学生说:“一篇论文的价值,不如培养出一个能提出新问题的学生。”后来,这门课走出了王诗宬等一批数学家,成为中国拓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这种教育理念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人才结构。
如今,中国在中端应用型人才储备上堪称充裕,甚至出现部分领域过剩的情况,但在芯片、光刻机等“卡脖子”领域所需的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却长期存在缺口。
姜老曾指出:“基础学科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就像一棵大树的根,根扎不深,树长不高。可现在的教育,总在催着枝叶生长,却忘了给根留足土壤。” 在AI时代,这一问题更显迫切。人工智能已能快速完成复杂计算、写出标准代码,但若论“提出新问题”“创造新方法”,仍依赖人类的原创性思维。
可当前教育仍在强化“快速解题”“精准套用”的能力,相当于让学生与AI在其最擅长的领域竞争。
姜老对此忧心忡忡:“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这些恰恰是我们的教育最容易牺牲的东西。” 近年来,“双减”等政策试图为教育“降温”,但在升学率、就业压力等现实因素影响下,不少地方陷入“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困境。
姜老认为,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回归教育本质:“教育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让人成为‘完整的人’——既有知识,更有思想;既能传承,更能突破。” 这位87岁的老人,至今仍会去旁听北大的基础课,偶尔给学生讲一讲“当年我们是怎么争论一个定理的”。
他的话语或许尖锐,却藏着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期盼:解开教育对自己的“束缚”,才能让更多顶尖人才破土而出,真正打破“卡脖子”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