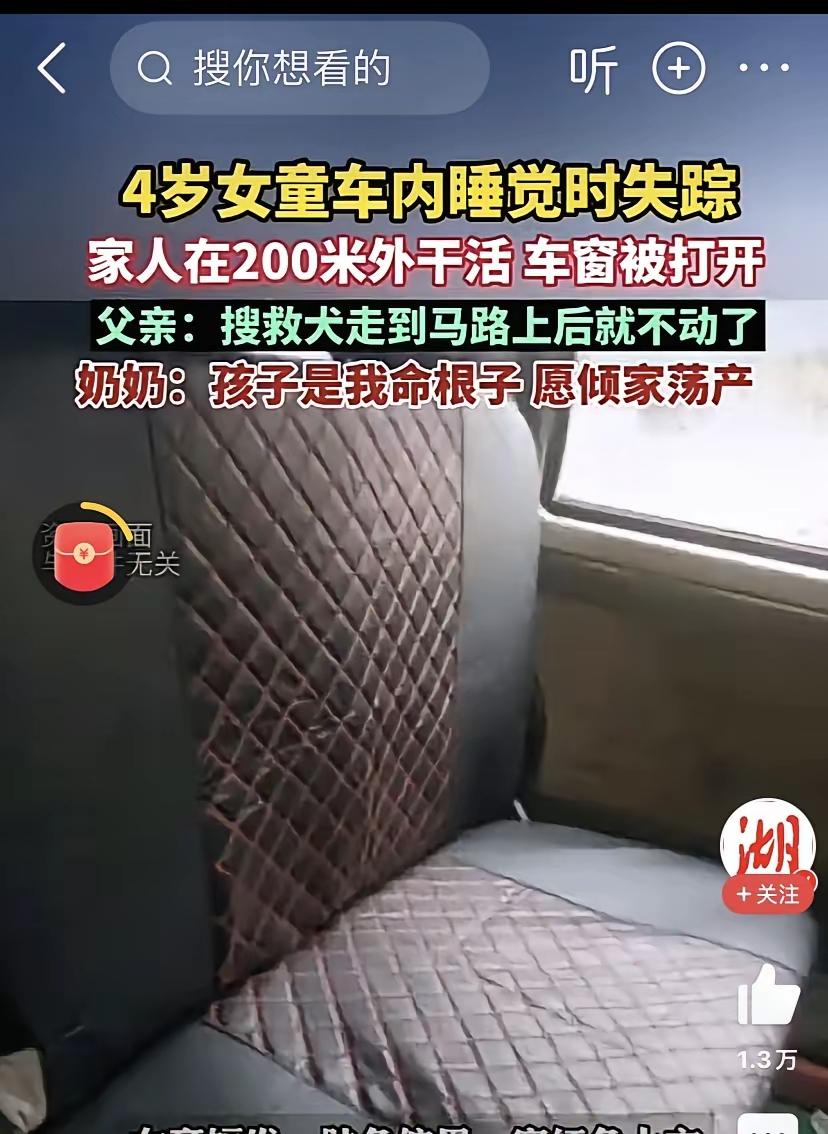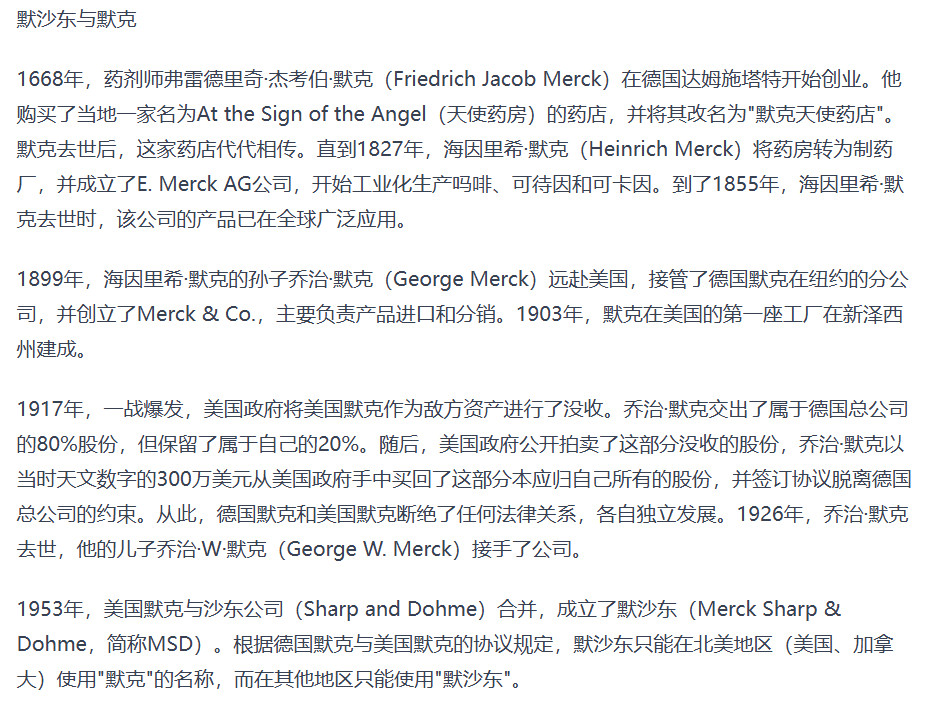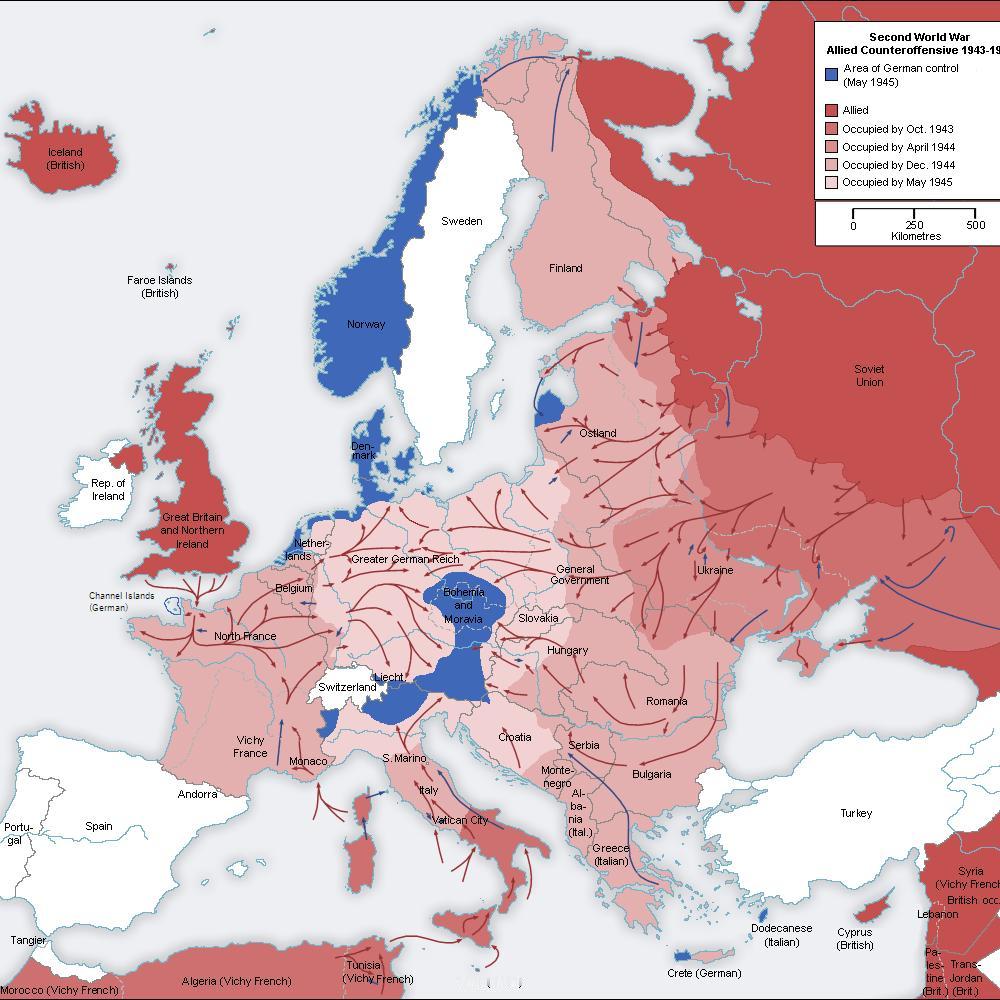710年,李隆基率军杀入宫中,在除掉了韦后和安乐公主后,当看到在一旁瑟瑟发抖的上官婉儿,心中有所迟疑,但还是将她杀掉,事后,太平公主震惊的说:“婉儿并非韦党,就这样被杀了,三郎的手段也太狠辣了。” 宫墙下的血还没凝住,太平公主捏着帕子的手在发抖。她想起昨夜婉儿送来的密信,字迹还是那般娟秀,却字字都在提醒:韦后已备下毒酒,邀相王明日入宫。那信纸此刻还藏在她的袖中,边角被冷汗浸得发皱。 李隆基擦拭着剑上的血,铜制的剑鞘映出他年轻却冷硬的脸。“姑母可知,婉儿案头那叠奏折里,有三封是替韦后草拟的遗诏?”他把一个锦盒推过去,里面是几页洒金纸,笔迹确实是上官婉儿的,只是结尾处“韦氏临朝”四个字被墨团涂得死死的。 太平公主猛地合上盒子。她当然知道这些,就像知道婉儿十四岁起就在武则天身边抄录奏章,知道她在中宗复位后,一边帮韦后写诏书,一边偷偷给相王递消息。这宫里的人,谁不是脚踩几条船?当年武则天杀了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她不还是靠着才华爬到了昭容的位置? “她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太平公主的声音发紧,“就像当年你我在武后跟前装疯卖傻,不也是为了活命?” 李隆基没接话,转身看向窗外。晨光正从紫微宫的鸱吻间漏下来,照亮了庭院里倒伏的侍卫。他想起三天前,谋士刘幽求跪在他面前,额头磕出了血:“殿下,上官昭容八面玲珑,今日可助韦后,明日便能附太平,留着她,迟早是祸患!”那时他只觉得这话太狠,此刻剑上的血腥味却让他清醒——这不是吟诗作对的场合,是要把脑袋拴在腰带上的政变。 婉儿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支紫毫笔。她大概是想再写点什么,或许是辩解,或许是另一份投名状。可她忘了,在刀光剑影里,笔墨从来抵不过刀锋。当年她帮武则天杀了多少李唐宗室?后来又帮中宗把韦后的娘家人一个个封了大官。她总以为自己是棋盘上的棋手,却不知在真正的权力游戏里,她不过是枚随时可弃的棋子。 太平公主心里像堵着块冰。她比谁都清楚婉儿的本事。那年吐蕃求亲,点名要她去当赞蒙,是婉儿在朝堂上引经据典,说“妇人无外事,若随异域,恐失国体”,硬生生把这事搅黄了。还有那次宫宴,安乐公主逼着中宗废了太子,也是婉儿跪在地上哭着劝谏,额头磕得青肿。这样的人,怎么就成了三郎嘴里的“祸患”? 可她看着李隆基眼里的决绝,忽然说不出话来。这侄子跟他爹李旦不一样,李旦会在朝堂上被韦后的人骂得缩脖子,李隆基却敢带着三百甲士直闯玄武门。他要的不是折中,不是平衡,是干干净净的权力版图——凡是有可能碍事的,不管是谁,都得挪开。 下葬那天,太平公主让人给婉儿换上了一身紫色朝服。按照礼制,昭容不该穿这个品级的衣服,可她知道,婉儿这辈子最在意的不是封号,是那身能踏入紫宸殿的官服。送葬的队伍走到朱雀大街时,有人认出了棺木上的标记,低声议论:“这不是上官昭容吗?听说她帮韦后谋逆呢。” 太平公主听见了,却没回头。她想起婉儿写过的一句诗:“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当年觉得这话说得真好,既讲情谊又守气节。如今才明白,在这皇宫里,连璧易碎,臭兰易枯,最不值钱的是情谊,最没用的是气节。 后来李隆基登基,成了唐玄宗。有回他翻看旧档,看到婉儿当年编的《全唐诗》,忽然问身边的高力士:“你说,当年朕杀她,是不是太急了?”高力士捧着茶盏,慢悠悠地说:“陛下,自古成大事者,眼里容不得沙子。” 李隆基没再说话,只是把那本诗集放回了书架。阳光穿过窗棂,在泛黄的纸页上投下光斑,像极了当年紫微宫里,婉儿笔尖漏下的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