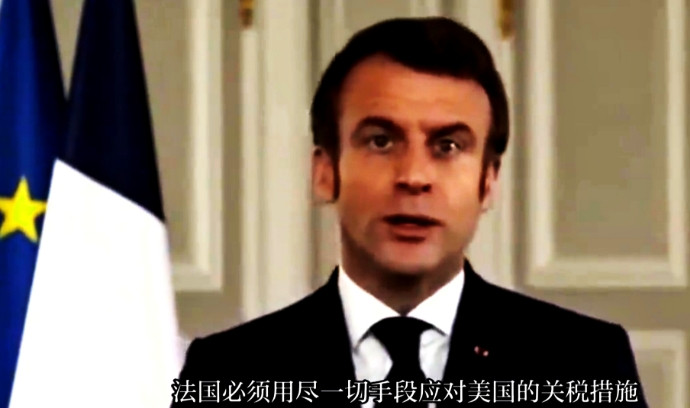马克龙要求欧洲上桌现如今,法国成了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最后希望。如果法国不行了,那欧洲真的就没救了。
法国的国防工业体系堪称欧洲最完整的存在。从达索公司的 “阵风” 战斗机到泰雷兹集团的电子战系统,从海军集团建造的 “戴高乐” 号核动力航母到 MBDA 公司的 “紫菀” 防空导弹,法国能够独立完成从设计到生产的全链条国防装备供给。这种自主性在 2025 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 当德国联邦国防军因美国延迟交付 “爱国者” 导弹系统而陷入防空真空时,法国陆军的 “SAMP/T” 防空系统已在罗马尼亚完成部署,其核心雷达与拦截弹均为本土研发。相比之下,英国皇家空军的 “台风” 战机虽挂着欧洲联合研制的标签,但其关键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仍依赖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技术授权;德国莱茵金属集团生产的 “豹 2A7” 坦克,主炮身管加工设备需从美国进口;意大利芬梅卡尼卡集团被美国雷神公司控股后,其 “欧洲多任务护卫舰” 的作战系统调试必须获得华盛顿的技术许可。
外交领域的自主性更是法国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显著标志。马克龙在 2025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直言 “欧洲不能再做美国的追随者”,这种表态并非空穴来风。从 2003 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 2018 年坚持与伊朗保留核协议,再到 2024 年推动欧盟与非洲建立独立防务对话机制,法国的外交决策始终保持着与美国的距离。这种独立性在俄乌冲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 当英国紧随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挑战者 2” 坦克时,法国虽也提供了 “凯撒” 火炮,却同时推动欧盟与俄罗斯保持能源谈判渠道;当德国因美国施压而冻结 “北溪 - 2” 项目时,法国仍维持着与俄罗斯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英国则完全不同,约翰逊政府时期提出的 “全球英国” 战略,本质上是通过紧跟美国全球战略来维持影响力,其在红海危机中派遣航母战斗群配合美军行动的决策,几乎与华盛顿同步。德国受二战后政治框架约束,外交政策始终以欧盟协调和美国安全保障为前提, Scholz 政府即便提出 “ Zeitenwende ”(时代转折)防务政策,其核心仍是增加对美制武器的采购。意大利则因政局频繁更迭,外交立场摇摆不定,孔特政府时期曾接近俄罗斯,梅洛尼政府又转向亲美,难以形成稳定的自主战略。
美军驻军的存在与否,更从物理层面揭示了欧洲各国的主权状态。法国境内没有美国永久驻军,这一事实在北约成员国中显得尤为特殊。自 1966 年戴高乐总统宣布法国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机构后,美军便撤出了法国本土,尽管 2009 年萨科齐政府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但仍坚持保留军队指挥权,美军在法仅设有少量联络机构,无作战部队部署。这种状态使得法国在军事行动决策上拥有更大空间 ——2024 年法国空袭非洲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时,无需像德国那样提前获得美国驻欧洲司令部的情报许可。英国则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支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常年部署 B-52H 战略轰炸机,其使用权完全由美国空军掌控;德国拉姆施泰因基地作为美军欧洲空运枢纽,每年处理超过 60% 的驻欧美军物资转运,柏林对该基地的活动几乎没有否决权;意大利阿维亚诺基地的美军 F-16 战机部队,其作战范围覆盖巴尔干至中东,罗马政府曾试图限制其行动范围,最终因美国施压而放弃。
法国推动欧洲自主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但其军工实力提供的物质基础、外交传统积累的战略自信、以及无美军驻军带来的决策自由,共同构成了其他欧洲国家难以复制的条件。英国的盎格鲁 - 撒克逊纽带使其难以脱离美国轨道,德国的历史包袱与现实安全依赖限制了其自主空间,意大利的政局动荡则使其难以承担长期战略责任。在美俄博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法国能否扛起欧洲战略自主的大旗,不仅关乎其自身定位,更决定着欧洲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角色 —— 是成为独立一极,还是继续作为大国博弈的附属品。这种特殊性,让法国在欧洲寻求自主的进程中,成为了无可替代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