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太原特宪队的食堂里,酒肉香正浓,十个刚沾满地下党员鲜血的特务举杯狂欢,却没人知道,雇来杀他们的杀手已站在门外,更荒唐的是,雇主竟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这帮特务属于阎锡山“特种警宪指挥处”,老百姓背后都叫它“阎王殿”。太原解放前夕,他们知道自己要完蛋了,就疯狂抓人杀人。 手段特别毒辣,有勒死的,有用湿纸糊脸闷死的,有逼人服毒打毒针的,甚至直接活埋。这么多人命,就为了保住他们那个摇摇欲坠的政权。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么快就成了被清洗的对象。特务头子徐端接到上级梁化之的密令,要求把直接参与屠杀的执行者也全部“处理掉”,来个死无对证。徐端于是找来了职业杀手查景道。 —— 查景道那年三十八,面相却像五十,皱纹里夹着旧刀疤,一笑像门轴缺油。他干这行不靠枪,靠“票”——一张印着“太原城防指挥部”的通行证,外加一根自行车辐条磨的尖刺,比子弹安静,比绳子快。徐端给他开的价是:十条命,一根金条,先付半根,事成后半根埋在西门外老槐树下,他自己去刨。查景道啐了口唾沫:“半根就半根,老子早想给阎王殿拆门槛。” 夜里十一点,他提着一只空食盒,盒底藏着那把辐条,敲响了食堂后门。灶上的老王见是“上面来送夜宵”的,没多问,还赔笑:“长官辛苦,里头正喝到兴头上。”查景道点头,顺手把一包“哈德门”塞老王兜里——烟里掺了迷药,三分钟后老王抱着灶台打呼噜,锅里炖着的狗肉咕嘟咕嘟冒泡,像嘲笑。 食堂里那桌,十个人已经喝成关公脸,领头的叫赵三金,一手撸串一手搂姑娘,姑娘是抓来的女学生,脸上泪痕没干就被灌了半碗烧刀子。赵三金喷着酒气唱《兄妹开荒》,调子跑到绥远,旁人拍手叫好,没人注意门缝里飘进一股冷风。查景道把灯一拉,只剩壁上一盏煤油灯晃,灯芯“啪”地爆了个花,像提前放枪。 他先绕到赵三金背后,左手捂住嘴,右手辐条从颈侧滑进去,位置精准得像挑猪脊髓,血“呲”一声喷在姑娘白衫上,像盖了个戳。姑娘吓得要叫,查景道捂住她嘴:“别出声,你自由了。”人没杀完,他先放人,这是他的怪规矩——“冤有头债有主,孩子算利息。” 剩下九个,已经醉得拿筷子当烟抽。查景道把桌上转盘一转,狗肉汤转圈,热气蒙住人脸,他趁机又放倒数人。有人觉出不对,摸枪,枪套扣着,辐条已经扎进眼窝;有人想跑,腿软跪倒,抱着查景道大腿喊“哥,我上有老下有小”,回答他的是一句“太原城下埋的人,谁没老小?”尖刺从下巴贯进,声音戛然而止。 三分钟,十具尸体横七竖八,酒气混血腥,像卤锅打翻。查景道把半根金条从赵三金牙缝里撬下来——那是预付的“牙筹”,行内规矩,命完牙掉。他顺手把桌上没动的汾酒倒在地上:“敬你们,也敬我自己,下辈子别当狗。” 出门时,月亮被云啃得只剩一弯,像老天也怕看。他路过刑讯室,铁门半掩,里头吊着个半死的地下党员,脚尖点地,已经没力气哼。查景道把人放下来,那人睁眼,瞳孔散得很大,却挤出笑:“兄弟……自己人?”查景道没吭声,把剩下半包迷药烟塞进他嘴里,背起人往外走。门口哨兵早被徐端调走,一路畅通,只有野猫跟在脚后,尾巴一扫一扫,像替死人收尸。 第二天,太原城防司令部贴出告示:昨夜共军特工偷袭,十名同志殉国,全城戒严搜捕。老百姓围着告示笑,笑完又哭,哭完往“阎王殿”门口扔臭鸡蛋。鸡蛋砸在徐端的车窗上,黄白一滩,像给他提前出殡。徐端坐在车里,手指敲膝盖,节奏跟查景道杀人时一模一样——他怕,怕梁化之连他也“处理”,更怕半夜有人用辐条敲他脑壳。恐惧这玩意儿,比共产党更不讲理。 查景道没拿后半根金条。他出西门,老槐树被炮火烧成黑棍,树下挖了个坑,坑里埋着半截骨头,不知是谁。他把辐条插进土里,转身奔太行山,后来有人传说他参加了解放军,也有人说他折在半路,被阎锡山残兵黑吃黑。真相没人追问,就像那十具尸体,草草扔进枯井,填土夯实,上面盖了座新厕所,屎尿一冲,恩怨归零。 我爷爷当年是太原师范的学生,被抓去陪绑,眼瞅着同学被湿纸一层层糊脸。他晚年才开口:“那时候,人比纸薄,血比酒贱。杀手替我们报仇?不,他只是换了个法子,让血继续流。”爷爷说完就灌一口汾酒,酒辣得他直咳嗽,咳得像要把肺咳出来。我那时小,只觉解气;长大才懂,所谓“以暴制暴”,不过是把刀子从左手递到右手,伤口还是那张伤口,结不了痂。 今天翻旧档,看到那张泛黄的《太原日报》,标题赫赫:“匪特夜袭,十烈士殉国”。我盯着报纸,耳边却响起查景道那句话——“下辈子别当狗”。可人和狗,到底谁先学会咬人?这个问题,报纸没答,历史也没答,只剩厕所墙上那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别信阎王殿,阎王也在逃难。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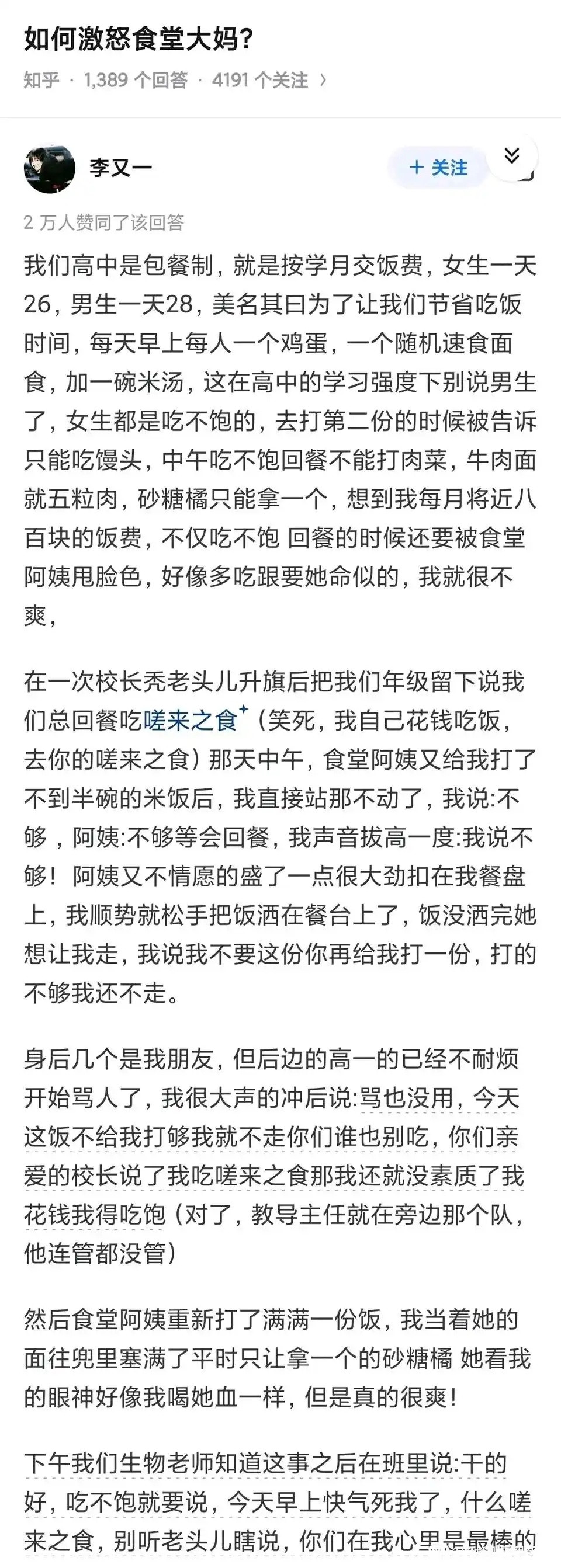







喵喵茶茶
写得有血有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