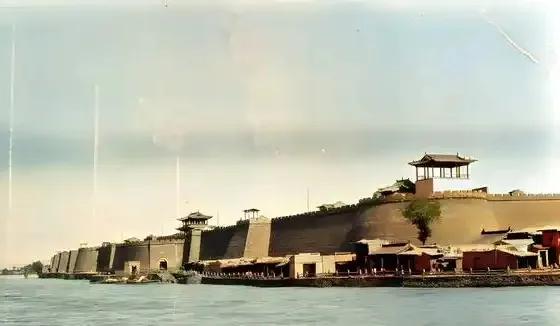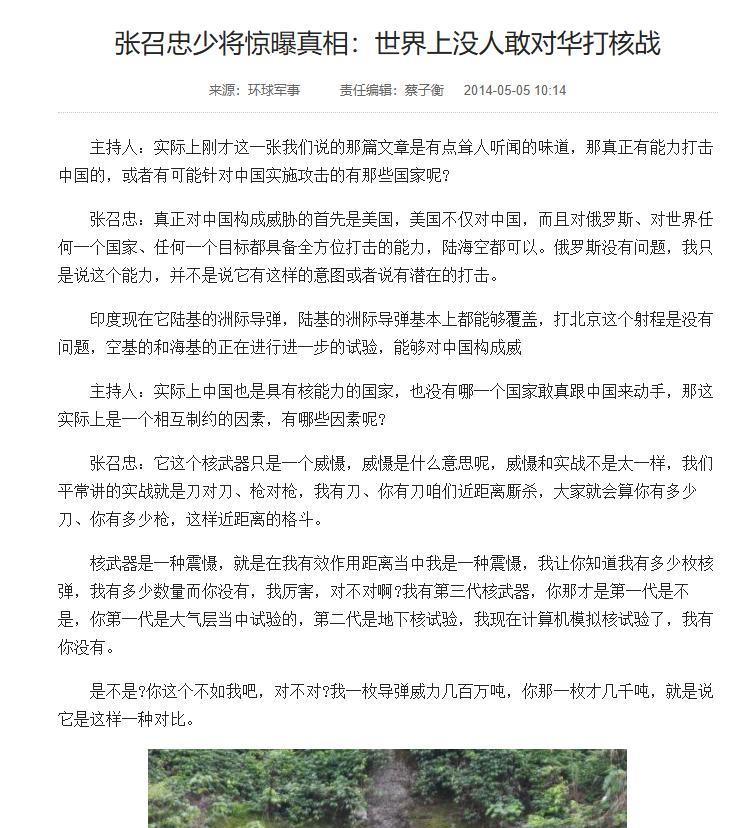1955年授衔时,毛主席看着名单,突然问道:吕俊生怎么没在里面?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名单都核对好了?吕俊生哪去了?”毛主席把那份厚厚的花名册扣在桌上,目光扫过在场人员。寂静里,一位组织局干部小声回答:“主席,吕俊生已批准复员,所以未列入。” 这一问,在会议室里炸开了锅。熟悉晋冀鲁豫战史的人都明白,“军中吕布”缺席,多少显得突兀。追溯往昔,吕俊生的名号最早流传在太行山区——提到白刃战,几乎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 1907年腊月,他出生在直隶邢台一个石匠家庭,兄弟姐妹七个,一碗玉米糊要分成八份。幼年讨饭,青年扛工,日子像磨盘一样碾人心智。偏偏他膂力惊人,十七岁进了当地武馆,当杂役却偷着练拳。馆主看他悟性高,索性免了学费,让他吃住在馆里。几年下来,枪棒拳脚样样通。 1937年深秋,日军过紫金关时放火烧庄子,他提着一把破大刀冲进人群。那天,他没能救下村口老汉,却在废墟旁默念:终究要找个能打鬼子的去处。同年冬,他翻山越岭跑到山西沁源,找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报名。登记员问:“识字吗?”答:“不会写,但能打。”一句实诚话,换来一张军装。 连队第一次小规模伏击发生在沁河畔。枪声刚起,他不听号令就扑到最前,四刀劈翻两名兵,旁人看得头皮发麻。排长事后批评:“冲得再快,再少个脑袋也不够换。”他嘿嘿一笑,掰着指头说:“多练几下就习惯。”这股不要命的劲儿,很快在师部挂了号。 到了百团大战,高邑一带的碉堡群卡住了运输线。夜色里,他带五兵,抱半筐手榴弹摸过去。枪林弹雨中,他扔进第一颗“闷雷”,轰然巨响后,碉堡口冒出火舌。他探身进去,甩开大刀连劈带砍,等主力冲到时,里面只剩一片狼藉。这场硬仗干净利落,指挥所直接记他一等功。自此,“军中吕布”传遍太行。 1943年,他在磁县一次反“扫荡”中被子弹擦穿肺叶,失血晕死。大夫出舱口拦住警卫员:“再晚半小时就回天乏术。”醒来后,他靠在担架上,还吼着要上火线。组织上硬把他调到后方休整兼任军械员。他闷闷不乐,整天抱着炸药包练拆装,嘴里念叨:“身子能好就还得回去。” 抗战胜利那年,他已是连长。随军整编时,部队统计:八次一等功,两次大功,无一次请功皆属实。有人打趣:“你该去当干部学校教刺杀。”他摆手:“写字太费劲,让我练枪倒快活。” 1949年国庆阅兵筹备,华北野战军选英雄模范进京观礼。他踏上火车,第一次看见天安门。10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与会代表。主席伸手握他胳膊,说:“你就是那个把碉堡掀了的吕俊生吧,好!”一句“好”仿佛又在耳边回响。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分到河北军区培训大队担任近战教员,然而旧伤频繁出血,让他举枪都打颤。1953年,他向组织递交复员申请,理由只有两条:身体不听使唤;家乡缺壮劳力要修水渠。军区多次挽留未果,1954年冬,他正式脱下军装。 因此,1955年授衔制度启动时,档案处把他列入“已复员优秀干部”栏。毛主席那句追问并非不知内情,而是不愿让一位战斗英雄被遗忘。工作人员当即回应:“待典礼结束,把相关情况专报,另行研究待遇。” 后来,人事部门给他补发了三级离休证,每月津贴三十六元,还附带“模范连长”金质奖章一枚。老兵们常去他家串门,聊起当年,吕俊生把勋章塞进抽屉,拍拍桌面:“别提那些虚头巴脑,还是说说村里今年麦子咋样。”语气轻,却掩不住骨子里的傲气。 他回乡后带头投工建水渠,一百多米的岩层硬是凿通。旁人问他图什么,他说:“修渠和炸碉堡是一个理儿——让庄稼长出来,让人活下去。”话简单,却管用。 1978年,他病危,县里把他送进医院。护士给他翻身时,看到后背纵横的弹痕,忍不住吸气。吕俊生睁眼笑:“疤是过去留下的,疼不疼都过去了。”11月4日凌晨,这位“军中吕布”停止呼吸,终年七十一岁。 有人统计,他总共参加大小战斗两百余次,亲手击倒敌人九十六名,带队俘虏三百多人,立功次数在原129师排前三。数字冰冷,却足够说明分量。更重要的是,他让后辈明白:勋章可以放抽屉,担当却得扛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