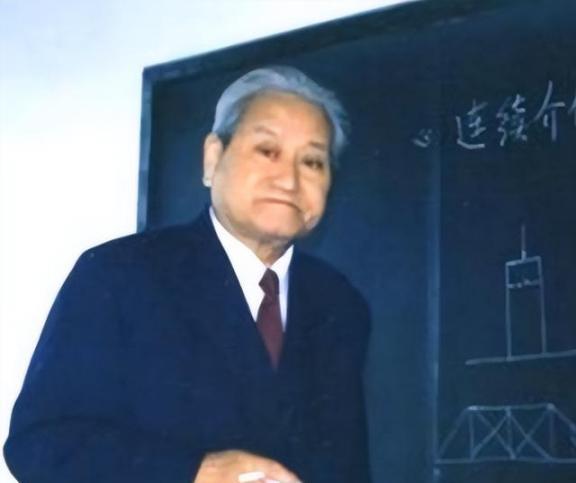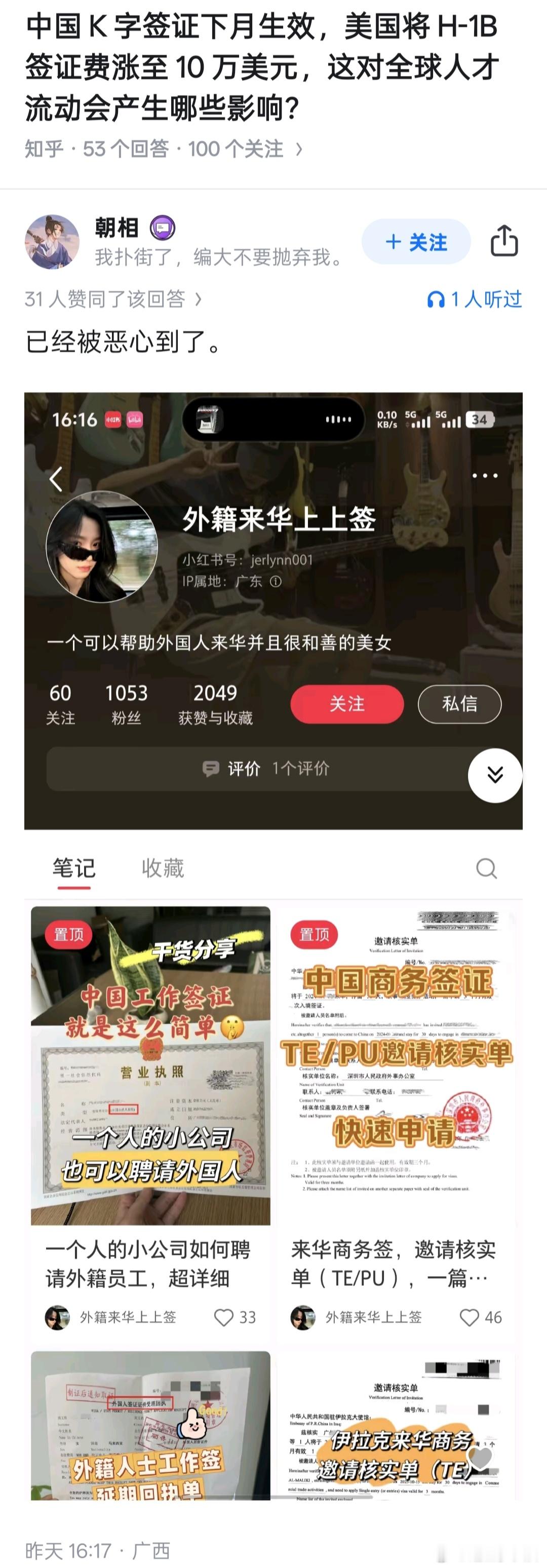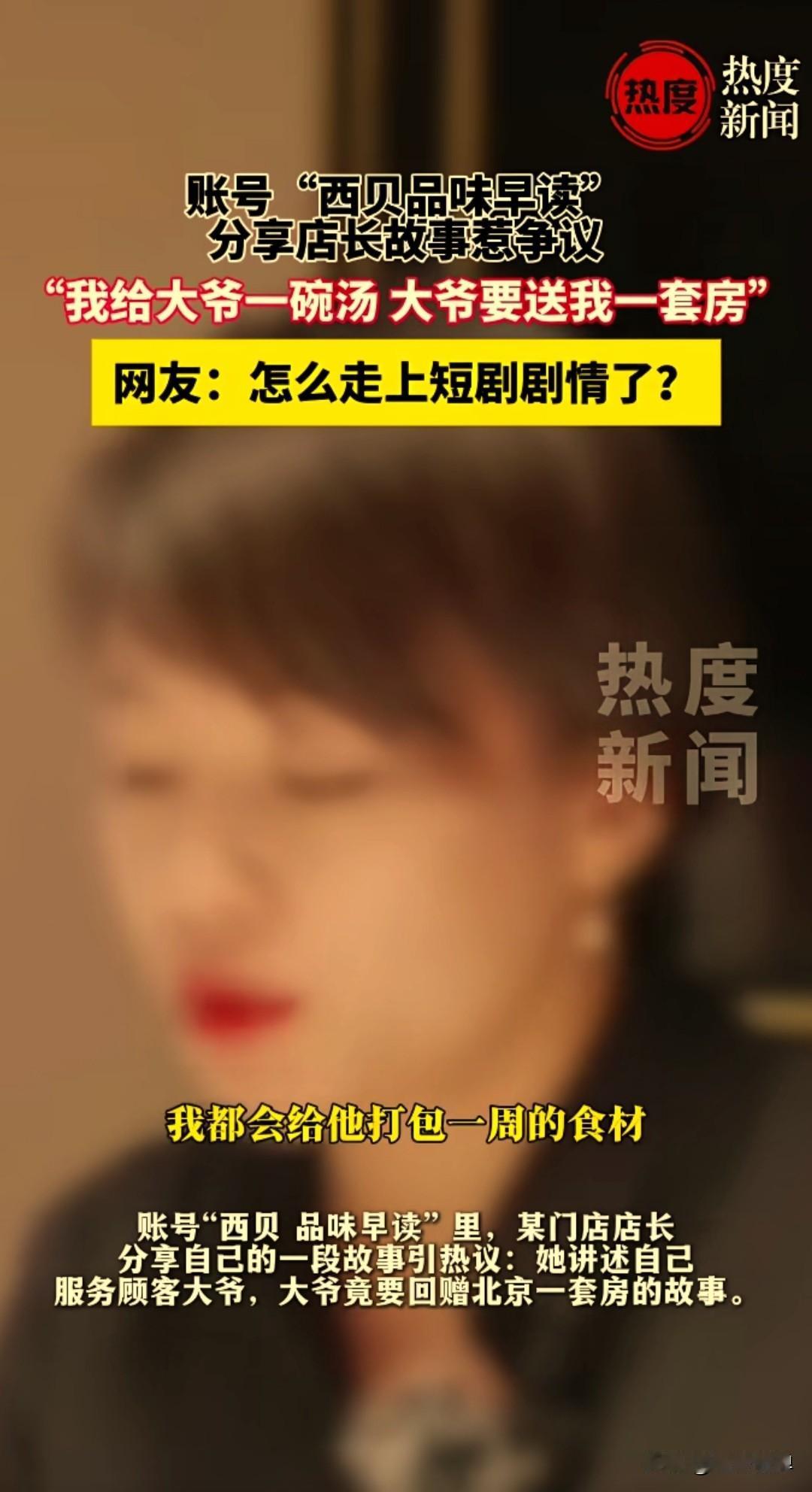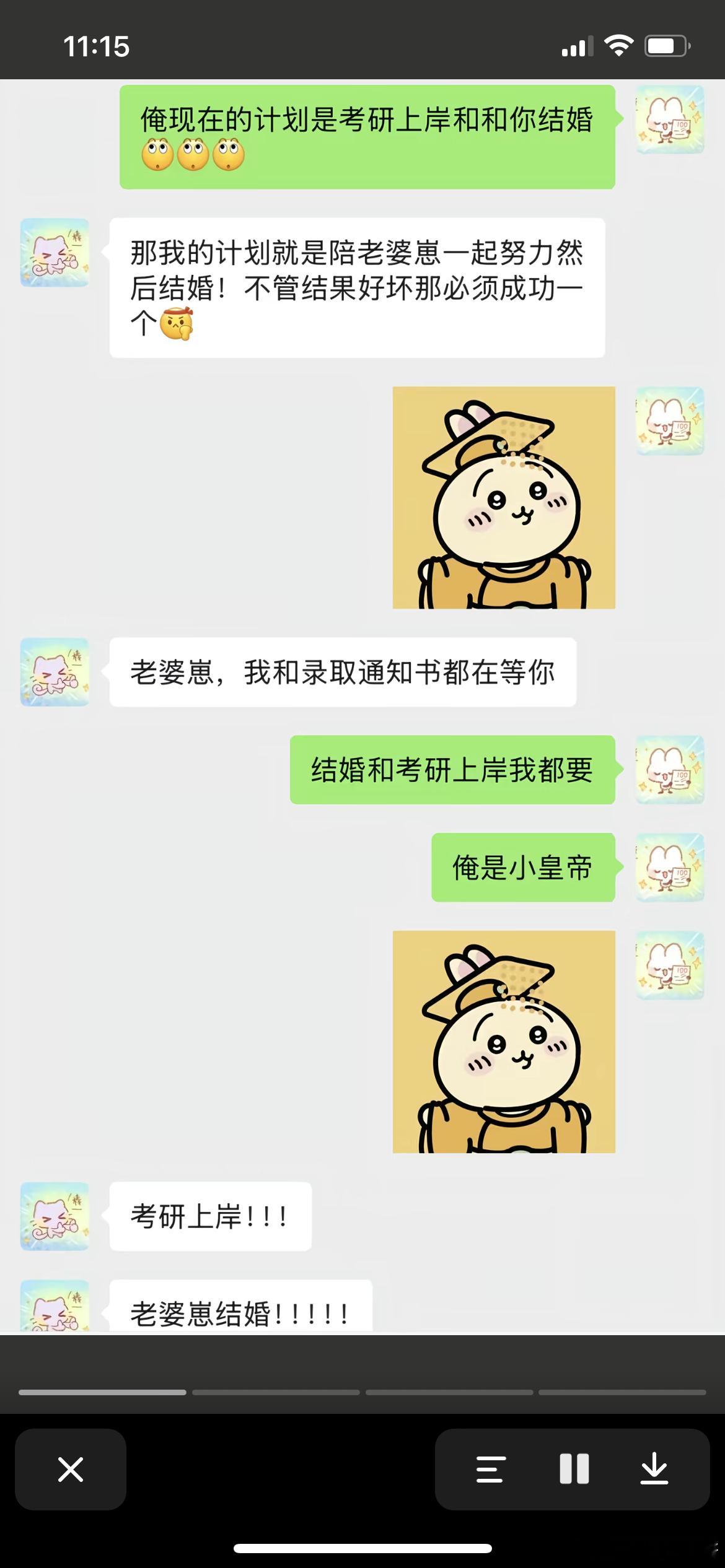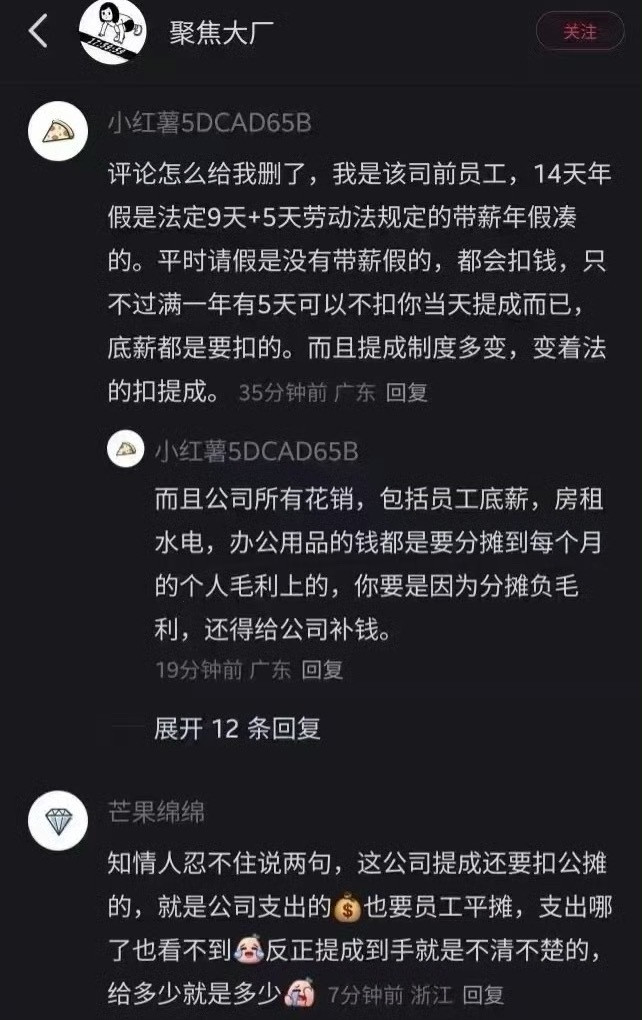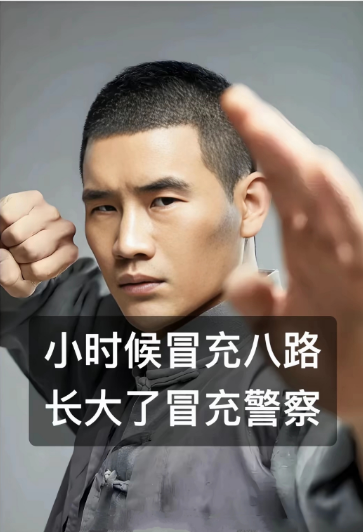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正加速起跑,可跟着出现的麻烦也不小,长江中下游年年闹洪水,电力紧缺制约了发展,重庆等上游城市因航道不畅交通受阻,长江流域的发展像堵了口的河水。 那时候的气氛是真紧,国家需要一个能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大动作,于是三峡大坝被推上台面。 当时的社会意见简直针锋相对,支持者说,这是“全国版的定心丸”,既能发电补上庞大的电力缺口,还能拦洪水、保平安,让长江变成真正的通海大动脉。 反对者则担心超级工程“过于冒险”,可能留下比收益更大的后遗症,黄万里就是其中最醒目的声音。 他认定长江泥沙量巨大,一旦在库区沉积,早晚得堵出事,下游河道抬高后防洪功能要打折扣,加上几百万移民、生态断裂,这笔账怎么算都不是“稳赚”。 可站在国家层面,难题同样摆在眼前,长江暴涨不是小范围灾害,而是动辄波及几千万人的生死安危,一次大水就可能摧毁一个城市。 光靠分散的小水库或堤坝,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而那时中东部电力缺口巨大,缺清洁能源来支撑工业化和城市化。 如果能有个集中发力的巨型工程,在较短时间里,把防洪、电力、航运这三座大山一起压下去,看起来这是最可行的方案。 于是在两条路线,“分散小规模治理”与“集中大工程”的较量中,后者赢了。 2003年,大坝逐步上阵,曾经的设想和担忧,开始在实践中一一对照,洪水来了,大坝通过提前空库、拦蓄洪峰,下游从武汉到九江少了灾难性损失。 发电上,三峡成了世界第一的水电站,每年送出千亿度的电,电费早早就回本,航运上,万吨级船直接开到重庆,让长江真正成了黄金水道,运输成本大减,带火了沿江经济带。 但伴随收获的,自然也有成本,泥沙沉积确实存在,只是因为上游修了梯级电站、加上植树造林,量比原来少了不少,而大坝本身的排沙设计也在起作用,所以暂时没闹大乱子。 但这并不是解决,只是动态调控中维持平衡,更让人头疼的是生态,洄游鱼类断了路,长江里的江豚生存更艰难,库区还出现过富营养化。 百万移民从搬迁到安家,生活虽然改善不少,但那份对故土的割裂感,始终无法弥补。 三峡的意义早已超越它本身,集中治理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可能留下长久的负担。 分散灵活的手段虽然微小,却能起到长远的补充,如何把两者结合,或许才是三峡真正留给后人的考题。 【信源:中国经济周刊——当年反对建三峡的那些“预言”应验了吗?我们为什么需要三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