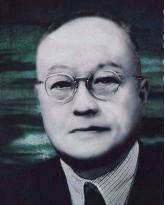1949年6月,国军师长黄振涛劝吉星文起义,吉星文说:“我是不会参与的,但老兄大可放心,出卖朋友的事我也不会干的。” 1949年6月,独立360师师部,一场命运的密谈,在沉默中展开。 黄振涛进屋时,连招呼都没打,反手把门闩死,动作利落得像在前线冲锋。 他满头汗,军装上沾着些灰,鞋边是干裂的泥巴,额角的青筋还没退下去。 他没坐,就站在那,喘了两口气,直奔主题:“老吉,再等半个月,解放军就要过江了。你想过下一步怎么走没有?” 吉星文没回答,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磨破的军靴,眉头动了动,像是从什么漫长的回忆里被拽回来。他没说话,气氛一下子冷下来。 其实他不是不知道形势。 补给已经断了整整八天,伙食糙得连糙米里都掺了沙子。 前天,三营的兵开始挖野菜,连长被他骂了一通,可心里知道,骂也没用。 士兵们瘦得脸都塌了,眼神跟野狗一样。他让副官封锁消息,就怕底下的人先乱了。 “你们部队的情况,我都知道。”黄振涛看着他,压低声音,“我们更惨,昨天还有兵为了偷红薯被老百姓追着打。 几个营长已经联名表态,要起义。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一句,要不要一起走这一步?” 吉星文抬起头,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眼神不怒不喜:“你疯了?” 黄振涛摇头:“我没疯,是清醒。咱们打了这么多年仗,真不知道现在为了啥了。 上头已经不管我们了,蒋介石忙着往台湾运金条,咱们还在这守着个鬼地方。 你说,这仗还打得下去?” 他掏出一封信,展开给吉星文看,是营长们的签字。吉星文扫了一眼,没接,也没说话。 “解放军那边,我已经联系上了。”黄振涛继续说,“他们答应了,起义可以既往不咎,愿意留的编入正规部队,不愿意的发路费回家,总之,能活着。” 说到这,屋里静了一阵,静得能听见窗外旗杆上的国旗“哗啦啦”地抖。 那面旗,边角已经磨破,风一吹,飘也飘不起来。 吉星文终于开口:“当年打淞沪,会战的时候,咱们一连死了九成,我是踩着尸体回来的。 那时候我发过誓,效忠党国,保家卫国。现在你让我转头去投敌,我做不到。” 黄振涛还想劝:“你是为弟兄们想想,他们跟着你不是为了死的。” 他摇头,脸色平静:“我这条命,是党国给的。哪怕现在党国不管我了,我也不能变节。 转身就像抽自己耳光,我这脸还要不要?” 沉默。 黄振涛收起那封联名信,缓了口气,语气放软:“我知道你是这个人,但我还是得来。 弟兄们都想活,我也得给他们找条活路。你不愿走,我不怪你。” 走到门口前,吉星文突然开口:“你今天说的这些,我就当没听见。 你要是真想走那条路,赶紧行动,别在我这儿待太久,夜长梦多。” “放心。”黄振涛点头,“我走了。将来……你要是走投无路了,来找我,我还认你这个朋友。” 门开了,风灌进来。黄振涛背影一下子被光吞了进去,脚步声很沉。 直到他走后半个小时,吉星文都没动。 他靠在椅子上,闭着眼,脑子乱成一团。他不是没想过起义,也不是不知道局势。 可他过不了自己那道坎。他觉得一旦背叛,整个人就不再是“吉星文”了。 可问题来了,部下怎么办?他们还能撑几天?他是师长,是全师的顶梁柱。 弟兄们跟着他吃沙子、挖野菜,他这个“顶梁柱”撑得住吗? 说到底,他不是不心软,只是认死理。 后来有人说,吉星文就是拉不下面子,其实不是。 他心里清楚得很,自己这条路,大概率是死路。可就是有人,哪怕知道前面是悬崖,也会选择往前走。 他没出卖黄振涛。 这点,很多年后被人提起时,大家都觉得意外。 那年头,谁都自顾不暇,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哪还讲什么“义气”。 可他就保住了。黄振涛从他这儿走出去,没人知道他来过,更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就像那天从头到尾,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后来怎么样? 黄振涛起义成功,被编入人民解放军,部下大多得以保命。 有人回家种地,有人继续带兵,活了下来。 吉星文呢?部队最后被解放军包围,他没投降,率部突围,伤重被俘。 有人说他死在战俘营,有人说他晚年在广西一个小镇当了个粮站保管员,没人能证实。 但有一点是真的——他没背叛,也没出卖朋友。 那年六月,两个老兵在一间闷热的屋子里,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一条可能是活路,一条,注定走不远。但那一刻,他们谁都没有后悔。 这世上最难的,是在大势已去的时候,还能守住一份底线。 吉星文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