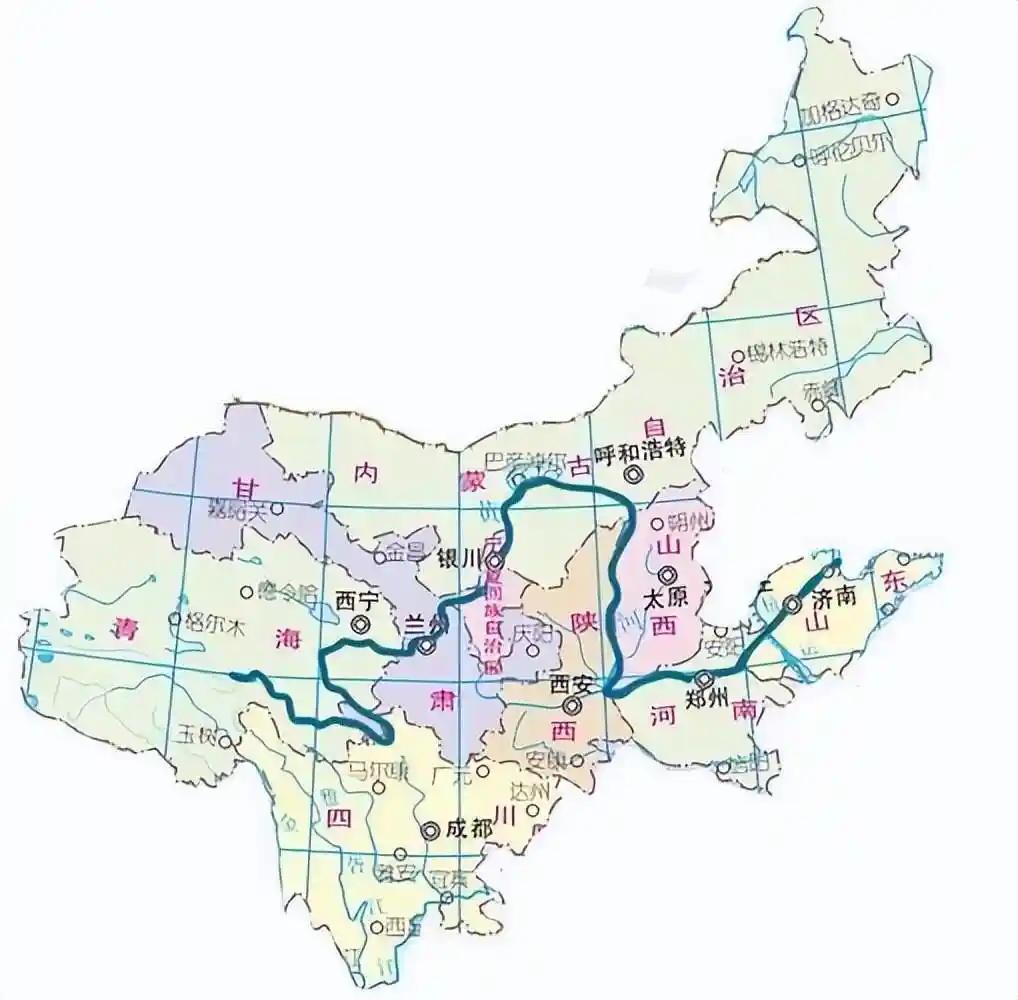1676年,康熙在黄河边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给了他一张烧饼。不料,乞丐不仅不要烧饼,还口出狂言:“半个时辰后,你桌上的菜都是我的,谁还差这张烧饼。” 这年康熙二十出头,正借南巡勘察黄河水情,岸边帐篷里确实刚备下六七个菜。但一个乞丐敢说这话,不是疯癫就是找死。 康熙按住侍卫,打量着乞丐,反倒来了兴致。他蹲下身来,看着乞丐正在地上画歪歪扭扭的河图:“你倒是说说看,菜怎么就是你的?!” 那乞丐也不客气,树枝在沙地上划得唰唰响:“您看这儿,上游三十里有个急弯,河水冲到这岸,把泥沙都带过来了。再看下游,河床比去年这时候高了整整三尺。”他说得激动,破袖子往河面一指,“这帐篷扎的地方,看着平坦,可底下都是新淤的软沙。待会儿风从芦苇荡那边过来,保准把帐篷连根拔起,那时饭菜可不都是我的了……” 康熙眯起眼,心里暗暗吃惊。这些细节,连他带来的治河官员都没注意到。眼前这个衣衫破烂的乞丐,倒把黄河水情摸得门儿清。 “你叫什么名字?”康熙问道。 “陈潢。”乞丐抹了把脸,露出被泥垢遮盖的轮廓,“浙江钱塘人,在黄河边转了七八年了。” 就在这时,河面上突然起了风。先是微风,转眼就成了呼呼作响的大风,卷起漫天黄沙。帐篷开始剧烈摇晃,侍卫们慌忙去拉绳索。果然如陈潢所说,不过片刻工夫,帐篷一角就被掀了起来,桌上的菜碟哗啦啦摔了一地。 康熙站在风沙里,看着满地狼藉,突然哈哈大笑:“好你个陈潢,真有你的!来,跟我进帐——换个结实的帐篷,咱们好好聊聊。” 新搭的帐篷里,康熙让人重新备了酒菜。陈潢也不推辞,洗了手就坐下,吃相虽急却不失礼节。几口热菜下肚,他苍白的脸上才有了血色。 “说说看,”康熙给他斟了杯酒,“你怎么对黄河这么了解?” 陈潢放下筷子,眼神变得专注:“皇上,黄河不是书本上的死物,它是活的。您得天天在河边走,看它春天怎么涨水,夏天怎么奔腾,秋天怎么沉淀,冬天怎么结冰。我在河岸上睡过几百个夜晚,听着水声入眠,才知道它的脾气。” 他越说越激动,干脆用手指蘸了酒,在桌上画起来:“治河不能光堵不疏。现在各地官员就知道加固堤坝,可河床越来越高,这不是长久之计。得学大禹,该疏通的疏通,该分流的分流。上游多种树固土,中游开凿引河,下游拓宽入海口......” 康熙听得入神,不时点头。这些话,他在朝堂上从未听人说得如此透彻。 “那你觉得,现在最要紧的是做什么?”康熙追问。 “清淤!”陈潢斩钉截铁,“从开封到徐州这一段,河床已经高出地面了。再不清理,明年汛期必出大事。” 帐外,黄河的咆哮声隐约可闻。康熙沉思良久,突然问道:“陈潢,朕若给你个官做,让你专门治理黄河,你可愿意?” 陈潢愣住了,手里的酒杯微微颤抖。他望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年轻几岁的皇帝,眼圈突然红了。 “皇上,”他声音有些哽咽,“我陈潢在黄河边漂泊这些年,见过太多百姓流离失所。若能治河,我不要官职,只求一个机会,让沿岸百姓不再受水患之苦。” 康熙站起身,走到帐门前,望着夜色中奔腾的黄河。这条养育了中华文明的大河,也是一条时刻悬在百姓头上的利剑。 “好,”康熙转身,目光坚定,“朕就命你为河道总督府参议,专司治河。你要什么人、多少钱粮,直接向朕禀报。” 陈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个在风浪面前从不低头的汉子,此刻却泪流满面:“臣,定不负皇上所托!” 从此,黄河边上少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多了一个日夜奔波的治河能臣。陈潢的身影出现在每一个险工段,亲自测量水深,设计堤坝。他发明的“测水法”,能精准预测水位变化;他主持开挖的引河,分泄了汛期的巨大压力。 有人说,经常看到陈潢深夜还在河堤上巡查,破旧的官服上沾满泥浆。每当汛期来临,他总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抢险,仿佛又变回了那个在风沙中与黄河较劲的乞丐。 而康熙每次南巡,必定要召见陈潢,听他说治河的进展。君臣二人常常在黄河边一站就是半天,对着奔腾的河水指指点点。 有一年汛期,黄河险情频发,陈潢连续三个月守在堤上。当洪峰安全通过的消息传来时,他累得直接瘫坐在泥水里,却笑得像个孩子。 随从要扶他回去休息,他摆摆手:“我得看着它平安入海才行。这条河啊,就像个倔脾气的孩子,你得时时盯着,一刻不能松懈。” 夕阳西下,黄河水映着金光,奔流不息。陈潢站在堤岸上,身影被拉得很长。从乞丐到治河名臣,他的人生因一张烧饼而改变,而千千万万黄河沿岸的百姓,也因他的坚守而得以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