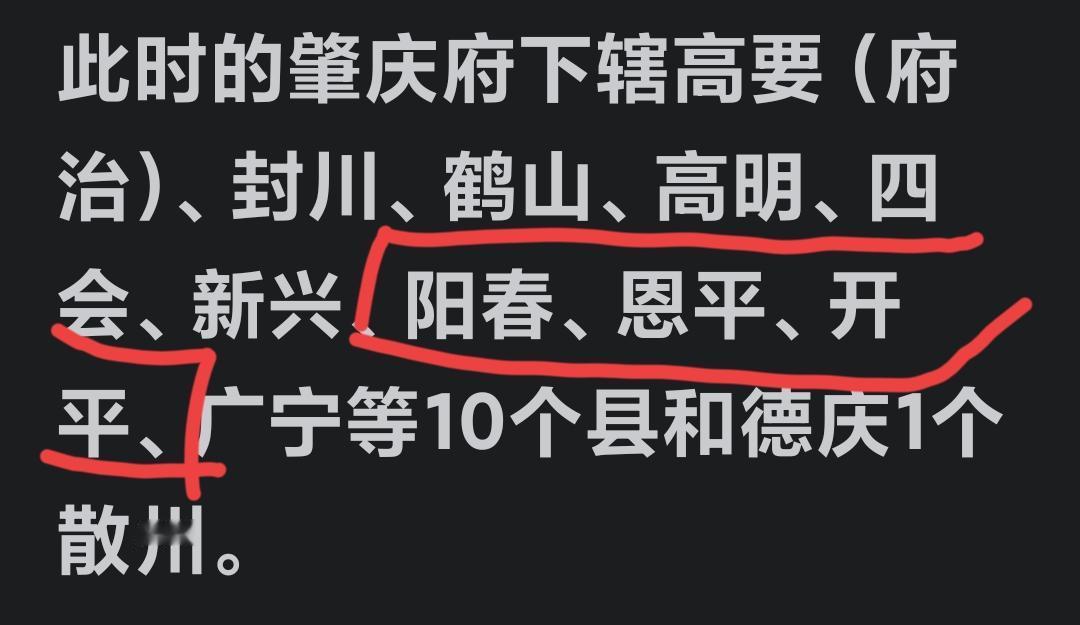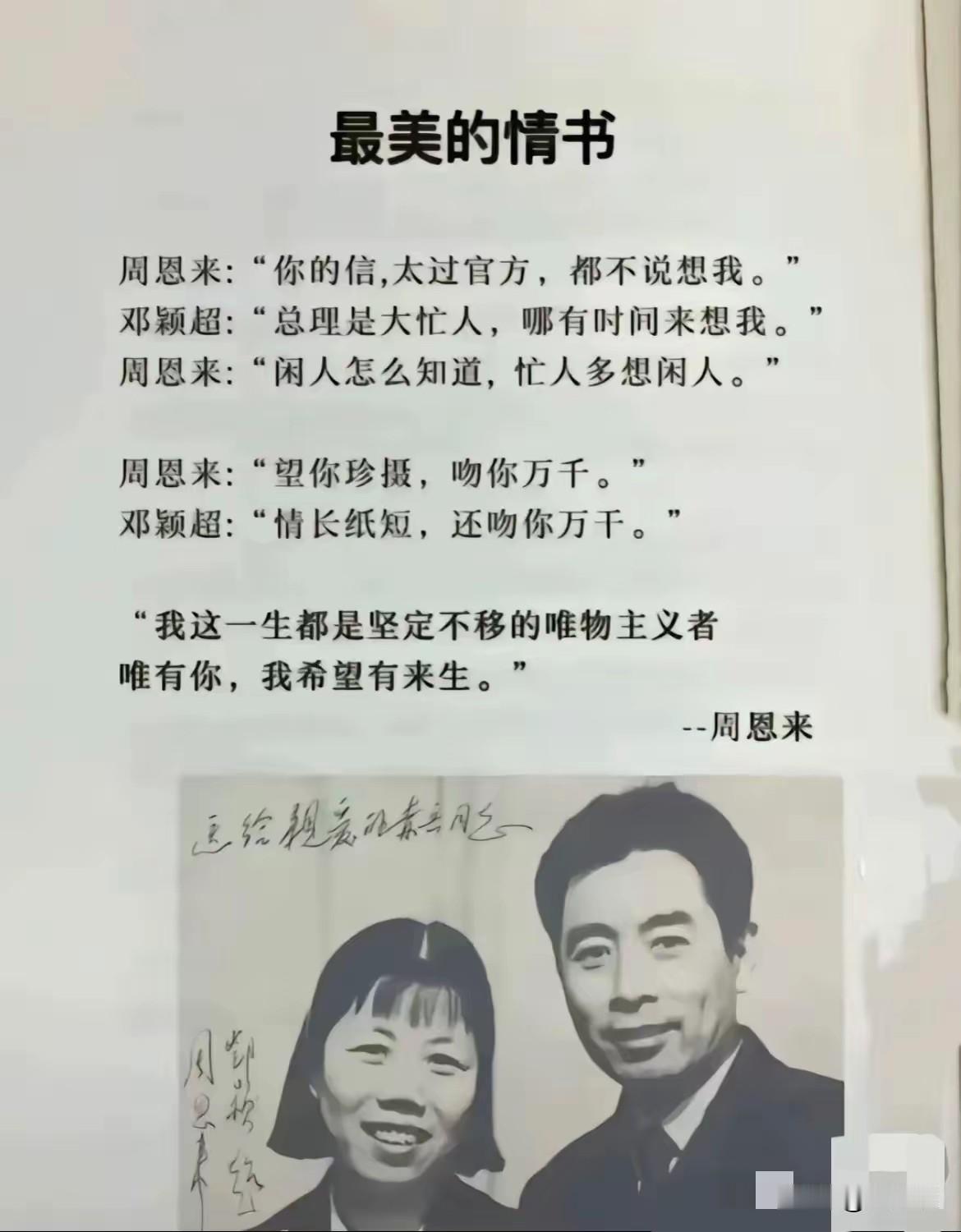1959年,88岁高龄的顾维钧,趁着正牌老婆黄蕙兰睡着,就跟做贼似的,偷偷摸摸溜进了另一个女人严幼韵的房间。 他哪能想到,自己的老婆压根就没睡,而是悄没声地跟在了他后头。 1959 年纽约公寓深夜,地毯吸走了顾维钧的脚步声。 88 岁的他扶着墙,踮脚溜向二楼严幼韵的房间,睡衣领口还歪着。 身后主卧的门轻轻开了道缝,黄蕙兰攥着黄铜热水壶,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她早摸清了丈夫的规律 —— 每到严幼韵来住,他总说 “去谈旧事”,实则另有盘算。 楼梯转角传来牌桌笑闹声,黄蕙兰深吸一口气,一步步跟了上去。 这三人的纠葛,早在三十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1920 年布鲁塞尔,顾维钧还是驻英公使,在宴会上遇见黄蕙兰。 她是印尼糖业大亨黄仲涵的女儿,穿巴黎定制礼服,开口就是流利的英、法、荷语。 彼时顾维钧刚丧第二任妻子,急需财力支撑外交场面 —— 黄蕙兰的出现,像及时雨。 婚后她用自家钱修缮使馆,办舞会宴请欧洲政要,顾维钧的 “外交明星” 形象,离不开她的铺垫。 而严幼韵走进顾维钧的生活,是在二十年后的马尼拉。 1942 年,她的丈夫杨光泩(顾维钧下属,驻菲总领事)被日军杀害。 寡居的她带着三个女儿,在战后辗转到纽约,第一时间投靠了顾维钧。 那时顾维钧正任驻美大使,黄蕙兰忙着在社交圈应酬,两人的婚姻早已没了当初的热络。 严幼韵懂心理学,会来事,常帮顾维钧整理外交文件,陪他聊往事 —— 这份 “贴心”,是黄蕙兰没有的。 黄蕙兰早就察觉了不对劲。 她从小过惯奢华日子,吃饭用银餐具,出门要带两个仆人,花钱大手大脚。 顾维钧虽靠她的钱撑场面,却私下嫌她 “俗”,说她 “只懂珠宝,不懂外交”。 有次严幼韵来家里帮忙,黄蕙兰故意把她调去联合国礼宾司工作,想隔开两人。 可严幼韵下班后还是来,顾维钧更是主动开车接她,两人在车里聊的时间,比跟黄蕙兰独处还长。 婚姻的裂痕,从那时起就再也补不上了。 回到那个深夜的楼梯口,牌桌的笑闹声越来越清晰。 黄蕙兰听见严幼韵说 “顾公使牌技还是这么好”,接着是顾维钧的笑声 —— 那是她多年没听过的轻松。 她猛地推开门,热水壶里的水还冒着热气,径直泼向顾维钧的头。 “烫!” 他跳起来,眼镜滑到鼻尖,牌桌上的人全僵住了。 黄蕙兰盯着他湿透的睡衣,声音发颤:“你不是说谈旧事吗?这就是你谈的旧事?” 顾维钧的反应,比黄蕙兰预想的更冷淡。 他没辩解,只是让佣人拿毛巾,对吓傻的严幼韵说 “没事,你继续玩”。 后来他对朋友说:“我和蕙兰早没感情了,她只认钱,幼韵懂我。” 这话传到黄蕙兰耳朵里,她反倒笑了 —— 当年若不是她的钱,他哪能在巴黎和会挺直腰杆拒签和约? 1919 年巴黎和会,顾维钧那句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成了外交史上的经典。 可没人提,那次会议后,是黄蕙兰买通记者,把他的发言译成多国文字,传遍欧洲。 泼水事件后,两人的婚姻彻底摊牌。 黄蕙兰搬出了住了三十多年的公寓,带走了她的珠宝和银餐具。 离婚时顾维钧提出 “补偿十万美金”,她当场拒绝:“我黄仲涵的女儿,不缺这点钱。” 她后来在演讲里说:“我帮他建起外交门面,最后却成了他眼里的‘门面包袱’。” 而顾维钧没等多久,就在同年娶了严幼韵,婚礼只请了十几个亲友,连婚纱都是严幼韵自己挑的。 那时顾维钧已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休,转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严幼韵成了他的 “生活秘书”,帮他整理案卷,订机票。 婚后的顾维钧,倒真过上了安稳日子。 1967 年顾维钧从国际法院退休,97 岁去世前的十八年里,身边一直是严幼韵。 而黄蕙兰离婚后没再嫁,靠演讲谋生。 1992 年她在纽约去世,享年 103 岁。 严幼韵的寿命更长,活到了 2017 年,112 岁。 顾维钧死后,她继承了财产,常捐钱给华人社团,还资助了几个外交史研究项目。 有人问她和顾维钧的感情,她只说:“他需要人陪的时候,我刚好在。” 三人的子女后来都在美国定居,顾维钧和黄蕙兰的两个儿子做了商人,严幼韵的女儿成了律师。 他们很少提父辈的这段往事。 如今纽约那栋公寓早已换了主人,可关于那个深夜的泼水事件,仍在外交史爱好者口中流传。 有人说黄蕙兰 “太刚烈”,有人说顾维钧 “薄情”,也有人说严幼韵 “精明”。 可没人能真正说清,这段横跨半个世纪的纠葛里,有多少是利益算计,又有多少是晚年的孤独渴望。 就像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的:“外交是妥协的艺术,婚姻或许也是 —— 可惜我到晚年才懂,却已没了妥协的机会。” 来源:《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黄蕙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