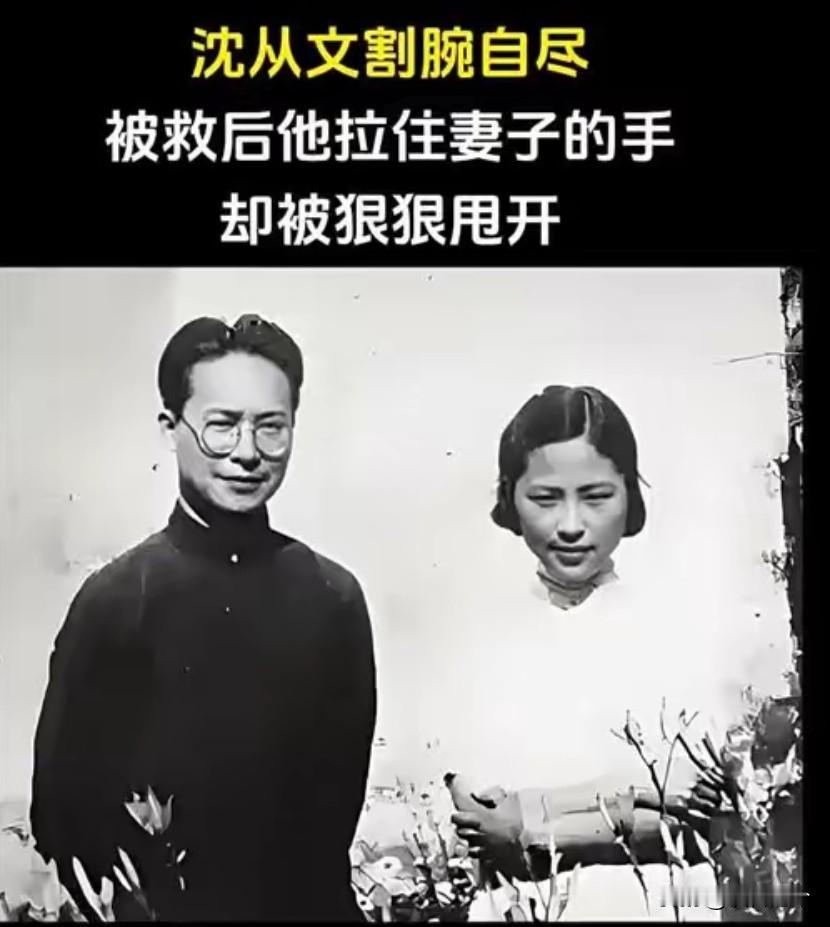1949年,沈从文喝下煤油割腕自尽,被救下后,他想拉妻子的手,妻子张兆和却甩开了。后来他被转入精神病院,妻子也没去看他一眼。弥留之际,沈从文对妻子说:“三姐,是我对不起你……” 这儿得说清楚,“三姐”不是别人,正是张兆和。她出身合肥名门张家,家里四个女儿按排行依次是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她排第三,连叶圣陶都称赞的“张家四才女”里,她就是那位“三小姐”。沈从文在家男子中排第二,写信时总落款“二哥”,对应着就叫她“三姐”,这称呼从追求时一直用到老,藏着俩人最初的牵绊 。 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这一年里其实自杀了两次。第一次是长子沈龙朱撞见他伸手摸电源插头,慌得一把拔掉电源,还把父亲蹬开才救下来。第二次更决绝,他反锁房门,用刀片割了手腕和颈上血管,还喝了煤油,堂弟破窗而入时,屋里已经鲜血四溅。这哪是一时想不开,分明是被彻底逼垮了。 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是郭沫若1948年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直接骂他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桃红色”作家,这话被北大学生抄在大字报上,贴得校园里到处都是。他在北大教小说史,以前课堂挤得满当当,那会儿学生们都在聊新思潮,没人再听他讲《边城》里的湘西人情,甚至有人直接站起来说他的东西“不合时宜”。一个把文字当命的人,突然被定性为“反动”,连笔都不敢拿了,那种绝望没法说。 张兆和甩开他的手,真不是铁石心肠。她后来回忆说,当时全家都觉得沈从文“落后、拖后腿”,一家子被搅得乱糟糟的。那会儿她自己还在华北大学二部学习,一边要顾着学业,一边要带两个儿子沈龙朱、沈虎雏,根本没时间消化丈夫的崩溃。次子沈虎雏后来也说,当时大家都觉得社会在欢天喜地变样,父亲的苦闷“没道理”,甚至觉得“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那个年代的人,哪懂什么抑郁症,只当是他钻了牛角尖。 没去精神病院探望,藏着太多时代的无奈。张兆和不是不想去,是真的分身乏术。她要上课,要管孩子,根本抽不出三个多小时往返西郊的医院。更关键的是,当时整个家庭都被沈从文的“问题”笼罩着,连亲友都觉得他“不正常”,她要是频繁往精神病院跑,不光自己受影响,孩子们将来的前途都可能受牵连。她后来整理沈从文手稿时,看到他那时写的日记:“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才懂他当时有多孤独。 要知道,当年沈从文追求“三姐”张兆和时,可是写了四年上千封情书的。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当老师,18岁的张兆和是外语系的才女,追求者能排成长队,起初根本看不上这个“土气”的老师,还拿着情书找校长胡适告状。可沈从文偏不放弃,信里写“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最后愣是靠这份执着打动了她,1933年成了婚。只是谁也没想到,曾经炽热的情书,后来会变成柴米油盐里的沉默与隔阂。 沈从文后来好转后,没怪过张兆和。他彻底放下了笔,转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每天在午门城楼上转来转去,冬天零下十几度也不能烤火,只能揣着手讲解文物。老友萧乾陪外宾去故宫,看见他拿着讲解棍认真解说的样子,躲得远远的不敢打招呼,怕伤他自尊。他倒挺坦然,只是偶尔会跟张兆和说,当年是自己太自私,没顾着家里。 弥留之际那句“三姐,是我对不起你”,藏了一辈子的愧疚。他愧疚自己当年的冲动让全家蒙羞,愧疚没能给她安稳日子,更愧疚自己让那个曾经被他用千封情书追到的姑娘,跟着受了半辈子委屈。张兆和晚年整理那些情书和遗稿,才真正懂了他一生的重压,她后来坦言“不完全理解他,直到整理遗稿才明白”,这份迟来的理解,成了俩人婚姻最沉重的注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