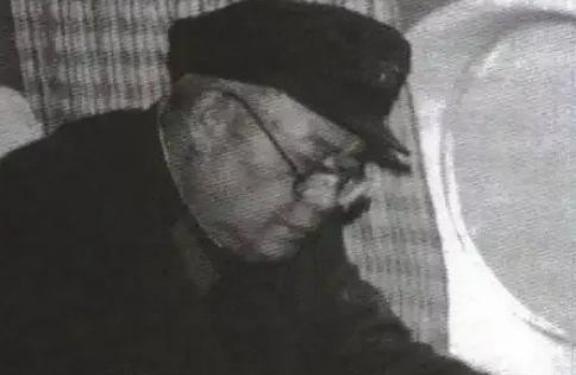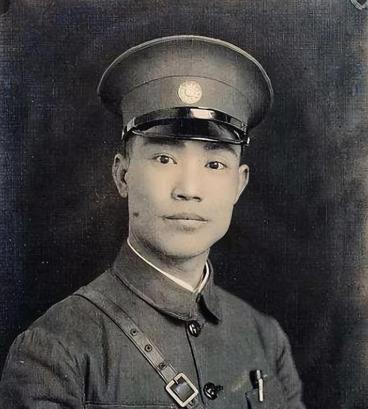1979年,已经恢复工作的杨尚昆心里,总悬着一件事。他要找一个人,一个只知道名字叫田政红的士兵。除此之外,部队番号、籍贯、年龄,一概不知。他交代下去,必须找到这个人,活要见人。 为什么要找一个普通的士兵?这事儿,得从1966年的冬天说起。 那一年,杨尚昆被错误地关押审查。他被单独囚禁,与外界彻底隔绝。身体上的折磨还在其次,精神上的压力几乎将他击垮。 更要命的是,他有严重的老毛病——低血糖。在那种缺医少食的环境里,这病随时能夺走他的命。 一旦发作,他会立刻感到天旋地转,浑身冒冷汗,四肢无力,眼前阵阵发黑,离休克只有一步之遥。 负责看守他的,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士兵。 他们纪律严明,不与看押对象说一句话,脸上总是带着冰冷的严肃。 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只是一个需要严格看管的“对象”。 但其中有个叫田政红的士兵,有点不一样。 他来自山西农村,心思朴实。他注意到,这个老干部有时候会突然扶着墙,脸色变得像纸一样白,嘴唇发紫,身体不停地发抖。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病,但他看得出,这人快不行了。 当时的规定非常严格,私下接触审查对象,轻则受处分,重则可能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 田政红心里很纠结,帮,还是不帮?帮了,自己前途未卜;不帮,一条人命可能就在眼前没了。 一个深夜,杨尚昆的低血糖又犯了,他蜷缩在冰冷的床板上,感觉自己这次可能真的挺不过去了。 就在他意识快要模糊的时候,他听到一阵极轻的脚步声。 田政红在巡查时,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到了杨尚昆痛苦的样子。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快步走了过去。 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飞快地塞进杨尚昆冰冷的手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快,吃了它,别让人看见。” 说完,他立刻转身回到岗位,像一尊雕塑一样站着,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杨尚昆用尽最后的力气打开纸包,里面是一撮白糖。在那个年代,糖是精贵东西,对普通士兵来说更是难得。 他顾不上多想,赶紧抓了一把放进嘴里。一股甜味瞬间在口中化开,随即化作一股热流,慢慢流遍全身。 他原本冰冷的身体开始回暖,神志也渐渐清晰起来。 他缓过一口气,抬头想看清那个士兵的脸,记住他的样子,可田政红始终没有回头。 就是这包糖,把杨尚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第二天,杨尚昆想找机会感谢他,但田政红一直目不斜视,完全不给他机会。 后来,杨尚昆在士兵们偶尔的交谈中,听到了这个名字——田政红。 他把这个名字,连同那包糖的恩情,一起刻在了心里。 时间一晃到了1978年底,杨尚昆恢复了所有职务。 回到领导岗位,千头万绪的工作等着他,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寒夜里递给他一包糖的年轻人。 他把秘书叫来,郑重地交代了任务:找到田政红,我要当面感谢他。 可问题来了,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全国叫田政红的人不知有多少,十几年过去,他肯定早就退伍还乡了。 唯一的线索,就是他曾在北京当过兵。 寻找工作就这么开始了。工作人员先是从当年的卫戍部队档案查起,一沓沓泛黄的退伍军人名册被翻开,一个个人名被筛选比对。 几年过去了,信发出去了无数封,也派人跑了好几个省,但得到的消息都是“查无此人”或者“不是你要找的人”。 眼看线索越来越少,连负责寻找的人都觉得希望渺茫。 但杨尚昆没有放弃,他隔段时间就会问起:“田政红找到了吗?”这句话,像一个无声的鞭策。 这场寻找,从197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6年,整整七年。 就在大家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一封来自山西阳泉的信件回复说,当地矿务局有一个叫田政红的工人,年龄和参军经历似乎对得上。调查人员立刻赶往阳泉。 在矿区的家属院里,他们见到了田政红。当年的年轻士兵,已经成了一个皮肤黝黑、两鬓斑白的中年汉子。 经过多方信息核对,最终确认,他就是杨尚昆要找的那个恩人。 消息传回北京,杨尚昆非常激动,立刻安排人将田政红接到北京的住所。 时隔二十年,两人再次相见。一个已是国家领导人,一个仍是普通工人。 杨尚昆一见他,就紧紧握住他那双粗糙的手,眼眶湿润了: “田政红同志,我找了你七年啊!你还记得那包糖吗?当年要不是你,我这条老命早没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田政红被这阵仗弄得手足无措,脸涨得通红,只是一个劲儿地说: “首长,您言重了,我真不记得了……那就是一件小事,谁碰上都会那么做的。” 一包糖,在绝境中是救命的甘霖;一句感谢,跨越了二十年的风雨和七年的寻找。 善良不问大小,感恩不分早晚,这便是人性中最温暖、最有力量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