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28日,段永平突然宣布要离开小霸王,老板陈健仁笑着给他办了欢送酒会,还送了一辆奔驰,却让他保证1年内绝不跟小霸王竞争。这场欢送会看似宾主尽欢,背后却是一场中国企业史上最经典的决裂与重生。 二十八岁的段永平孤身闯进怡华集团旗下那个亏着两百多万的烂摊子时,面前是积了厚灰的机器和根本理不清的账本。 仅仅三年,他就硬生生把这个名叫日华的小厂子改造成了日后大名鼎鼎的小霸王。 靠的是什么?就是一股要把“打工”变“伙计”的心气儿。 那会儿广告可是实打实地砸了四十万进去,黄金时段一播,全国家长一边嘴硬说买来学习,一边给孩子掏钱买快乐。 销售额像是坐火箭一样,愣是从零飙到了几亿元的量级,甚至一度压过了当时的IBM和联想。 早年间,集团那边画的大饼那是相当诱人,“三七开”分股说得信誓旦旦,后来不声不响缩成“二八”,再后来变成“一九”。 这数字变戏法似的缩水也就罢了,关键是那满车间的工人连夜倒班、段永平在烟灰缸里按灭无数个烟头换回来的真金白银,转头就被上面抽走去填其他窟窿。 到了1994年,段永平那一纸股份制改革方案递上去,本想着让跟着自己熬通宵、跑市场的一帮兄弟能有点真正的盼头,结果被上面冷冰冰一句“不搞”给堵了回来。 那时候他就明白,这已经不是赚多少钱的事了,是一个没有契约精神的环境,就像那是永远也兑现不了的“空头支票”。 所以那一天的离职才显得那么平静却又震耳欲聋。 他跟老板陈健仁那个“君子协定”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收下一辆奔驰车当个念想,换来的是一年内不在国内搞对抗,承诺只带走那几个最贴身的核心骨干。 这场面体面得甚至有点反常,可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切割。 当时车间外头那一双双红着的眼睛,和那些从头到尾不吭声的老员工,其实心里都明镜似的:主心骨走了,这魂儿也就散了。 那几个跟着他走出厂门的人,谁能想到日后就是这几颗种子,长成了把持中国手机半壁江山的参天大树? 陈明永、沈炜这些人,当年也不过是在小黑屋里跟他一起改方案、吃泡面的战友。 一江之隔的东莞,步步高随后拔地而起,这次没有什么模糊的“三七开”,一来就是明明白白的股权激励。 虽然小霸王还想照葫芦画瓢,继续打广告、铺货,可没了那口气,节奏全乱了套。 反倒是东莞那边,新的商业帝国正按照那个男人最初设想的透明规则疯长。 经销商也是人精,这头观望一下,那头就已经有人拎着现金去东莞排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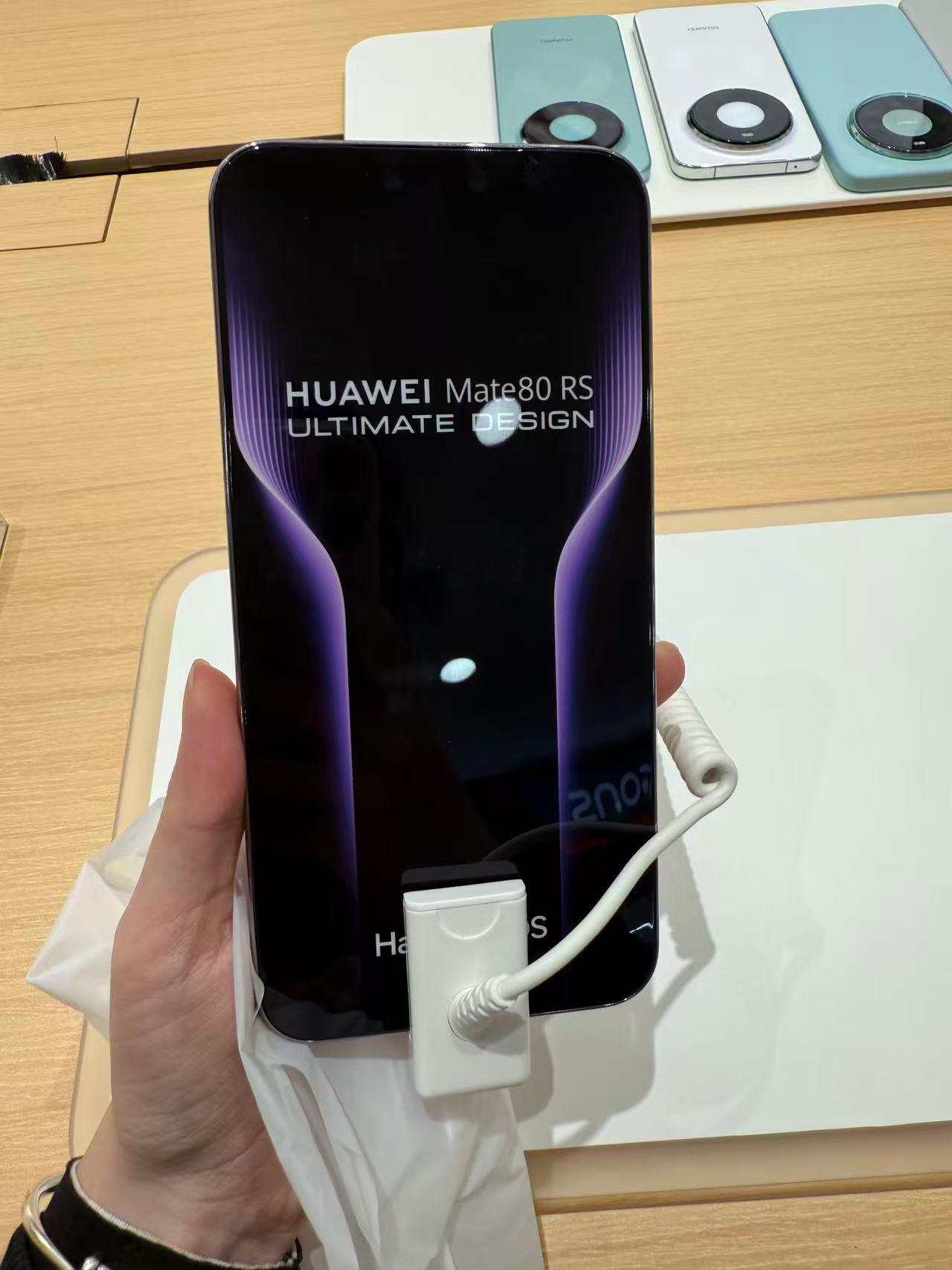
![杜姐:又整这死出[doge]这招就是和王楚钦的场上密谋。杜凯琹和搭档被他俩层出不](http://image.uczzd.cn/7741449590501654537.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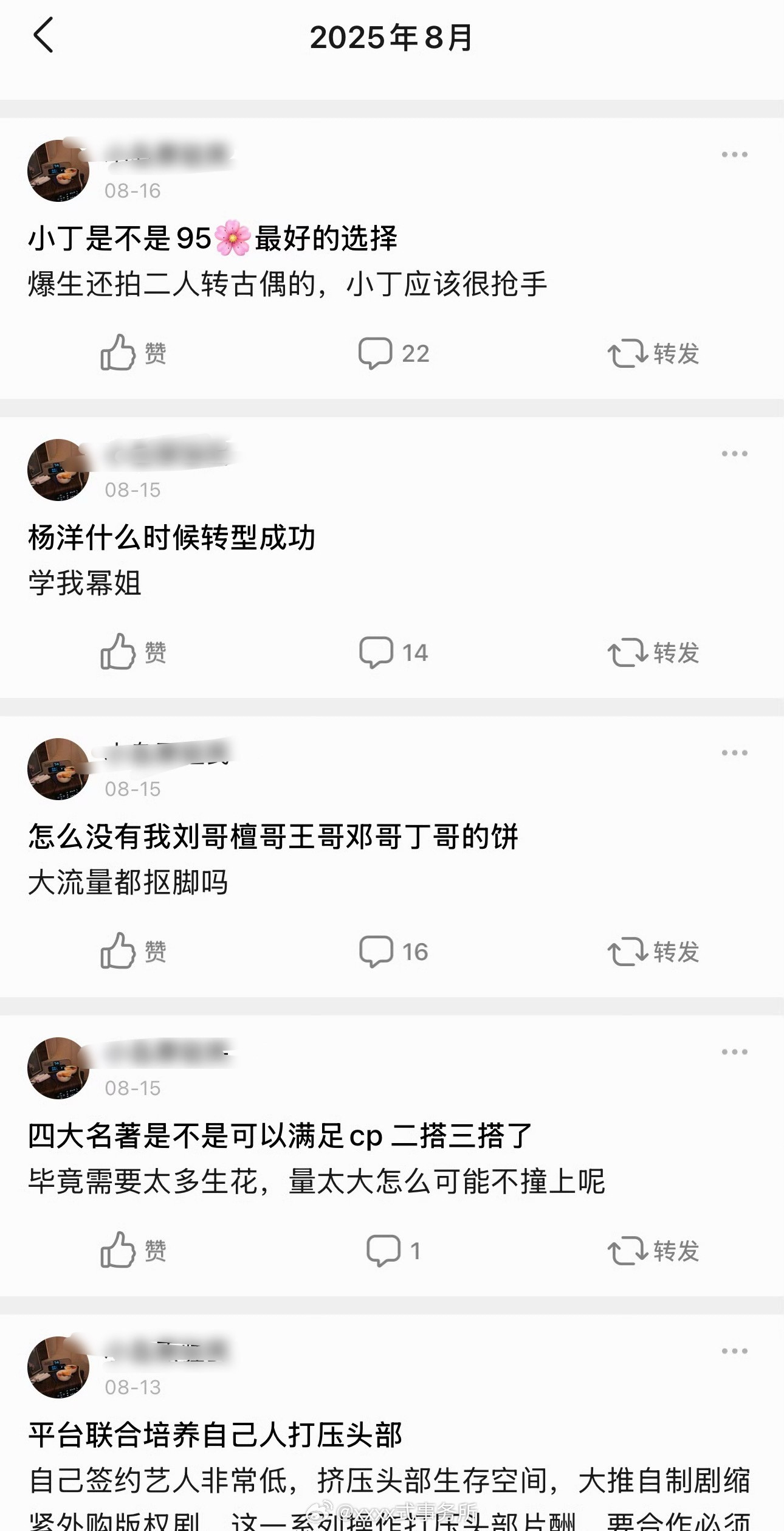




![已经渐渐地有了将军的步伐![赞]](http://image.uczzd.cn/1131820347958213082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