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滕西远私藏两支手枪,民警让他上交,可他却说:“这两支枪,一支是粟裕大将给我的,一支是开国中将给我的,你们要哪支?” 1996年的山东枣庄,秋阳晒得院子里的玉米棒子金灿灿的。滕西远蹲在门槛上,手里摩挲着个铁皮盒子,盒子上的红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斑斑锈迹。院门外传来摩托车的声音,他抬头一看,两个穿警服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帽檐下的眼睛透着严肃。 “滕大爷,我们是派出所的,来跟您说个事。”年轻民警掏出工作证,“最近开展枪支清查,您家里要是有老物件儿,特别是枪支,按规定得上交统一保管。” 滕西远没起身,指了指院里的小马扎:“坐。”他慢悠悠地打开铁皮盒子,里面垫着块褪色的红绸布,两支老式手枪躺在里面,枪身磨得发亮,却保养得干干净净。 民警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枪。左边那支枪管略短,枪柄上刻着模糊的花纹;右边那支更长些,枪身上还有个小小的凹痕。 “大爷,这枪……” “你们要哪支?”滕西远突然开口,声音有点哑,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这支,是粟裕大将给我的。”他拿起短枪管的那支,指尖在枪柄上轻轻敲了敲,“那支,是开国中将王必成送的。” 民警们愣住了。他们听过滕西远是老革命,却没想到他手里有这样的宝贝。 “1947年孟良崮战役,我是通讯兵。”滕西远的眼神飘向远处,像是落进了回忆里,“那会儿我才18,跟着粟司令在前线跑。有次送信,半道上遇见敌机轰炸,我把文件包死死压在身下,自己被弹片划了道口子。” 他卷起袖子,胳膊上一道长长的疤痕像条蚯蚓。“粟司令见了,从腰里把这枪摘下来给我,说‘小滕,拿着防身,文件比命金贵’。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自己用了三年的配枪。” 另一支枪的来历更惊心动魄。滕西远拿起那支长枪管的,指着枪身的凹痕:“这是王必成将军给的。1949年打上海,我在突击队,他是军长。总攻前夜,他把我叫到指挥部,说‘明天冲的时候,这支枪给你,能多带一个兄弟回来就多带一个’。这凹痕,是流弹崩的,当时离我心口就差一寸。” 两个民警听得入了神,手里的笔录本都忘了翻。 “这些年,我天天擦枪,就跟伺候老伙计似的。”滕西远把枪放回盒子,红绸布轻轻盖上去,“1955年转业,组织说枪得上交,王将军特意跟组织打招呼,说‘这枪跟着小滕立过功,让他留着作念想’。粟裕大将也说,‘是个好兵,留着吧’。” 他看着民警,眼睛里有点红:“不是我不交,是这枪不能交。它们不是铁疙瘩,是跟着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是老首长对咱当兵的信任。” 年轻民警挠了挠头,这情况他们没遇过。按规定,私藏枪支确实不合规,可这两支枪的来历,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沉。 “大爷,我们理解您的心情。”年纪稍长的民警斟酌着说,“但规定是死的,您看这样行不?我们向上级汇报,看看能不能特殊处理,比如由博物馆代管,标注清楚来历,让后人也能知道这些枪的故事。” 滕西远沉默了半晌,手指在铁皮盒盖上敲了敲。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响,像是在替他拿主意。“行。”他终于点头,“但得我亲自送去,我得跟它们告个别。” 后来,这两支枪被送进了枣庄革命纪念馆。展柜里,红绸布依然垫在下面,旁边的说明牌写着:“1947年粟裕同志赠滕西远同志,1949年王必成同志赠滕西远同志”。 滕西远去看过两次,每次都站在展柜前,一站就是俩小时。馆里的讲解员说,老爷子看着枪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比枪身还亮。 这事传到村里,有人说滕西远死脑筋,有人说他守着老物件不放。可他不在乎,只是每次跟孙子讲起过去的事,总会说:“枪是死的,人是活的。但老首长的情分,得记一辈子。” 就像那两支枪,虽然离开了他的铁皮盒,却把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把老一辈革命者的信任与嘱托,永远留在了看得见的地方。这大概就是滕西远最在乎的——不是枪能不能留在身边,而是那些故事,那些精神,不能被忘了。 (来源:大众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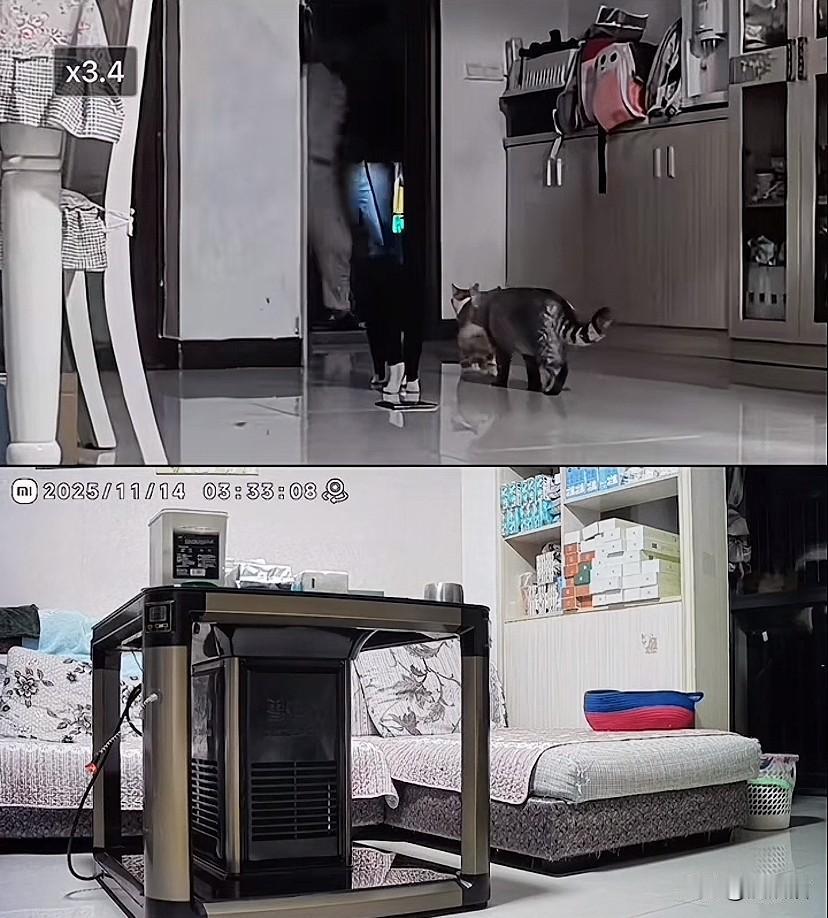
![七万骑兵?吴俊升一个师长能养的起十多万匹马?[吃瓜]](http://image.uczzd.cn/15213221908252555442.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