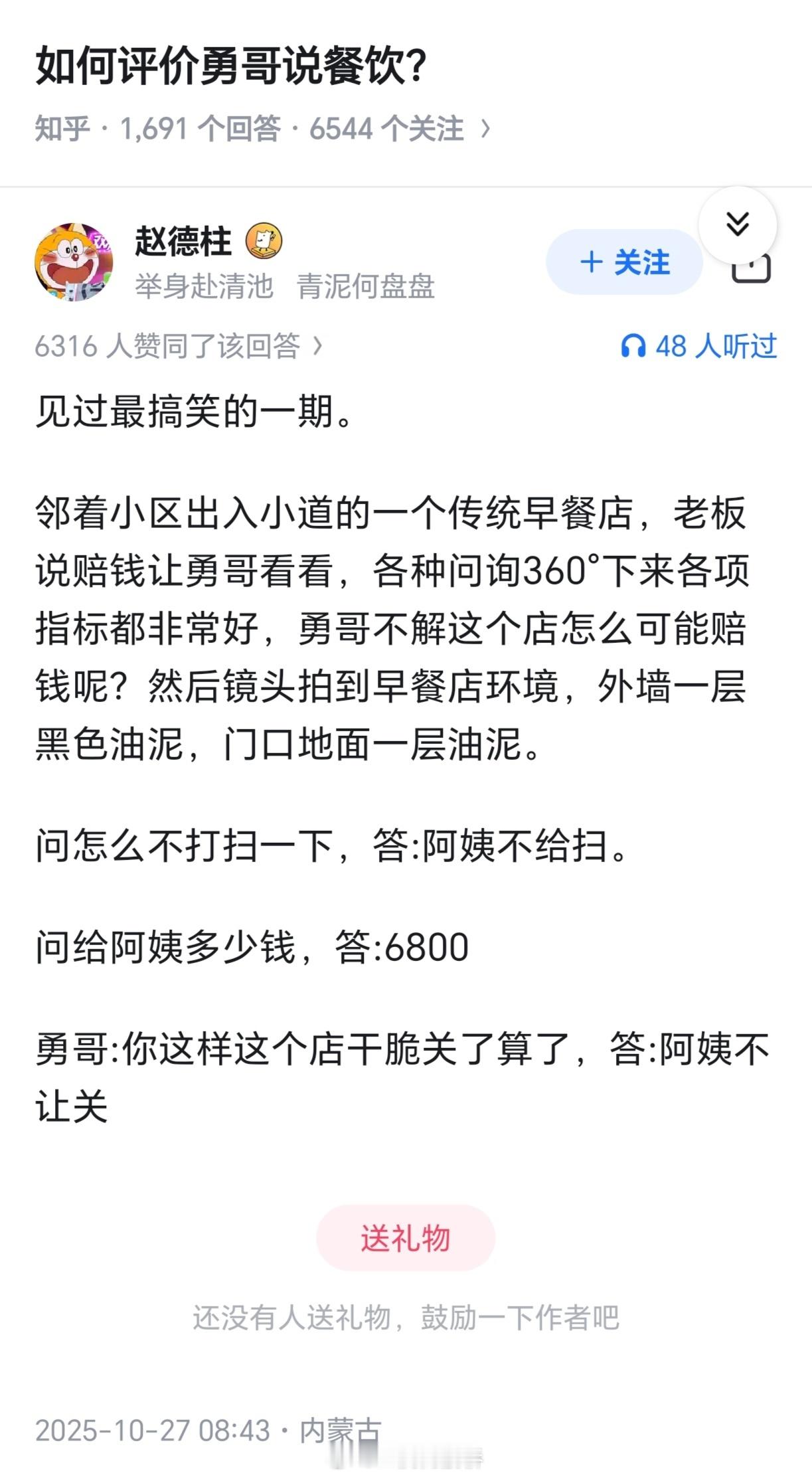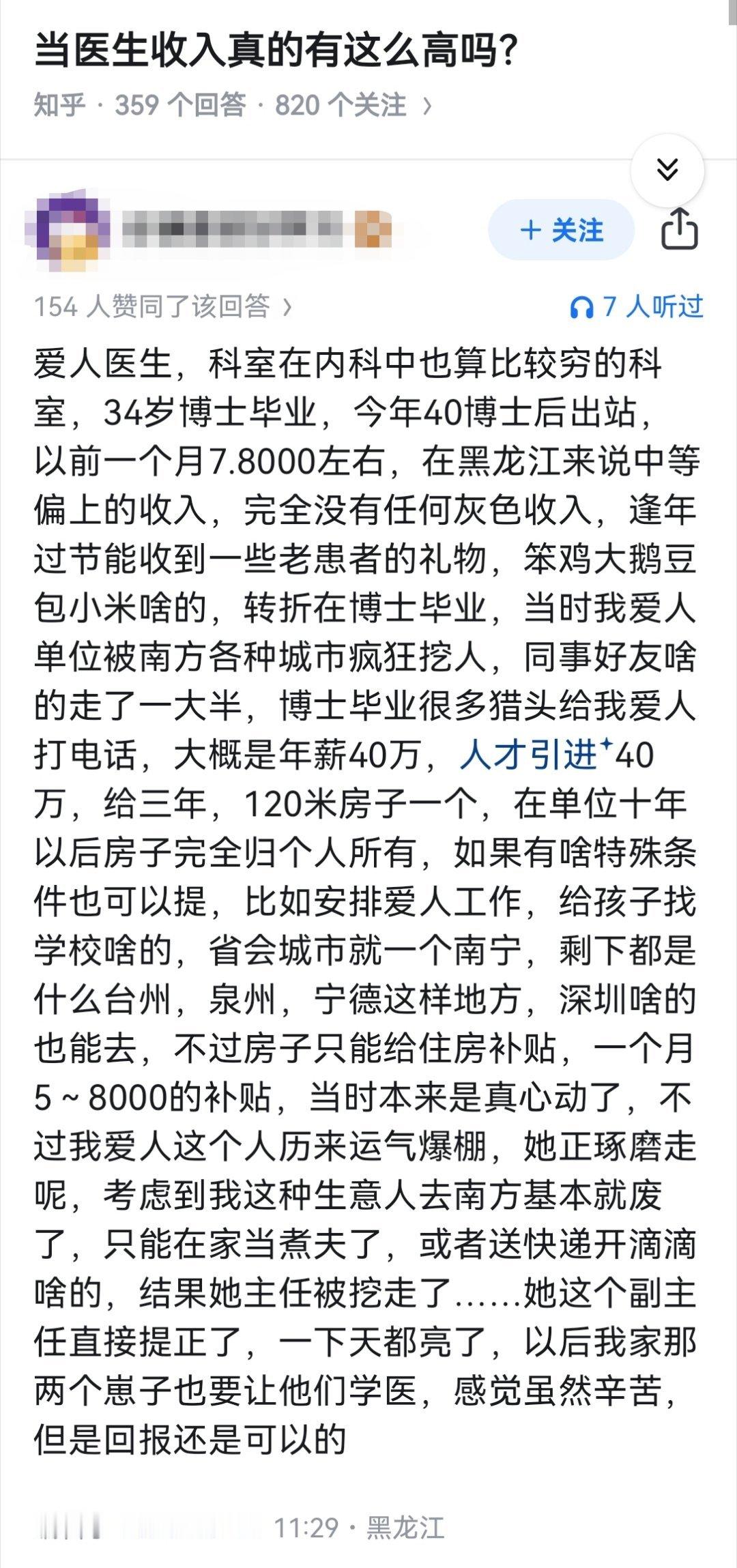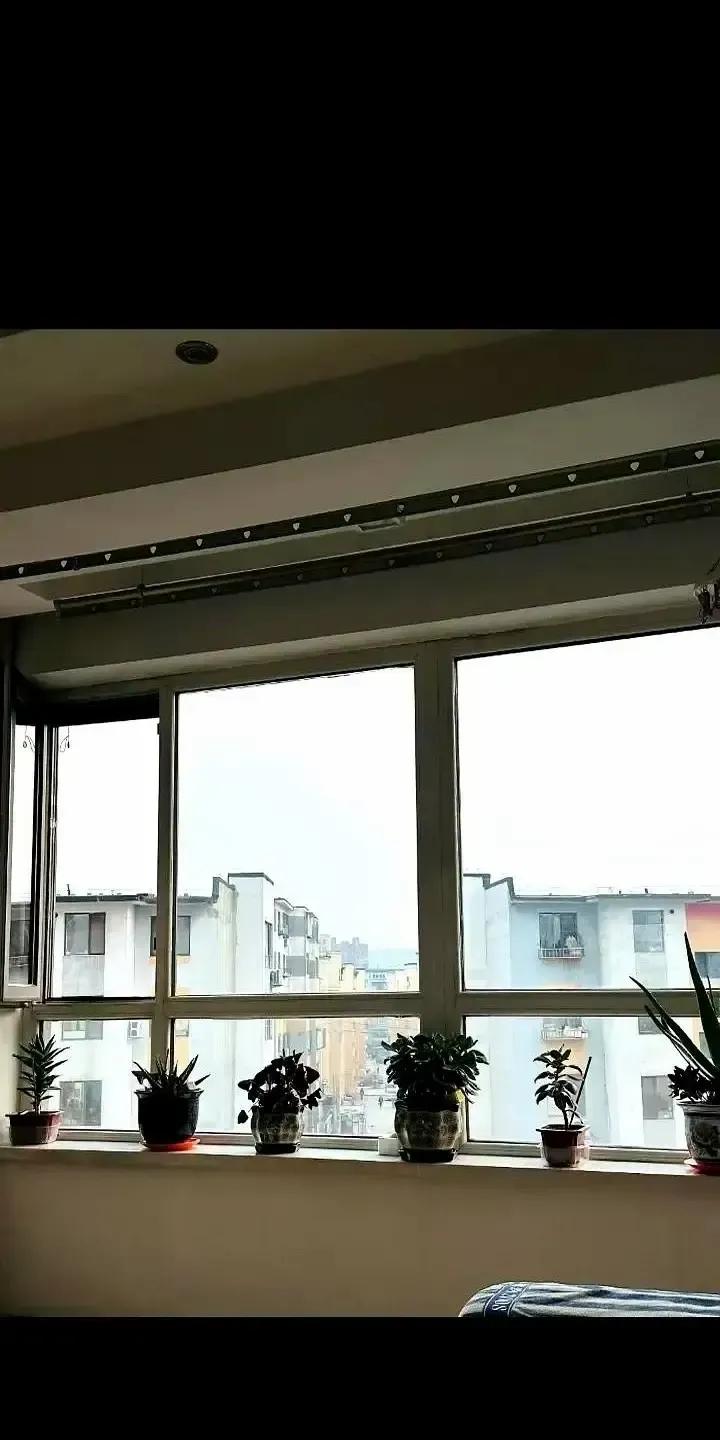医院退休老专家不在大医院坐诊,在小区开小诊所,不用机器检查,光把脉问几句就知病情。我也是偶然发现这家诊所的。去年冬天我儿子总咳嗽,在大医院查了胸片、验了血,说是支气管炎,吃了半个月药也没见好。那天接孩子放学,路过 3 号楼底商,看见挂着个 “李大夫诊所” 的木牌,玻璃门里摆着两张旧藤椅,不像别的诊所那样堆着各种仪器。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推门进去,里面坐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戴着老花镜正在写东西,听见动静抬头笑了笑,说 “坐吧,哪不舒服?” 去年冬天冷得早,我家小子咳得夜里睡不安稳,后脖子总贴着退热贴,黏糊糊的。 大医院跑了三趟,胸片拍了,血验了,报告单上“支气管炎”五个字印得清清楚楚,头孢、止咳糖浆吃了小半箱,咳嗽声还是像漏风的风箱。 接孩子放学那天,西北风刮得人脸疼,路过3号楼底商,玻璃门上“李大夫诊所”五个黑字被太阳照得有点晃眼,木牌边角磨得发亮,门里两张旧藤椅并排坐着,椅背上搭着件灰扑扑的羊毛坎肩——不像别处诊所,墙上挂满仪器显示屏,空气里都是消毒水混着塑料的味儿。 我拉着儿子的手在门口站了会儿,他小脸红通通的,还在小声咳。 推开门时,风铃叮铃响了一声,里头没开大灯,日光灯管悬在天花板中央,光淡淡的。 靠窗的木桌后坐着个老人,头发白得像冬天的霜,鼻梁上架着老花镜,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手里捏着支钢笔,正在泛黄的本子上写着什么。 听见动静,他抬头看过来,嘴角往下弯了弯,不是笑,是把皱纹挤开了些,说:“进来吧,孩子咳得紧?” 我把儿子往身前拉了拉,心里打鼓——大医院的机器都查不出根儿,他就靠问? 他没起身,指了指对面的藤椅:“坐。孩子多大?咳了几天?白天咳得厉害还是夜里?” 我挨着儿子坐下,藤椅“吱呀”响了一声,像在叹气。 他伸出手,手背皱得像核桃皮,手指却稳当,搭在孩子手腕上,眼睛半眯着,手指轻轻按了按,又换了另一只手。 这时候我才看见,他桌上没电脑,没打印机,就一个掉瓷的搪瓷缸子,里头插着几支铅笔,旁边堆着几本线装书,书页边缘卷得像浪花。 “晚上咳得厉害,”我插了句,“大医院说是支气管炎,药吃了半个月……” 他没接话,手指还在孩子手腕上停着,过了大概半分钟,才松开手,又看了看孩子的舌头,摸了摸他的后脖子。 “不是支气管炎,”他慢悠悠地说,声音像老茶壶倒茶,“是积食,火往上走,堵在嗓子眼里了。” 我愣了一下,积食?大医院的化验单上可没写这个。 他拿起钢笔,在纸上写着什么,笔尖划过纸页沙沙响:“回去用白萝卜煮水,加三块冰糖,早晚各喝一碗;晚饭别让孩子吃太饱,睡前揉肚子,顺时针揉五十下。” 没开药?我盯着他写方子的手,那手背上还有个浅褐色的疤痕,像被什么烫过。 “不用吃药?”我忍不住问。 他抬头看我,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用手指推了推:“药吃多了,脾胃更弱。孩子小,脾胃功能没长好,吃进去的东西不消化,堵着就生热,热上来就咳。” 我半信半疑地接过方子,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像蚯蚓爬,但笔画挺有力。 付了十块钱诊费,推门出来时,风铃又叮铃响了一声,儿子拽了拽我的衣角:“妈妈,那个爷爷的手好暖。” 那天晚上,我照着他说的,给儿子煮了白萝卜水,加了三块黄冰糖,水熬得稠稠的,儿子喝了小半碗,说甜甜的。 第二天早上,孩子醒了没咳,我摸他后背,汗湿的睡衣换成了干爽的。 后来我才知道,李大夫是市医院退休的中医专家,小区里的老街坊说,他在大医院坐诊时,号难挂得很,现在开这个小诊所,就是图个自在,不为挣钱。 有人说不用仪器检查不科学,可我看着儿子喝了三天萝卜水,咳嗽就真的好了,晚上睡得安安稳稳,小脸红扑扑的有了血色。 现在路过3号楼,总看见那两张旧藤椅上坐着人,大多是带孩子的家长,或是拎着菜篮子的老人,没人催,也没人吵,李大夫就坐在那儿,不紧不慢地搭脉,问几句家常,手里的钢笔沙沙地写着方子。 诊所的玻璃门上,阳光照进来,把“李大夫诊所”那几个字映得亮亮的,旁边的旧藤椅,还是那样安静地待着,像在等谁来歇脚
医院退休老专家不在大医院坐诊,在小区开小诊所,不用机器检查,光把脉问几句就知病情
若南光明
2025-11-26 05:27:56
0
阅读: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