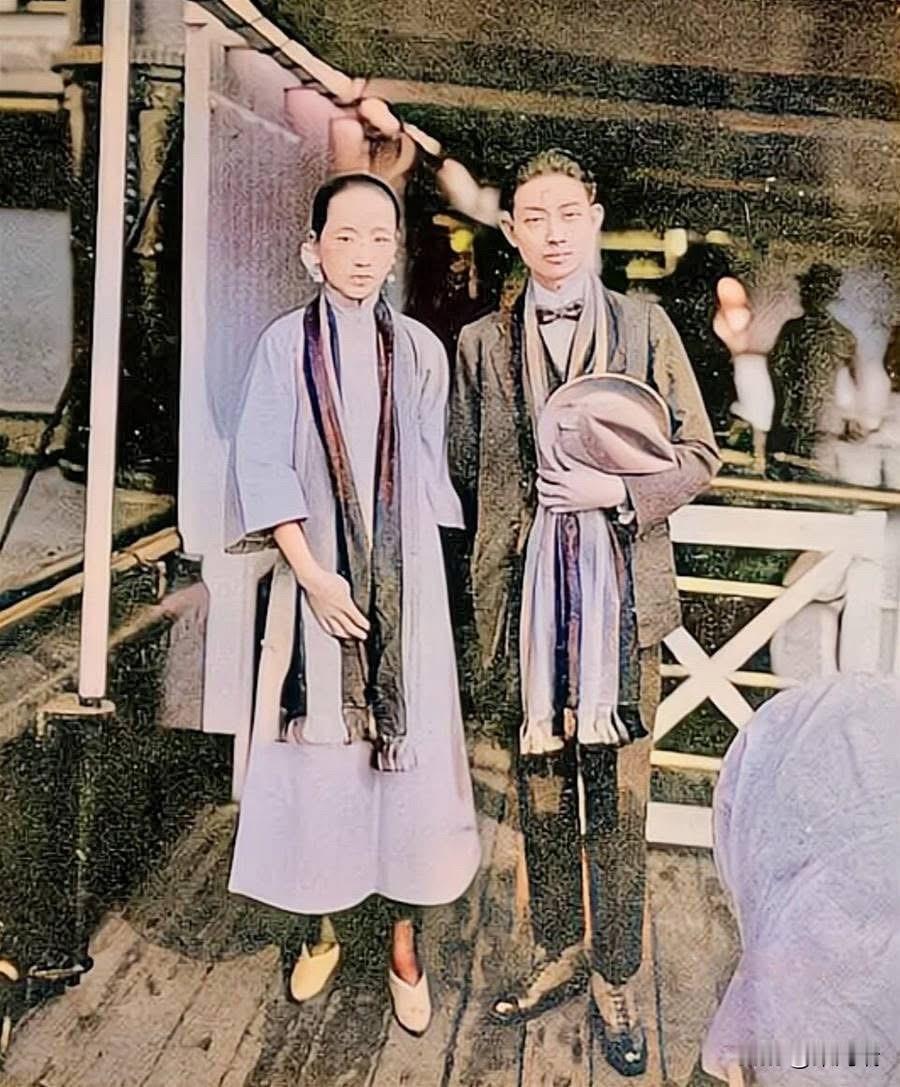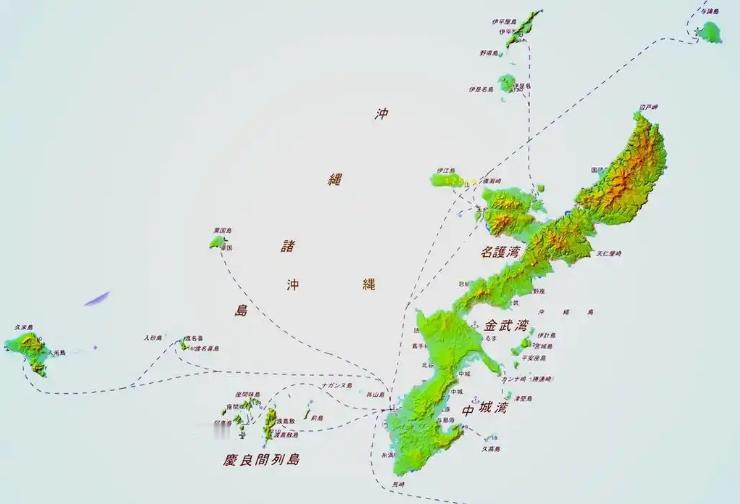1923年成都的冬夜,军靴踩碎青石板的声响混着酒气飘进后院。 杨森推开那扇雕花木门时,醉眼里的人影晃得厉害,他把穿着月白袄子的少女拽进怀里,嘴里还嘟囔着“我的美人儿”。 少女的指甲掐进掌心,直到天快亮才敢哭出声,她红着眼眶说:“我要读书。” 曾桂芝第一次见杨森时,正蹲在街边啃别人丢下的菜根,这个后来成了四川军务督办的男人,当时穿着笔挺的军装,让副官把她带回了杨家。 三姨太给她洗了澡,换上绸缎衣裳,教她认“天地玄黄”,可铜镜里的小姑娘总觉得,这金丝笼再亮,也照不进真正的太阳。 杨家的日子过得像钟摆,规律却沉闷,早上练琴,下午描红,晚上听三姨太讲“女子无才便是德”。 直到有天新来的先生带来几本《新青年》,曾桂芝才知道,原来女人也能进学堂,能和男人一样讨论“自由”。 她偷偷把书页边角磨卷了,在“男女平等”四个字底下画了道浅浅的横线。 那个改变命运的夜晚前,杨森看她的眼神早就变了,从前是摸着头喊“乖女儿”,后来总在她练琴时站在窗外,一站就是半个时辰。 她十六岁生辰那天,他送了支金镯子,链上坠着颗小铃铛,走一步响一声,像在提醒她身份他的“干女儿”。 醉事过后,杨森塞给她一匣子珠宝,说要封她做七姨太,曾桂芝没接匣子,只重复了那句话:“我要读书。”杨森愣了愣,大概没见过哪个女人不要名分只要学堂名额。 他最终点了头,却让副官跟着她去了女子学校,美其名曰“保护”。 新式学堂的风到底吹开了她心里的门,她在课堂上知道了“人权”,在操场上和男同学讨论“革命”,课本里夹着的字条写着“我们去上海”。 这些事没能瞒过副官的眼睛,杨森来学校那天,手里攥着那些字条,指节捏得发白。 枪声响起时,曾桂芝正和男友收拾行李,子弹穿透胸膛的瞬间,她好像又看见那个蹲在街边啃菜根的自己。 杨森站在门口,军靴上的马刺闪着冷光,他没再看她最后一眼,转身时说了句“晦气”。 后来成都城里的人说,杨公馆后院那棵老槐树,每年春天都比别处开花晚。 有人说,是因为树下埋着个爱读书的姑娘,她当年攥皱的课本,现在还在哪个旧书堆里躺着,扉页上“曾桂芝”三个字,笔画里还带着没写完的“自由”。 那个冬夜她攥紧的衣角,后来总在梦里被风吹起,课本里夹着的字条早被鲜血浸透,可“我要读书”四个字,像颗种子落在了那个年代的泥土里。 她没能看到女子真正站起来的那天,但至少在倒下前,她用自己的方式,对那个权力压人的世界说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