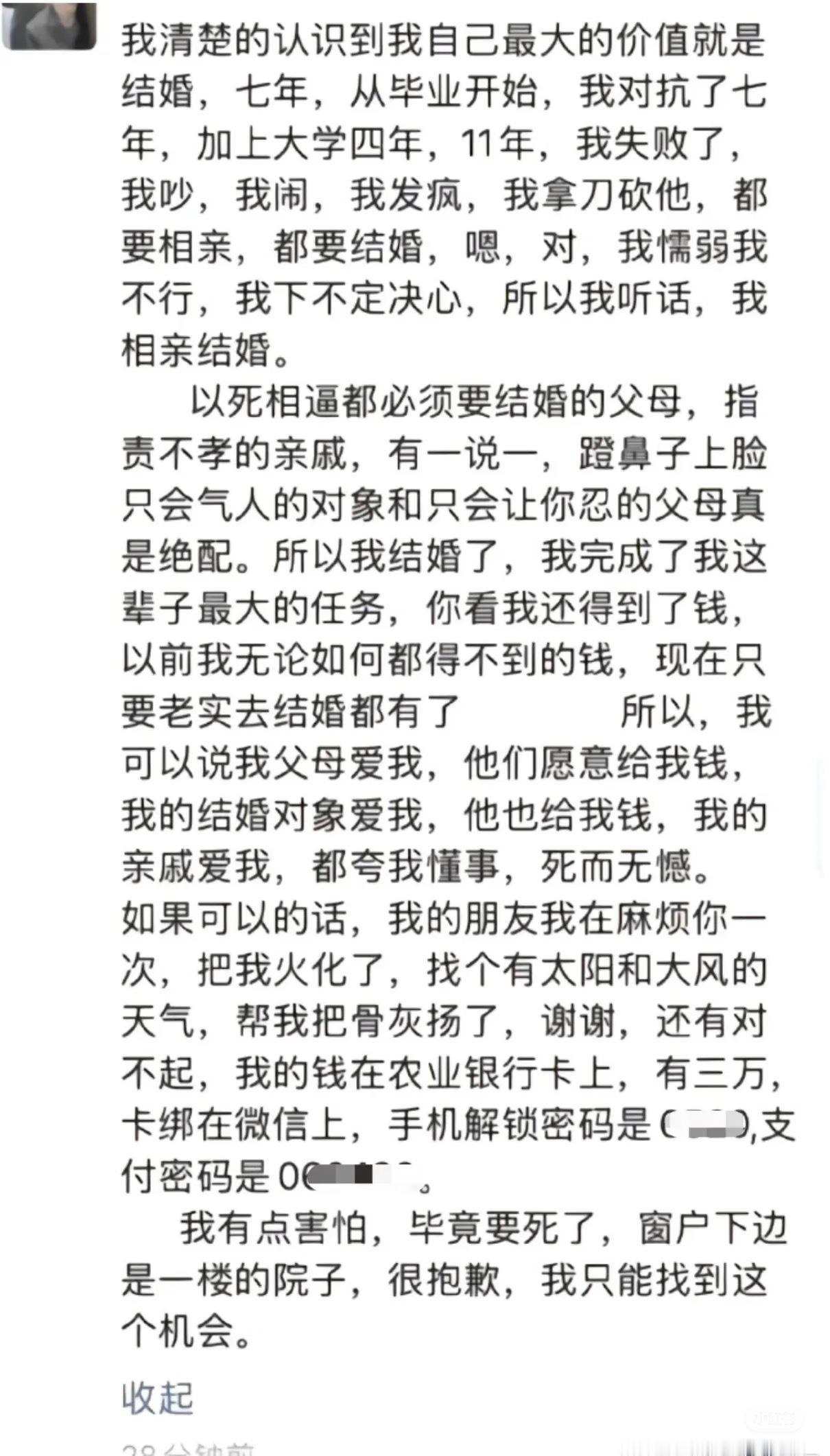一位89岁老人非常现实的话: “人死了,就让孩子把骨灰扔垃圾桶。如果孩子于心不忍,就让他找野地挖个坑埋了。不要骨灰盒,不要墓碑,不要砌坟,不要烧纸,不要供品,不要祭拜,不要花一分钱,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回归大自然,多好啊。 现实社会,人们总是对死亡讳莫如深,其实,死亡恰恰是每个人终究无法避免的宿命。很多人年老了因为没有人为自己养老送终而悲伤,很多人就为了这个所谓的养老送终,拼了命生儿子。还有的人看到别人死后的哀荣羡慕不已,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买墓地,买好棺材。 其实,人死如灯灭,最后就是那一把灰。即便为你风光大葬,花几十万给你买最好的墓地,留下墓志铭,那又如何? 事实是,人死后,几十人的送葬队伍真正为你哭泣的没几个,前几天人们对你津津乐道,几个星期后你就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中被遗忘,你的东西被扔的扔,被烧的烧,被卖的卖,几个月后彻底没了消息,几年后你将被彻底遗忘,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你的信息。” 装父亲骨灰的,是个吃空了的黄桃罐头玻璃瓶。儿子小陈骑着共享单车往郊外去时,车篮里的瓶子随颠簸轻轻作响,像父亲晚年总在口袋里揣的那把钥匙。 父亲遗嘱就一句话,写在病历本背面:“撒了,别花钱。”可真到殡仪馆,小陈还是多付了三百块要了最普通的骨灰盒。 抱着那个枣红色木盒走出门时,他忽然想起父亲总说“包装比里头的东西还贵”,又折回去退了。工作人员叹口气,递给他这个洗净的罐头瓶。 河滩的芦苇正抽穗。小陈蹲下身,拧开瓶盖。风突然大起来,第一把骨灰扑了他满脸,细密的粉尘钻进鼻腔,有股淡淡的、像雨前泥土的味道。 他闭上眼,想起六岁那年父亲教他骑车,也是这样的风,父亲的手稳稳扶住后座说:“怕就闭上眼睛。” 剩下的骨灰他倒进刚挖的浅坑。覆盖时,指尖触到几粒特别粗的是没烧化的碎骨。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它们推进土里。父亲骨质疏松多年,这些骨头活着时就已经很脆了。 起身时,裤腿上沾满草籽。远处有群孩子在放风筝,笑声被风扯成断续的丝线。小陈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选这里:周末总有家庭来露营,平日有钓鱼的人,永远不缺生气。 回到家,妻子盯着他空空的双手:“办好了?”他点点头,去阳台抽烟。月光很好,照见花盆里那株半死不活的茉莉,父亲生前最爱打理它。 小陈舀了勺水浇下去,忽然笑了。原来人走了,可以这么轻,轻到一阵风就能带走;又可以这么重,重到随便看见什么,都能想起他的影子。 夜风穿过窗户,把烟灰吹散在茉莉叶上。小陈深吸一口,缓缓吐出。烟雾融进夜色时,他仿佛听见父亲在说:对了,就是这样。 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老人希望骨灰归于野地,正是顺应“气散”的自然之理,不执着于形骸的留存。这与庄子鼓盆而歌的达观一脉相承,视生死为天地间气的聚散循环。 《礼记·檀弓》记载,孔子主张“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 儒家本有薄葬的传统,重在心哀而非形式隆盛。老人要求不置碑、不祭拜,是将对逝者的哀思内化于心,而非外显于物,这其实更贴近古礼中“丧致乎哀而止”的精神。 佛家讲“四大皆空”,“身如芭蕉,中无有坚”。 肉体终将坏朽,执着于坟墓、祭品皆为着相。让骨灰融入自然,是彻底放下对“我执”的眷恋,契合“本来无一物”的般若智慧。 陶渊明诗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或许是老人心愿最好的文学注脚。与山林草木融为一体,完成生命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回归,胜过任何人工修筑的坟墓与仪式。 因此,老人的话并非消极,而是对生命归宿极为通透的领悟。 它消解了丧葬的沉重形式与物质负担,将死亡还原为一场平静的自然代谢。 这其中既有对子女的体谅,不花钱、不添累,也有对天地法则的深沉敬畏。 在日益厚重的丧葬习俗中,这种选择提醒我们:生命的尊严与缅怀的真挚,从来不在外物的铺陈,而在内心是否真的能与这份逝去的安然,静静和解。 是啊,现实难得活得如此通透的人呐! 你认同这个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