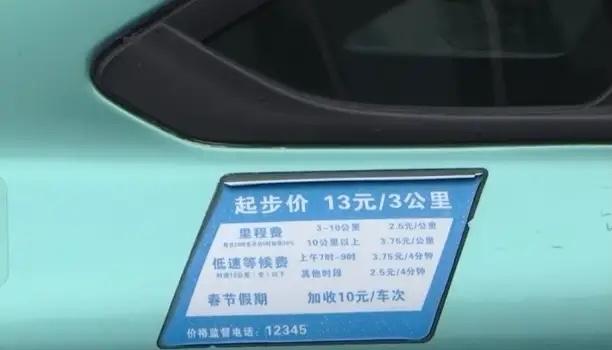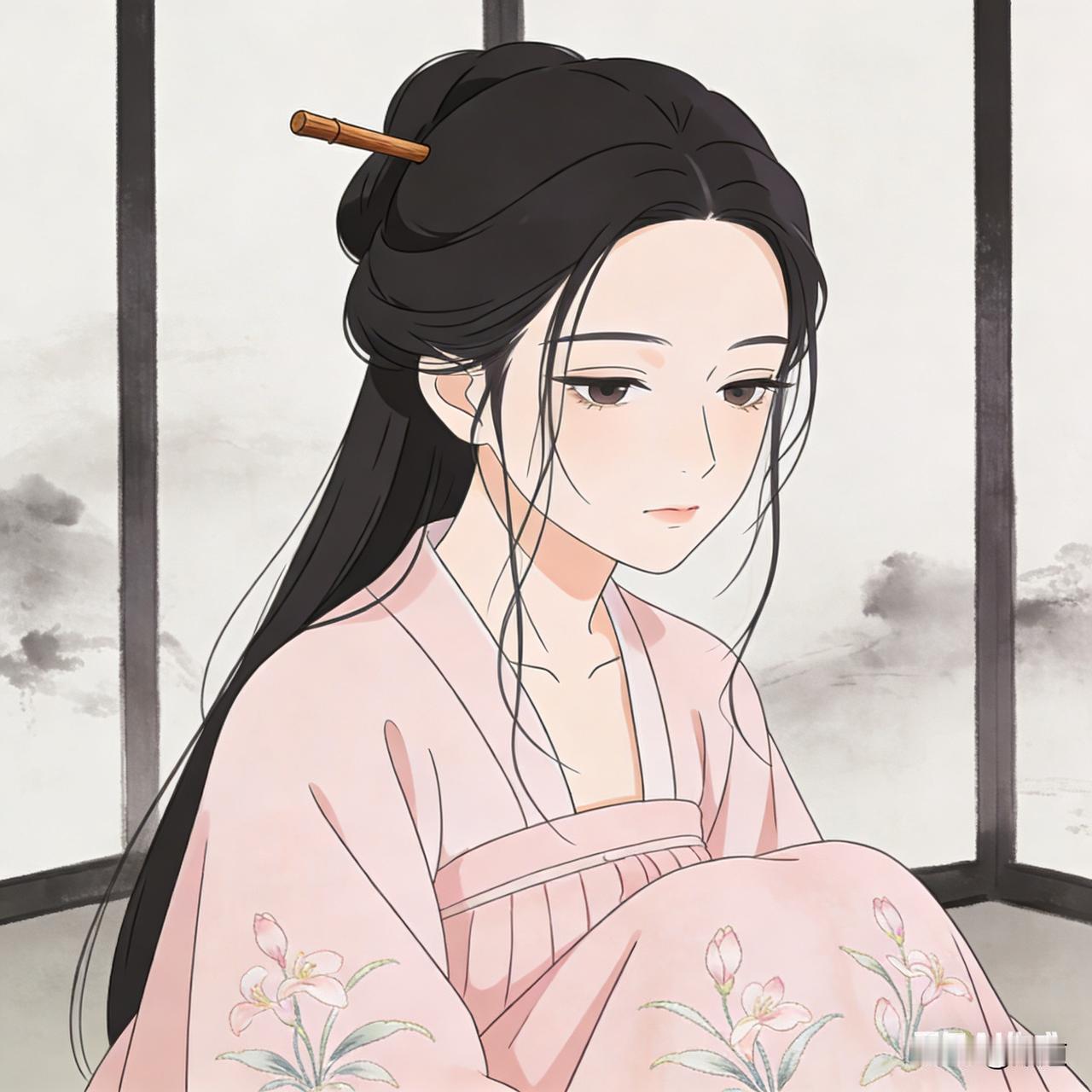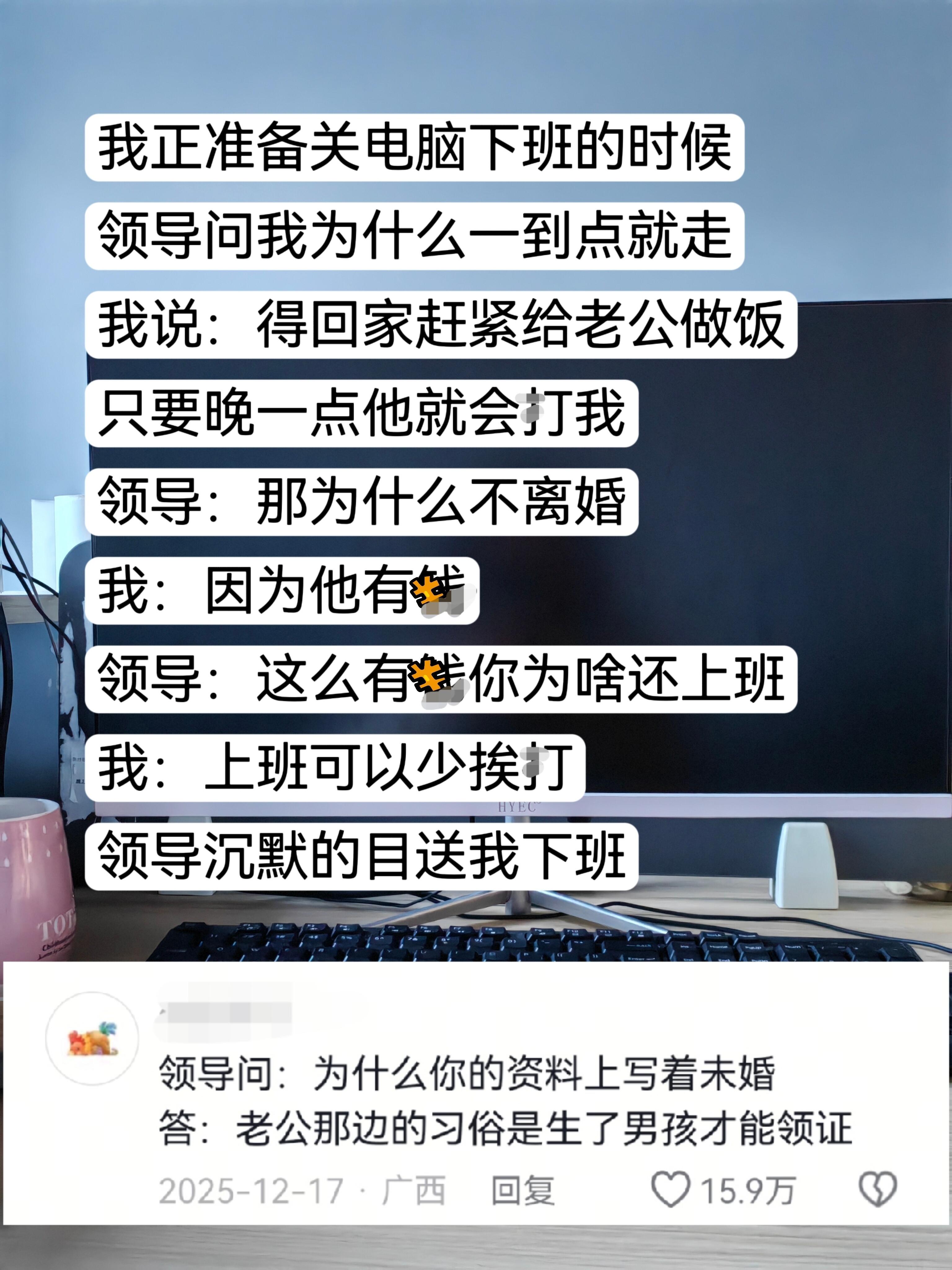我打车回家,司机故意绕路,我默不作声。到站后,师傅说:“一共 95 元!” 我瞧了瞧计价器,回应道:“哦,给你,不用找零了!” 师傅顿时瞠目结舌:“钱在哪儿呢?” 我把手机支付页面转过去,屏幕光刺得他眨了眨眼。师傅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领口蹭着块黑乎乎的油渍,头发跟被风吹乱的草似的,两鬓白花花一片。他攥着方向盘的手松了松,指关节那道青白印子半天没褪,喉结滚了滚,没吭声。 车里空调“嗡嗡”响,混着点烟味和旧座套的霉味。副驾座椅套磨出个小洞,露出的棉花团沾着根黄头发。仪表盘上压着张照片,边角卷得像波浪,我扫了眼——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张卷子,笑得缺颗门牙,卷子上“100分”红得刺眼。窗外路灯“啪”地亮了,光斜斜切在师傅脸上,眼角皱纹里还卡着点白灰。 “小伙子……”他突然开口,声音哑得像吞了沙子,“那绕的路……”我刚摸到车门把手,他从仪表盘下面摸出个东西,硬塞我手里:“这个你拿着。”是颗水果糖,糖纸皱巴巴的,印着只咧嘴笑的小熊,糖身软塌塌的,快化了,黏得我手指发黏。 “俺闺女的,”他指了指照片,“今天十岁生日,非要个会转圈的蛋糕。俺想着多跑两单……”他挠挠后脑勺,那撮翘起来的头发更乱了,“刚看你一直盯着窗外,还以为你没瞅见导航……” 我推开车门,夜风裹着路边烤红薯的甜香漫过来。师傅还在那儿絮叨:“要不俺退你二十?微信转你?”我摆摆手,把那颗快化的糖揣进裤兜,关车门时听见他小声骂自己:“老糊涂虫,净干这破事。” 出租车尾灯晃了晃,拐进巷口不见了。我摸出兜里的糖,糖纸黏在手心,甜腻腻的。没走两步,手机“叮”地响,是条转账消息,二十块,备注:“闺女说的,错了就得改。”
近日,一位哈尔滨出租车司机在凌晨4点多接到一个特惠一口价订单,要送一位南方女乘客
【16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