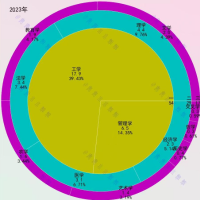本篇以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为背景虚构创作。
后周显德六年春,赵匡胤统兵征讨割据,平舒县作为瓦桥关南的重要据点,久已陷于契丹人之手。
然而后周先锋将领王彦升夜渡大城河时,忽逢迷雾,船行迷渡,两岸灯火冥冥,不知方向。
这一夜,他的战船泊在一个荒渡旁,忽然隐约听到雾中传来隐隐约约的声音,似鬼魅低语,又似故土长歌,竟隐隐指引着他前行——一切,似乎与这片土地的命运息息相关。
王彦升本是北周降将,归附后周后,以治军严明著称,但他从不信鬼神之事,只道是行舟时恍惚听闻的幻声。
然而,他登岸探察时,却发现那声音愈发清晰,竟似从渡口的古祠中传来。这座古祠被荒草掩埋,碑额断裂,只见上头刻着"平舒故祠"几字。
他推开祠门,一阵雾气升起,竟看见一盏孤灯悬在空无一人的神像前,灯影动摇,却听不到任何风声。
此时,荒祠旁忽然传来脚步声,却无人形。王彦升猛拔佩剑,却发现步履声仿佛从地上、墙壁间、天边传来,像有千百人正踩着落叶与水波行近,却怎么也看不见人影。
他压剑而立,忽而听闻一阵若有若无的吟诵:"平舒故地,北控三关,南系沧海,草木无言,天地有心......"这声音不悲不喜,犹如山河浩叹,回荡在空寂无人的渡口。
王彦升将剑归鞘,从怀中抽出一块玉佩,玉上刻着一个"舒"字。
这是他自幼随父游历平舒县时母亲赠予的护身宝,据说此玉可镇邪驱鬼,但这玉佩忽然在雾中生出柔和的光,光影渐显,竟将那"舒"字化为一幅地图,平舒县山河脉络跃然其上,而那河流交汇之处,一片红光隐隐散开,似是烽火未燃却已现的危机。
他还未来得及细观,那光图忽然消失,只留下玉佩的阵阵清凉。
他定了定神,决定循那隐隐可闻的吟诵声向前探寻,雾气渐渐散开,眼前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历史——

他看见平舒古时的城池,北魏时期的戍卒巡逻河岸,高粱连天与河岸并行;接着是唐代,驻军士兵的盔甲在阳光下闪亮,有儒生与渔人隔岸和诗。
随后是五代割据的乱象,烽烟卷过瓦桥关,平舒县沦为契丹占领地,而当地百姓却始终不愿改口,称这片县境为"平舒遗民";最奇特的是那片红光,仿佛是从宋太祖未出征时就已燃起的,那火光不散......
忽然,王彦升脚下的土地开始震动,似有千军万马行过。他举目远望,看见河面浮现一艘古旧渡船,那船无声无息,船头站着个披甲执戈的将军,但当雾气散开时,那"将军"的身形竟淡薄得像水汽一般。
将军回首一笑,道:"彦升,渡此河,平国仇。"王彦升想问是谁,话未出口,却只看见那渡船忽然化为流光,飞入远处雾气中消失不见,只余下悠悠的风吟:"平舒之归,须待山河重铸......"
后来,王彦升回营后立刻整顿兵卒,不顾后方粮草未及,竟连夜挥军直取平舒县。
时人皆不解,然而王彦升胸有成竹,他带领先锋队在晨光中越过大河,竟奇迹般发现原本契丹驻守的城池门户大开,城内空无一人,但墙上的旗帜已换成了后周的"周"字。那日,平舒百姓闻王师到来,不战而降。
战后,王彦升独自来到县衙后的一座石桥上,这座桥是当年赵匡胤曾与他共坐夜谈之地。
忽然他看见桥下浮现一点灯火,灯火似光非光,渐渐凝出一段文字:"平舒易姓,山河未变,玉佩渡人,忠魂守护。"待他俯身去捞,那灯火却复又散为水光,流入桥拱石缝之间。
他忽明白,这片土地虽然收复,却不是靠血肉拼杀得来的——那些不知名的精魂,曾将守土之意托付于他,平舒县的归服,不仅是武力的胜利,而是跨越天地的守护之功。
数年之后,王彦升改任沧州刺史,他离任时,地方官送来一幅新绘的《平舒县志图》,卷末附有一段文字:
"吾地虽屡失疆,然忠义未散。王将军渡河,虽战而未伤一命,实乃山河元气复生之兆。渡头孤舟如归,方知平舒为忠信之地。"
此后,当地流传一个传说,每当月圆之夜,王彦升曾渡河的"孤渡"仍可隐约听见吟诵声:
"山河千里归平舒,古渡无舟见渡夫。忠魂不散山河在,孤月重辉护万夫。"
大城河之滨的一些村落便以此为名,传为"平舒万夫村",以纪念这段山河重铸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