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朋朋 编辑 | 范志辉
不知所云。
这是刚开播的《新说唱2024》阿卡贝拉环节中,许多选手对于“河南说唱之神”的初印象。
这位97年出生的新生代rapper与众人画风迥异,像个误入此处的游吟诗人,娓娓道来一个村庄的故事,甚至过于激动到哽咽,带着哭腔完成了表演。
当法老把项链交给他时,大张伟在一旁感叹他是“说唱界张楚”。

节目播出以后,《工厂》MV正式上线,朋友圈直接被这首歌刷屏,围绕着歌曲的争议登时烟消云散。
数据显示,《工厂》MV上线不过三天,B站播放量直逼200万,只要打开这一视频,实时有数千人同时在看;多位乐评人、rapper纷纷为这首《工厂》录制reaction视频;视频号点赞、收藏超过10w+,转发9.8w;微博的转发列表里,遍布法老、洪荒、老狼等诸多不同圈层的名字;《工厂》同样位列QQ音乐的飙升榜,收藏数过万。

大家众口一词,“河南说唱从此有了神”。
那么,这首《工厂》到底好在哪?为何能接棒《阿普的思念》成为第二首破圈之作?
河南说唱,从此有了神《工厂》的破圈,离不开MV中的影像叙事。
MV的取景地正在他从小长到大的村庄,位于河南省焦作市。MV中,萧索的村庄,表情木讷的村民,在尘烟中嬉闹的孩子,赶着羊群路过的牧羊人。河南说唱之神在他们之间,讲述着压在这座村庄背上的沉重过往。

在官方的语境中,焦作拥有120年的煤矿开采历史,是一座因煤而建、缘煤而兴的城市,焦作煤矿是河南第一座现代化煤矿,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无烟煤产地之一。
在河南说唱之神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工厂的烟雾盖住了星,周围的村庄都被他合并”,他出生之初焦作煤矿已常年亏损,运转困难。下岗潮濡湿了两代人,他和父母生活在贫瘠的村庄,低头是中原的黄土,抬头是工厂遗留下的烟囱。

当兴盛的时代过去,才有那句“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MV中的演员都是他身边的素人。那些嬉闹的孩子正是村庄里的孩子,那些簇拥在镜头前的中年人,是河南说唱之神妈妈秧歌队的成员。他们都曾“看着网络上骂着农民”,曾自责没给下一代更好的环境。

这首《工厂》正是他们身上真诚而赤裸的故事。他们无力与一个时代对抗,“搬不走的人成为了钉”,沉默而隐忍地咽下一切苦难,“他们是孤独的,认的是命”。
到了河南说唱之神这一代,“逃离”便成为父辈们的训导,成为他们的使命。
在歌曲的评论区,天南海北的ip都在讲述着相类似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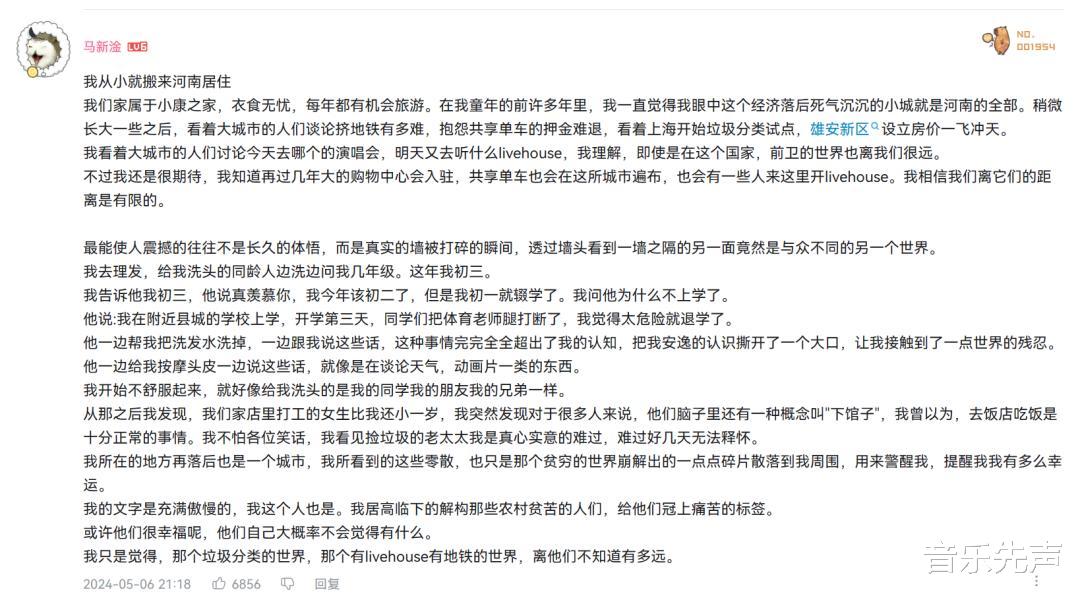
有人感叹“山河四省的年轻人成人礼是一张通往南方的车票”;有人共情“这片土地的牺牲好像是众星捧月一样,作为星星,一时闪耀后逐渐暗淡下去,空中只有那月亮还发光”;有人呼应“我很爱我的根,我的家乡,但是我想要更好的生活,我需要钱”。
也许河南说唱真的有了神,渗透着悲凉而无力的神韵。
小镇青年的赛博哭墙事实上,《工厂》中反思的社会议题在文艺作品中并不是全新的。
近的是2023年,《漫长的季节》席卷全网,悬案不过是这部剧的外壳,真正让人回味悠长的正是没有跟上时尚前行的列车。而被困在那个季节的东北工人,他们有过短暂的辉煌,却只能在时代辗过的车辙下咬牙向前。

稍远的是2010年,《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发行,讲述了一个河北的药厂工人,见证着自己重复30年的生活轨迹陡然易辙,茫然、徘徊、无力回天。万能青年旅店并未讲述这位工人的结局,只留下“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的余声。
更远的是贾樟柯导演的一系列电影,将镜头对准山西县城中的众生相,忠诚地记录下每一个、每一代人的困顿与失意。贾樟柯曾经说过,他一次次远行的动力可能源自封闭的故乡带给他的创伤体验,而每一次的远行又能让他更好地去理解自己的故乡。

而《工厂》这首歌,无疑呼应了贾樟柯的情感体验。河南说唱之神讲述着他对故乡复杂而矛盾的情愫,他一生都被训诫要逃离故乡,却在逃离之后也无法挣脱故乡的束缚。所以,他“幸运地逃离了那地儿”之后,还希望能为那些“姊妹兄弟”发声。
可以说,《工厂》并未讲述一个新的故事,但引发的却是新的共鸣。
时代的红利过去,《工厂》的故事早已不再局限于东北、河北、山西和河南的几个据点,拉扯、延展成为一代年轻人之间普遍的低气压。即便没有从辉煌到衰败的城市历史,没有下岗潮中成千上万的失意者,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同样也能体悟到那种相仿的困顿和迷惘。

那些故事,在这个时代有了新解。
它是拥挤的公务员考试,是工作日推背感的地铁,是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是五险一金和降本增效,是离我们太远又太近的房地产市场,是无休无止的精神内耗,是穿上又脱下的孔乙己的长衫。
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坦诚又残忍,将从前密不透风的城乡差异、阶级鸿沟展露在年轻人面前。当《工厂》被唱起,在河南说唱之神现代诗般的表达中,我们才能真正地正视一些情绪和故事。
工厂青年与县城青年成为大家自我的投射,残忍的现实隐藏在音乐的艺术加工中,才不至于将我们击垮。
所以说,《工厂》的走红,是偶然也是必然。
中文说唱的本土化叙事近几年,中文说唱从地下走到地上,迈入了主流的视野。与此同时,在商业化发展的进程中,中文说唱也在从“汉化”向“本土化”大步迈进。
被业界誉为“内地说唱第一人”的王波曾愤慨地说过,Hip-Hop的历史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历史是人家那边的,中文说唱历史是从零开始的。初入中国,第一批说唱音乐人听的是英文说唱,模仿着他们对于金钱、暴力和性的崇拜。

2010年之后,西安红花会、成都说唱会馆和重庆GO$H等一众地方说唱厂牌的崛起,为本土说唱音乐积蓄了一批坚实的受众。在这个过程中,川渝地区无疑是说唱本土化的领头羊。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川渝方言以其平卷舌、尾音向上等语言特点完美地解决了中文说唱押韵难的问题,使得用川渝方言创作的说唱歌曲在押韵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川渝传统文化中的侠义之风与说唱音乐通常表达的主旨不谋而合,率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然而,川渝地区的说唱音乐并未抛弃Hip-Hop的精神内核,只是将其进行本土化处理。将“街区”变成“江湖”,将“帮派”变成“侠肝义胆”,但确实奠定了中文说唱本土化的基调,以至于川渝方言成为了中文说唱的核心,知名rapper中有一半都在成都生活和创作。
随着说唱音乐在中国进一步生根发芽,rapper们抛弃了美国说唱的精神内核,开启了说唱本土化中的中文叙事。
此前,将中文说唱叙事做得最彻底的是董宝石。以《你的老舅》专辑为代表,整张专辑塑造了一个不务正业的小舅形象,讲述的是最具东北地区特色的本土故事。众所周知的是,这张专辑也成就那首最具破圈效应的说唱作品《野狼disco》。

董宝石曾在采访中表示,《野狼disco》能够爆火,是因为它足够“接地气”。所谓的接地气,不过是本土化的另一种说法,将本土化的故事、精神融入到说唱的风格中,才能突破说唱受众的圈层,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而跃升成为“文旅宣传曲”的《阿普的思念》也是源于此。即便歌曲中的hook大多为彝语演唱,但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并不具有理解的壁垒。

然而,河南说唱之神的《工厂》开启了中国说唱本土化的第三个阶段。与此前提及的所有作品又不相同,相较于方言说唱,它没有本土说唱中最典型、最稳居舒适区的地域特质,讲述一种时代情绪,尝试承载更为沉重话题。
真诚不遮掩,真挚不悬浮,这是《工厂》破圈传播的动能,或许也是说唱进一步本土化的可行方向。
*本文图源网络,如侵权联系删改
排版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