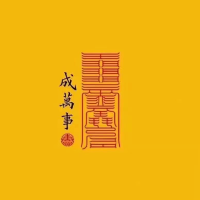青年书生杨于畏,山东省泗水县人,因父母双亡,家境贫苦,为读书方便,便独自搬到泗水边一座孤庙中来住。这座寺庙年久失修,周围荆棘丛生,古墓垒垒,初来乍到,不免让人产生一种荒凉冷落的感觉。然而对他来说,倒是一个难得的清静所在。
一天黑夜,风吹得白杨树哗哗作响,其声犹如波涛汹涌,乱得他读不成书,睡不着觉,只好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半夜以后,风停了,四周死一般的沉寂。他便点亮蜡烛,又埋头苦读起来。
这时,忽听墙外有人吟诗道:
玄夜凄风却倒吹,
流萤惹草复沾帏。
如此反复吟诵,声音是那么凄凉、哀楚。他仔细玩味,领会那诗的意思是:元宵之夜,本来是男女相邀、出外游戏的良辰,然而悲凉的风却吹个不止;看见飞行无定的萤火虫招引野草,想到自己孤苦伶仃的命运,不禁眼泪又浸湿了韩帐。
杨于畏被这诗情感动了,他站起来,走至窗前,侧耳静听。那声音纤细、婉转,好像是个女子。他很疑惑,深更半夜的,在这荒郊野外,从哪来这么个女子呢?他又听了半天,直到声音断绝,方才就寝。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墙外去看。转了半天,找不到一点人迹,只是在荆棘丛中发现一条紫色鞋带,他便拣回来放在窗台上。
这天晚上,约摸二更时分,他又听到和昨晚一样的吟诵声。他想看个究竟,便搬了个凳子,悄悄地放在墙下,慢慢地踩上去,刚抬头探望,吟诵声顿然停止。这一下他明白了,吟诗者不会是人,肯定是鬼。然而,那凄苦的情绪却引起他深深的同情和爱慕。
次夜,他干脆伏在墙头上侦察。一更以后,只见一女子缓步从草丛中走出,手扶小树,低首哀吟。杨于畏轻轻咳嗽一声,那女子急忙藏进荒草中。于是,他由墙上滑下来,蹲在墙下谛听。不一会,那女子又吟诵起来:
玄夜凄风却倒吹。
流萤惹草复沾帏。
听她吟毕,杨于畏隔墙续吟道:
幽情苦续何人见,
翠袖单寒月上时。
续诗的意思是:深沉的感情,痛苦的思绪,有谁看见呢?每当月亮上来时,孤立荒野,无人相伴,只有寒风灌进青白色衣袖。
这样吟罢许久,听不到外边有啥动静,杨于畏便回到室内来。刚坐下,忽见一个美人从外边走进来,敛起衣襟一拜,娇声嫩气地说:"只因您才学高深,风度不凡,所以我不敢轻易接近,怕您耻笑。"
杨于畏心中很是高兴,但见她身瘦体弱,若不胜衣,便拉她坐下,问她家居何处,是否久寄此地。
女子回答道:"我是甘肃陇西人,跟随父亲流落到这里。十七岁上突然得病,不幸死亡,至今已二十余年了。在这九泉荒野,孤苦伶仃,实感寂寞。因此作诗自吟,以寄托心中之恨。可是,仅仅两句,想了好久也连接不起来。今天您代我续起后两句,续的实在是好,使我在九泉之下也感到高兴。"
杨于畏想和女子求欢,女子皱着眉头说:"我是个夜间出没的鬼魂,同活人不能相比。一旦和你幽会,要折损你寿数的,我实在不忍心祸害你呀!"
杨于畏这才断了念头。他又用手去摸她的乳房,发现女子依然是个处女;接着,又看她裙下的两只脚。女子低头一笑,说:"你太啰嗦了,老看我这脚做什么?"
杨于畏不回答,只是左一眼右一眼地看个不休。只见她足上穿着丝线扎成的月色锦袜,一只鞋上系着紫带,另一只鞋上系一条黑色粗线,他便问道:"你这两只鞋带为何不一样?"
女子说:"前天晚上因怕你看见,慌忙躲避时把一条鞋带挂掉了,不知遗落在何处?"
杨于畏微微一笑,说:"我给你换了它。"说着便从窗台上取了紫带还给她。
女子惊奇地问:"这带是从哪儿来的?"
杨便以实相告。女子高兴地抽去黑线,将紫带换上。接着,二人面对面坐在案前。她随手翻看案上的书,翻着翻着,忽然翻出一本《连昌宫词》,她一看,不胜感慨地说:"我活着的时候,最爱读这本书。今日看见,仿佛在梦中一样。"
杨见这女子如此爱书,便和她谈起诗文来。从先秦散文到楚辞、乐府,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杂剧,她样样都懂,尤其是宋词,她能一口气背诵几十首。天资聪明,令人喜爱。杨于畏好像遇到一位知心朋友,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乎,越谈兴致越浓,直到窗纸发白,还舍不得离开。
从此以后,每到夜晚,只要听到轻轻的吟诵声,不多一会儿,她就来了。临走时,总是嘱咐道:"咱们二人的关系,你要保密,别告诉外人。我从小就很胆怯,最怕那些不正道的人欺侮。"
杨于畏也总是说:"不怕,请你放心。"
于是二人便像鱼儿得水,尽情欢乐,常常整夜整夜地在一块儿。尽管这样,但
他们从不乱来,行为非常正派。
杨于畏觉得,他和这女子虽不是夫妻关系,然而相亲相爱,却胜过夫妻。每当她在灯下给杨写书,字体端庄秀丽,使他赞不绝口。她又选择了宫词一百百,整整齐齐地抄录下来,二人齐声吟诵,不胜喜悦。她还叫杨画了棋盘,买了琵琶,每夜教他下围棋;要不就拨弄弦索,弹奏各种乐曲。每当她奏起辛酸的曲调,常常使他痛楚得听不下去;这时,她又弹起欢乐之声,顿时又让他觉得心怀舒畅。二人在灯下歌唱舞蹈,往往高兴得忘了天明,忽见窗上现出曙光,她才张张慌慌离去。
一天,一个姓薛的书生来访,正值杨于畏卧床睡觉。他环视室内,只见又是琵琶又是棋局,他很奇怪,觉得杨于畏向来不善于玩耍,为何突然对这些东西发生了兴趣呢。他又翻书,翻出一本抄写的宫词,一看字迹,显然不是出自杨于畏之手,他更加怀疑。杨于畏醒后,他便问道:"你这琵琶、围棋从哪来的?"
"我自己买的,想学习学习。"
"这诗卷呢?"
"是个朋友的,我借来用用。"
薛生反复细看,见最后一页有细字一行,写着某月某日连琐书。他心中已明白八九,便笑着说:"这是女郎小字,何必这样欺哄我呢?"
杨于畏被弄得很不好意思,吞吞吐吐答不上话来。薛生苦苦追问,杨于畏就是不肯相告。薛生将诗卷挟在腋下,这下杨于畏可没法子了,只好告诉了他。薛生蔥求见这连琐一面,杨于畏就把连琐嘱咐他的话也以实说了。薛生一听,更加仰慕,更想见见这位多才多艺的女子。杨于畏无奈,只好答应。
这天夜半连琐到来后,杨于畏便将薛生的要求透露给她。连琐一听大怒道:"以前说的什么?叫你保密、保密,你偏偏向人说。"
杨于畏有苦难言,只好把薛生来访的经过详详细细叙述一遍。
连琐说:"什么也别说了,我和你的缘分已经尽了。"
杨于畏急得什么似的,又是安慰又是解释。可是,好话说了千千万,连琐终究不高兴。她双眉紧蹙,脸色阴沉,痛心地说:"我只好暂去避一避。"说完,告别而去。
第二天薛生到来,杨于畏便代连琐转告她身上不舒服,不能相见。他怀疑是杨于畏有意推托,心中很是不乐。当晚,他邀集两位同学来到杨于畏住处,久留不去,故意扰乱,终夜喧哗,惹得杨于畏十分讨厌,可是也无可奈何。
这样一连几夜,不见连琐踪影,他们也就心灰意懒,喧闹声渐渐平息。正欲走时,忽闻吟诵声从墙外传来,凄凉、婉转,令人痛绝。薛生正聚精会神地倾听,其中一个会武术的王生,端起一块大石头隔墙扔了过去,大声喊道:"装模作样不见客,念的什么好诗!悲悲切切的,活活把人闷死!"
薛生等好不容易才听到连琐的声音,不料被王生这一砸,把刚发现的线索砸断了,几夜工夫也白费了,心中好生不快,埋怨王生太鲁莽。杨于畏对此举动更是恼恨,说了许多难听的话。
次日,这伙人扫兴而去。杨于畏独个儿在室内躺着,他希望连琐再来。可是,眼巴巴等了一天,连个人影也没有。过了两日,连琐忽然来到杨于畏室内,哭着说:"你招来那些孬人,几乎吓死我!"
杨于畏深感不安,连忙向她认错。
连琐竟然转身出门,说:"我所以说缘分已尽,就是从此离别了。"
杨于畏急忙上前欲拉她,已不见踪影。自此一个多月不来。杨于畏日夜思念,身子一天比一天消瘦,脸上的骨头都露出来了。然而,她一去不返,到哪里去找她呢?
一天黑夜,杨于畏坐在床头独自饮酒,忽见连琐撩起韩帐进来,杨于畏喜悦万分,便说:"你对我宽容了?"
连琐默不作声,眼泪像断线珠似的滚落到胸腔上。
杨于畏急切地问她因为何事,连琐欲言又忍,半天才说:"我一气之下,弃你而去,今又急来求你,难免惭愧啊!"
杨于畏再三追问,连琐才说:"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龌龊小吏,硬逼我给他做妾。我想我是清白人家的后代,岂肯屈身于一个肮脏的鬼吏?可是,我身软体弱,怎能抗拒过他呢?你若念及旧情,咱俩重新和好,我再也不过独身生活了。"
杨于畏勃然大怒,恨不得将那个龌龊鬼吏打死;但又考虑到人鬼隔世,怕是有力也使不上。
连琐说:"这倒不妨。来夜你早点睡觉,我在梦中邀请你替我出气就是了。"于是二人又倾诉衷肠,一直谈到天明。连琐临走时,嘱咐杨于畏不要白天睡觉,等到晚上好在梦中约会。杨于畏点头同意。
这天傍晚,杨于畏喝了几盅酒,乘有醉意,上床蒙衣仰卧。迷糊中忽见连琐进来,给了他一把佩刀,拉着他的手走了。去到一个院里,刚关上大门要说话,忽听外边有敲门的声音,连琐惊叫一声:"仇人来了"杨于畏突然开门冲出,见一人头戴红帽,身穿青衣,一脸横肉,胡须绕嘴。杨于畏愤怒地斥责恶吏,恶吏不甘示弱,立眉竖眼,谩骂不休。杨于畏怒冲冲地奔过去,不想那恶吏已将石头朝他打来,一块接一块,骤如急雨,飞石正好打在杨于畏手腕上,痛得不能握刀。正在这危急之间,远远看见一个人,腰中悬挂弓箭。仔细辨认,原来是王生,他便大声呼救。王生急忙跑过来,张弓一箭,射在那恶吏大腿上,又一箭,那恶吏一命呜呼。杨于畏见恶吏死在地上,很是高兴,连忙上前感谢王生。王生问因为何事,他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一遍。
王生射死恶吏,感到可赎以前投石之罪,就和杨于畏一起走进连琐住室。连琐惊魂未定,又害怕又害羞,远远站在那里低着头不说一句话。王生向室内扫视一眼,只见案上放有一把小刀,虽只有尺把长,然而却用金玉装饰。抽出一看,明光闪闪,他高兴地赞叹着,爱不释手。王生与杨于畏略谈数语,见连琐又羞又惧,怪可怜的,便出门而去。杨于畏也独自回去了,他来到墙外,正要骑墙而人,一失手摔了下来。他惊醒了,原来是个梦。
这时,他听见村上的鸡已乱叫,忽觉得手腕痛得厉害。天明一看,皮肉又红又肿。待到中午,王生来了,进门就告诉夜梦除恶救人之事。杨于畏问道:"你梦见射箭没有?"王生对他预先知晓感到很奇怪,杨于畏便伸出手来让王生看,并将昨夜之梦细述一遍。说完,同声大笑,想不到两个人同梦到一件事。王生极力回忆梦中连琐的容颜,只恨不能真见一面。他庆幸自己救了她,觉得立了一功,于是就请求先见她一面,杨于畏满口答应。
夜间,连琐前来道谢,杨于畏把功劳归于王生,并提出王生诚恳的请求。连琐听了却说:"武士相助,感恩不尽,岂能忘怀?不过,他气势雄伟,我实在有点怕他。"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武士不是爱我的佩刀吗?那刀是我父亲去广东时,出百两银子买的。因我十分喜爱,父亲就给了我。我用金线相缠,用明珠装饰。父亲可怜我夭亡,便把此刀作为殉葬品带在我身边。今日我情愿割爱相赠,他见了刀,也就等于见我了。"
第二天,杨于畏向王生转告了连琐的意思,王生大为高兴。这天夜晚,连琐果然把刀带来,对于畏说:"嘱咐他珍重,因为这是海外奇宝,并非中国之物啊!"从此二人来往密切,情同当初。
数月后的一天夜晚,连琐突然出现在灯下,望着杨于畏微笑,似乎想说什么,可是欲言又止,脸蛋儿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杨于畏问了几遍,她才羞羞答答地说:"很久以来承蒙你的爱慕,得到你的人气,又吃了人间的饭,我这白骨已有生还之意。但还需你的精血,我才可以复活。"
杨于提笑了笑,说:"只是你固执不肯,难道是我舍不得精血?"
连锁说:"你可要大病二十多天。不过,也没有什么,吃点药就会好的。"
接着,两个人同入帏帐,紧紧地抱在一起。
云雨方毕,连琐又说:"还须你一点热血,你能忍痛割爱吗?"
杨于畏立即取来利刀刺臂出血,连琐躺在床上,让他将血滴入肚脐中。起来后,她又说:"我就不来了。请你在百天头上到我坟前,见有青鸟在树上鸣叫,就赶快掘墓。"出门后又嘱咐道:"千万记住!准准一百天。迟了早了都不行。"说完,去了。
过了十余天,杨于畏果然病了,腹胀得要命。他服了医师开的药,泻下的粪便像黑泥一样。二十天头上病就痊愈了。
转眼已到百日之期,杨于畏叫了仆人扛着锄头来到连琐坟前。等到日头偏西,果见两只青鸟在树颠鸣叫,杨于畏高兴地说:"动手吧!"
仆人立刻斩荆掘墓,只见棺木已朽,而女子的容貌却和生时一样,抚摸胸口,还有点儿温热。杨于畏赶紧给她蒙上衣服,抬回来放在暖处。不多一会儿,听到呼吸的声音,渐渐地可以喝下汤,咽下稀粥。半夜以后,复活了。
从此,连琐常常对杨于畏说:"二十余年如同一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