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国之间致命斗争的背景下,非周国往往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在公元前649年。许王的儿子泰召集的几群人联合起来攻击都城。
他们的阴谋失败了;泰受到惩罚,在蔡寻求庇护。萧王和荣格的关系变得紧张,我不得不担任两党之间的调解人。
在另一个例子中,公元前627年,秦动员了蒋荣,在他们的帮助下打败了秦。然而,三年后,秦再次进攻秦,收复了失去的领土,成为西方荣格的君主,后者承认自己的霸权。

秦最初是如何使用蒋荣格的?他们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是后来才出现的(公元前559年)。在蒋钟和秦大臣范贤祖的争吵中。
为了防止蒋荣的头参加一个大型的州际会议,秦高官声称荣格首领的一位祖先,只穿着稻草,来寻求秦的保护,他和他的人民得到土地耕种。
荣格现在没有表示感激,而是散布关于秦的谣言,在其他周国家中损害了国家的声誉。

因此,荣格酋长将不被允许参加会议。荣格贵族(一个“子爵”,或tzu)的答复明确表明,秦一直在利用荣格作为加强国家的资源。
他说,当时秦因正在迫害他们,秦的许公爵,他认为荣格是“四山”的后裔,他们就容他们定居在南部边境,一个被狼和狐狸困扰的荒凉的土地。
荣格84年清除了这片土地,表现为忠诚的臣民,甚至给予钦军事支持反对钦:“如果军队没有回到它的国家也就是说。

它被消灭了——荣格的首领说——这要感谢我们。”他指出,钟格在军事和政治上是对秦的宝贵援助,如果“你们的军官军队犯的一些错误造成了与其他周领主的距离”,现在就没有责任了。
在撤退之前,荣格酋长说:
“我们荣格的食物、饮料和衣服都不同于中国(华),我们不和他们交换丝绸,我们的语言也不能相互理解。”
这句话,经常被引用来表示华夏和荣提之间的文化距离。

表明,这种文化距离并不意味着政治距离:荣格是周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额外的一部分士兵和农民的来源。
公元前533年,秦被指控有罪。依靠外国军队打击的核心周政治体系表明,这个时候外国军队可能被用在如此大的数量,他们构成一个单独的力量在中央国家,他们的存在只是成为焦虑的来源。
中国较大的国家吞并和使用非周民族,平行于新行政区划的划划和军队规模的增长。

再次以秦为例,在632年公元前629年,为了对抗钛。在现有的三支军队中增加了三个纵队公元前,军队增加到5支,也在588年作战。
在郑和帝人被迫合并后,秦的军队增加到6支——只有周家可以指挥一支90人的军队——很可能有很多新军队新兵来自被征服的荣格和提人。

一些钛在受到其他人的威胁时也自发地向周国投降,并可能提供他们服兵役以换取保护。一些提部落也非常容易被征服,比如当鲁国打败了可能属于提”星系的肯谋人时。
笔者认为:这些例子和其他例子明确地表明,到公元前6世纪末,钛族人民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各国的军事机构。
非周族加入了周族的军队,以及与他们的旷日持久的战斗,也促成了周族军事战术的重大变化。
到公元前541年。秦的状态已经向其战车军队转变为一个步兵,这将更能适应崎岖的地形,并专门打算与荣格和Ti步兵作战。

部队中对这一过渡的抵抗一定是相当大的,因为对拒绝服从的士兵所施加的惩罚是死亡。
随着胜利的周国不断合并外国人民,他们政治的扩张需要新的政府体系在政治和行政上吸收他们;因此在公元前七世纪。
周族制度周族制度是作为一个新的行政单位而创建的,旨在纳入新的主体,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非周族。如何保持他们的忠诚的问题也被讨论过了。
揭示在公元前538年中国高官的谴责他的主,他告诫主,傲慢或不虔诚的行为会导致彝族,荣格,提反抗,统治者的能力管理外国人民的公平手段而不是强迫的是他的精湛的一个基本属性。

春秋时期见证了周族与非周族之间新关系的兴起。在商朝和西方的商朝(一边是商朝和后来的周朝)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另一边是位于两朝核心区周围的许多民族。
然而,管理他们关系的原则是不清楚的,我们留下了一个边境的形象,那里的军队是最高的,来自中国国家的外国远征,以及外国人的敌意入侵。
然而,从周东方开始,周国和非周族(其政治组织水平难以评估)之间的政治关系变得更加规则和正式。

这种关系在三个层面上发展:被周国对非周政治的征服,周国与非周国之间的外交交流,以及将非周国纳入周国扩张的领域。
只要有可能,周国试图征服北方非周民族并合并他们。这一政策尤其在公元前八、七和六世纪得到实施。

由最积极的扩张主义政治政体,即秦、秦和秦。通过外交手段--会议、条约、人质交换和访问告上法庭——周列国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与外国势力的和平。
国家在和平时期的目标包括节约资源(人员、武器、设备和食物),展示睦邻友好关系,以及雇佣外国人来捍卫国家利益。
当他们征服外国人时,各州利用它们来增加军队的规模,保卫边境,并开辟新的土地。

这样,荣格和Ti就成为了国家争夺霸权的基本因素。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各种关于周氏国外交关系的学说。
在一般层面上,特别是在协议和程序方面,这些学说被大多数参与的政治体所遵守,无论是在周的政治和文化社区内外。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些学说应用于非周民族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在这方面,我认为,尽管人们用假定的道德差异来解释敌人为“可征服的”,但这些道德主张既不是固定的,也不适用于每一个外国政体。

对它们的背景的仔细分析表明,它们是政治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在周政治文化社区中正在发展的文化凝聚力的迹象。
对那些在原则上至少没有被视为外国的国家实施同样的道德制裁,清楚地表明,“道德”或“文化”共同体的概念仍然是流动的。

这种流动性反映了周东方的政治背景:在外交关系中,道德话语完全服从于战争和激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并适应了当时的紧急情况。
看周国家与外国人民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是否“军国主义”或“和平主义”学说出现反映了特定状态的目标在一个给定的时刻而不是更大的周(中国)文化意识表达自己的“道德内部人士”和“不道德的局外人。”

佐川和郭宇的历史信息也表明,道德考虑是次要的,仅次于我们所谓的锁定致命战斗中的政治的“理性选择”。就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提和荣格似乎作为独立的政治体基本上被淘汰了。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比如中山州,只在名义上是外国的,而事实上,它的居民在文化上与周州的居民没有区别。
政治吸收和文化同化的过程使中国北方国家接触到另一种类型的人种学和政治现实:北方游牧民族。

荣格人和提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牧羊人或登山者,他们的军事技能很容易与之媲美,而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战术和技术,尤其是与骑马有关的,构成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接下来的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境历史讲述了这次相遇及其对中国和亚洲内部的历史的后果。

在前帝国主义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时期像战国时期(公元前480-221年)那样改变了北方边境的物质方面和政治意义。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增长和军队规模的增加需要国家资源的不断扩张,迫使每个统治者都要找到最大化自己资源的方法,并试图压制对手的优势。

在战国后期,领土扩张的趋势持续稳定,北部的秦、延安和赵小兰三个州试图扩大他们对新土地和民族的控制。
笔者认为:北部边境是国家扩张进程的一部分,但与前几个世纪相比,中部各州现在面临着一种新的、要困难得多的情况。如第三章所述,中国北方田园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贵族游牧民族的军事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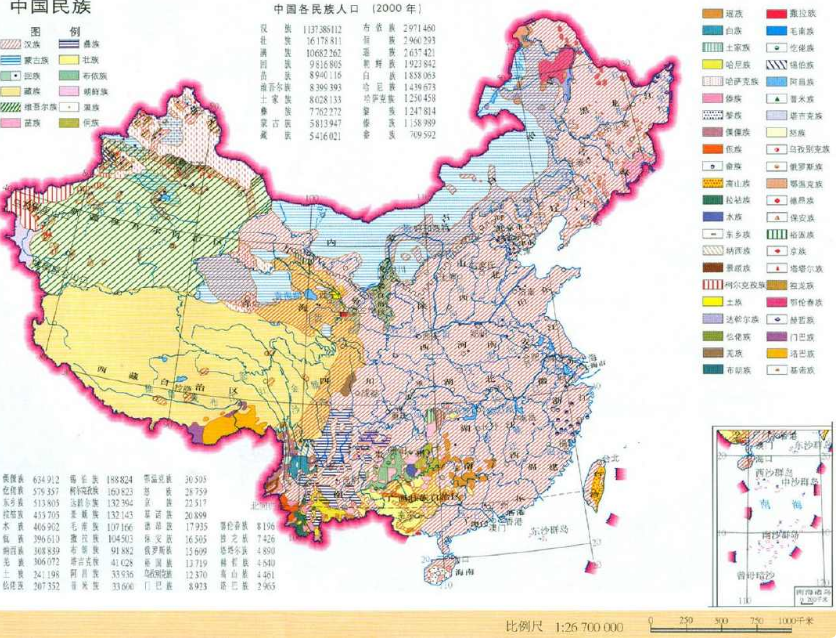
作为一种新的“人类学”类型,游牧民族以胡的名字出现在汉语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游牧的:他们饲养动物,骑马战斗,擅长射箭。
胡可能被组织成分为血统和部落的等级社会,很快就证明有能力创造类似帝国的政治单位。
他们刚到中国北方吗?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当然不是,但我们的知识仅仅是基于考古材料,而且仍然没有绝对的年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田园生活游牧文化可能在公元前7-6世纪就已经成熟了,尽管它们当时可能被限制在较少的中心,并与半定居的民族混合在一起。

从他们后来的成功来看,这些军事团体在军事上可能比毗邻中国的农牧社区组织得更好。
荣格逐渐消失的历史记录——尽管他们的名字继续使用修辞或痕迹——很可能不仅这些集团的同化的中国国家也游牧群体的力量增加他们的统治对这些民族,将他们在自己的政治。
战国后期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采用骑兵和在北方建造了被称为“长墙”(清长城)的军事设施。
所谓长城的前身,长长城构成了军事防御工事的北方线,后来在他统一中国后,由其连接成一个单一的体系。这两项事态发展都促成了北方明显的军事化和“更硬”边界的形成。

稗官青史
有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