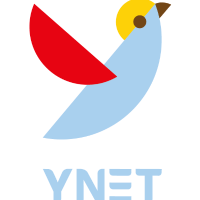朱自清与叶圣陶
◎高迪(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
商金林,1949年生,江苏靖江人。1975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他的新著《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聚焦于鲁迅、胡适、沈从文、叶圣陶等一大批重要作家,关注他们的思想心态、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和友朋交往,解读著作版本、书信日记、报纸杂志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并结合亲历所得,从历史的纵深处揣摩和欣赏,让读者从不同侧面欣赏到他们的流光溢彩。本版刊发该书的责编高迪与商教授的访谈文章,以使读者管窥一二。
从编撰《叶圣陶年谱》入手,与圣陶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迪:商老师好,您的新著《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非常关注人,钱理群老师认为您的研究具有“现代中国人文史”视野,所以我们的访谈就从“人”来展开吧。您是叶圣陶领域的专家,而且和叶圣陶先生一家是很熟悉的。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的场景吗?
商金林:1975年7月,我毕业留校当教员,自知根基浅薄,就开始有系统地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1976年冬天,系里恢复了教研室,我定位在现代文学教研室之后,就选择圣陶先生作为研究的一个“点”,从编撰《叶圣陶年谱》入手,与圣陶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圣陶先生的文章平易切实,写作年头长,对各种文学形式都作过尝试,作品非常丰富;他的生活脉络清楚,除了教书就是当编辑,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没有介入派系之争,联系面很广,受到同辈及文学史家和教育史家的敬重。研究他可以纵观现代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发展的历程,追寻近现代知识分子奋进的足迹。把圣陶先生研究得差不多了,再研究现代文学就有了基础。这就是我把圣陶先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动机。
圣陶先生是1988年谢世的,享年94岁。从1976年到1988年这12年间,我多次见到圣陶先生,他“列旁听”时的插话和提问,给我的启迪和教育是全方位的,既有文学史知识,也有治学的方法和为人处世的准则。说到“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的场景”,可说的当然有很多,让我最感动的可借用“到处逢人说项斯”这句话来表述。提到现代文学史和教育史上的名家,圣陶先生总是称赞他们的成就,赞美他们的人格。他的这种虚怀若谷、谦卑好学的美德特别值得弘扬。
高迪:当时您对和研究对象的交往有怎样的预期?
商金林:预期其实很单纯,就是觉得像我这样的新中国同龄人被荒废的时间太多了,得要脚踏实地,争分夺秒好好读书,好好补课。
编撰《叶圣陶年谱》,我从搜寻佚文和考订笔名等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凡是有可能发表圣陶先生文章的报刊都认真地查阅,年复一年、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因而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圣陶先生的长子至善先生在《编后》中说:“父亲的第一本集子就是《隔膜》,1919年以前的所有文篇都没有编入集子,散见于当时出版的各种报刊上。商金林同志为了寻找作者的少作,几乎跑遍了收藏丰富的几个大图书馆。一个个尘封的故纸堆都翻遍了,收获果然不小,文言小说就找到了近20篇,还找到了作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谈》。”
寻找到的散文就更多了,至善先生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说我搜集到的散文,“编两本集子也绰绰有余”。至于诗歌和论文搜集到的也很多。
在浩如烟海的旧报刊上查到圣陶先生的一篇佚文或一个笔名,我总是怀着喜悦送请至善先生审定。圣陶先生只要身体尚好,也总出来接见我,亲自审定。后来他眼睛看不清文稿了,笑着说“只好列旁听”。他静静地听我和至善先生交谈,有时插几句话,提一两个问题。最后连耳朵也听不清了,仍然走出来,坐到我们身边,笑着说“旁而不听了”。
和严家炎先生一起阅研究生考卷 800份试卷看了一个星期
高迪:这本书的第一辑叫做“认识在北大中文系执教过的老师们”,谈的是叶圣陶、朱光潜、闻一多和鲁迅。其实您自己也是北大人,作为“文革”结束后开启学术生涯的第三代学人,您进入北大时对中文系的感受是怎样的?
商金林:北大中文系是北大文科中的大系,人才济济。我最难忘的是1976年到1979年这三年。那时我住在北大南门附近的19楼,这是一幢三层高的筒子楼,临时用来作为教工和家属的宿舍,每层共用一个卫生间和水房。“四人帮”被粉碎了,老师们都憋着一股劲,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19楼白天寂静无声,晚上灯火通明,读书、备课、写作成了老师们生活的全部。晚上看书看到十点十二点,到水房打水洗脸遇到左邻右舍时,总会很自然地交谈起今天做了什么、看了哪些书刊,要是遇到感兴趣的话题或是某个疑难问题,就回到宿舍深入交流探讨,清晨一二点之后才熄灯休息是常态。
高迪:在北大,对您影响较深的老师和朋友有哪些?
商金林:19楼的老师朝夕相见,宛如一家人。系里其他老师大都也住在校内或学校周围的几个家属院,靠得都很近,在校园里常见面。我是系里的新教员,老师们对我特别关心。
有一次在未名湖边散步,迎面走来古代文学教研室的陈贻焮先生,陈先生问我进修古代文学的计划、读书遇到哪些困难,说他可以当我的辅导老师,欢迎我随时找他辅导。袁行霈先生讲毛主席诗词,我因有事缺课,他就把讲稿借给我阅读。教研室给我布置了讲《中国当代小说概况》《文学研究会》《解放区文艺》等几个专课的任务后,孙玉石和黄修己老师不仅帮我修改讲稿,还亲临课堂听讲,课上帮我撑场面,课下还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
1978年现代文学教研室要招收6名硕士研究生,考生多达800人,阅卷任务重。严家炎老师和我两人合判一道题,满分是“20分”。严老师是出了名的“严加严”,判卷时让我先看,他复审。他复审时往往为了评高了半分或评低了半分与我“商榷”,那800份试卷,我们整整看了一个星期。严老师的“身教”让我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什么才叫严格和认真。
承蒙你说我是“北大人”,我身上是有一些“北大人”的素质,如爱学习、做人做事还都算是认真,这些素质离不开北大老师和朋友们熏陶和感化。
高迪:我们知道为本书作序言的钱理群老师也是您的老同事、老朋友,他在序言里提到,您的研究是“超越文学史”的“人文学”研究的最初尝试。您对钱老师的评价有什么回应?
商金林:人文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礼乐教化、各种文化现象、人世间事和习俗人情等等,涉及文学、哲学、历史、艺术,以至文物考古、媒介传播等方面,人文学研究的领域极其广阔。
钱老师说我的这本书是“超越文学史”的“人文学”研究的最初尝试,大概是指我比较注重对“人”和“文”的研究,不仅仅是把人与文联系起来,从文中读出作者这个人来,而且把人放回到特定时代和群体中,从在艰难年代和他们做出的自我选择中追寻真相,力求较全面而准确地解读作者这个人和文,并在他们的人生思想和作品里找到可以追随的人生范式,“奠定一个深厚的精神底子”。我也的确是有这方面的向往和追求的。
其实钱老师的很多研究都可称得上是人文学研究。他在《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的《后记》中说他的“生存和学术状态:永远在路上”,他就“如鲁迅笔下的‘过客’,‘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我只能拼将生命的最后之力,‘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后面’”。
“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可以理解为是要把“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新的问题”,尽可能回放到中国社会更广阔的时空中去研求和探讨。所不同的是鲁迅笔下的“过客”并不知道从此地到那里的路该怎么走,他只是在寻求。而钱老师的学术追求和奋进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重振‘现代中国’的研究,认真总结20世纪、21世纪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教训,建构‘现代中国人文学’,解答‘现代中国之谜’”,并坚信他的学术研究“会有意想不到的新的发现,成为新的思考与创造的一个起点”,因而特别值得我们期待和尊敬。
把握到作品的真相和滋味 不被旁逸斜出所迷惑
高迪:您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您还是学生时北大中文系不主张年轻人过早发表文章,更强调好好读书。有句话说“读书要早,著书要晚”,其实您对著书、作文就是非常认真、谨慎的。您的书里也谈到朱光潜、叶圣陶、叶至善几位先生的严谨,他们写下一行字可能要阅读大量的文献。想请您谈谈您对读与写的关系的感受和认识。
商金林:读书能积累知识,拓宽视野。阅读的书籍似乎可以分两类,一类是略读的,读得快,是一般性的浏览,其目的是拓宽阅读面,这也就是鲁迅所主张多读。另一类是精读的,咬文嚼字求甚解,用鲁迅的话说是“研究性的阅读”,不止于了解大意,还要领会那话中的话,字里行间的话,即言外之意;既要看到书中的精华和珠玉,也要看到书中是否有“理未明”或“见未熟”的地方。
除了多读和研究性的阅读,鲁迅还主张读书要杂,甚至主张要读明明知道是“有害”的书,“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也要随便翻翻,总之是越多越好,越杂越好。
“读书要早,著书要晚”,这个早不仅仅是说要趁着年轻精力充沛多读书,也在强调读在写之前,多读才能找到可写的题目,才能增进写作的能力,多读文章和立论才不会蹈空。读当然是要把握到作品的真相和滋味,不被旁逸斜出所迷惑,陷于误区。
《宋云彬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时取了一个很醒目的书名《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书名下面又印了两行题词“亲历红尘,看天下风雨如晦/傲世冷眼,载笔端今是昨非”,将宋云彬的傲慢和嘲讽都说成是“红尘冷眼”,日记卷首的评介文章又把“红尘冷眼”说成是在提倡 “精神文明”,称赞“这样的日记方配为正史注脚” “令人敬佩”,完全读走了样。
书读走了样,与读得少不是没有关联的。研读宋云彬日记,至少得要把同代人的日记找来对照着看,有了比较和鉴别后,说出来的话才会有依据。我写《〈宋云彬日记〉的心态辨析——兼论史料研究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就是由此而感发的。叶氏父子说写下一行字往往要看几本书,其实就是为“读书要早,著书要晚”示范。
高迪:您刚刚谈到读应该把握作品的真相和滋味。您上一次出版论文集还是2004年,书名《求真集》,正与真相对应,这一次书名中的“读解与欣赏”在真相的基础上更强调滋味。在新著的后记中,您谈到自己对 “读解与欣赏”比较看重。请您谈谈为什么会看重这两点,以此作为书名希望传达给读者什么?
商金林:《求真集》意在说明做学问要把“求真”放在第一位,依归一个神圣的真字,拒绝承受新旧伪知识。读解是要把潜隐在字里行间的各种信息读出来,作出准确的解释,这是对知识和学术范畴的超越。在读解过程中享受美好的事物,领略其中的情趣,企求精神的高尚纯美,这就是欣赏。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都很善于读解与欣赏。
以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为例,俞平伯在《“五四”周甲忆往事十章并注》中写道:“太学举幡辉青史”,“后此神州日日新”,这两句诗称得上是对“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及“五四运动”作出的最庄严的评价。
沈从文在《五四和五四人》一文中谈到,“五四运动”造就了一代新人即“五四人”:他们“都有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热忱”,更有“做人的准则——有所为,有所不为,都是君子,爱己也爱人,都有一种‘青春不老创造的心’,都还带有一点天真的稚气,因而极其可爱,极其可贵。”这对“五四运动”说来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解读。
解读文献应该像侦探探案一样尽量寻找到“真正的真实”
高迪:您的文章涉及很多颇具争议的话题,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话题,是否遇到过其他研究者来和您争论?
商金林:人们习惯于把学问分为三类,一是发他人所未见、令人信服的定论;二是能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三是毫无新意的人云亦云。成为定论会很难,流于人云亦云毫无意义,成一家之言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要真能成为一家之言又谈何容易。前人留下来的史料有的很有限、我们的认知也会有偏差和局限,很容易造成两种窘境,一是对文本本身的解读出现误差;二是对文本背后的东西缺少应有的关注,做出来的学问就很难成立了。
前天跟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通电话,他对书中第三辑“史料与阐释”部分所收的带有论争性质的文章,说了很多肯定的话。解志熙教授人好心慈,明显是在鼓励我。我在这五篇文章中得出的某些结论的确是与“对方”的结论相左,反响也不尽相同,有表示“尊重”的,有“反批评”的,也有“漫骂”的。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尊重,欢迎反批评,对漫骂也能理解。
选择这些话题,是因为这些话题值得关注,文学史及作家作品方面的一些是非曲直,我们应该敢于去触碰,这是学者应有的姿态。我的解读也许并不到位,我写作的目的只是说明我在这个问题上是这么理解的,与你探讨和商量。做学问一定要充分利用各种文献,解读文献应该像侦探探案一样,尽量寻找到“真正的真实”;下结论要十分谨慎,审问制度上的“三审定谳”应该成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指南。
高迪:您书中的一些文章涉及经典作品的解读。学界和社会上都曾出现过对经典进行“祛魅”的做法,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商金林:所谓经典是说这个作品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魅力,对我们个人乃至全社会的思想文化繁荣和学术积累有一定的感召力和传承意义。时代在发展,对经典进行重新审定,是很自然同时也是很有必要的。至于经典重新审定中出现的污名化的倾向,就必须警惕了。
朱自清的《背影》写于1925年,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写的是一件很普通的生活琐事:父亲到车站为回北京读书的儿子送行。写父亲,朱自清侧重写了父亲的“背影”,第一次是父亲买橘子时穿过铁路,在月台边爬下爬上时的“背影”;第二次是父亲回去时“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的“背影”。可就是这篇篇幅不大的散文,新中国成立之前至少有30多种语文课本选用作教材,被编入各类散文选本的次数就更多了,作品中写到的“父子亲情”感动了几代人。
《背影》为千家万户传诵,表面上看来是把父爱写得温情脉脉,不同于同时众多作家笔下的严父,而更主要的是溶入那个时代像朱自清这样的家庭父子两代人的忧伤。“背影”,其实是父亲在旧中国挣扎的一个侧影。
“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小有产阶级“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引起了全社会的共鸣。有的研究者,不去细读文本,把握《背影》写作的背景和立意,而是去深挖父亲纳妾以及私自冒领朱自清薪酬等“劣迹”,指责父亲不守交通规则,甚至梳理出朱自清的恋母情结,把《背影》解读成了朱自清对父亲有“怨恨”,被誉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的朱自清(叶圣陶语)似乎成了“不孝子孙”,这对作家和作品都是一种戕害。
“祛魅”的本意是要剥离作品不该有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回归作品应有的品格,而不是别出心裁地做翻案文章。对像《背影》这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要有敬畏之心。见仁见智是百家争鸣的象征,众声喧哗有益于经典从原有的魅力中滋生出新的活力,永远流传,但批评必须谨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学术研究应有的素质和修养。“知”是对作品的确有真知灼见,而不是嘈杂的“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