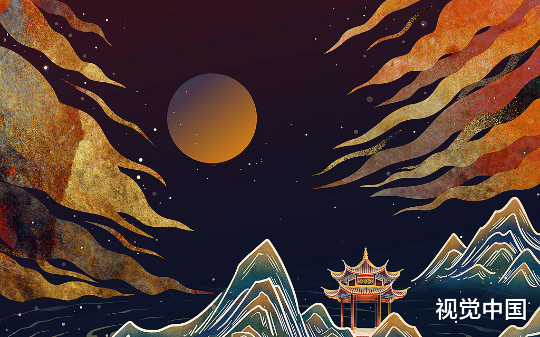城里的林员外有三大爱好,抽水烟,养舞女,看兽戏。
而我是被送到府上的舞女翘楚。
林员外饲虎为儿,笑着将我赤身关进了虎笼。
“既是难得的尤物,不如先让我儿尝尝味道如何!”
我以香汗为饵,伏虎作犬。
员外大悦,将我收入后院做他的干女儿。
他不知道,我没有一刻不想杀了他。
1
这个月又有一个新来的舞女被扔进了虎笼。
女孩浑身赤裸,看得出被养得珠圆玉润,没吃过什么苦头。
一旁的猛虎在笼子里摩擦着爪趾,张开的虎齿间流着涎水,默默看着女孩,犹如窥伺着一块白花花的猎物。
林员外养的老虎已经三日没有进食了。
我指尖微颤,想给虎偷偷喂能镇定的药丸,但是被林员外一瞬不瞬盯着,终是没能成功。
他勒令女孩穿上红衣跳舞。
她不敢反抗,颤抖着穿上,在偌大的铁笼里举起双臂,如走钢丝般踮起了舞步。
可是对于饿了数日的猛虎来说,一个会动的活物,还是鲜明的红色,更加激发它的兽性。
随着一声惨叫,女孩被猛虎擒住。
红裙被撕碎成布片,和皮肉交织在一起飞舞在虎笼中。
几滴鲜血溅到了我的脸上。
一时间,浓烈的血腥味、老虎的怒吼、女孩的惨叫声,从铁笼里传出。
林员外拊掌大笑,“妙哉,春杏生得美艳,果然适合做这兽女。”
我紧紧盯着虎笼,不消半刻钟,一只胳膊掉了下来,老虎嚼得认真,重新卧伏起来。
我回头对林员外说:
“干爹,她已经死了。”
他眯起了眼睛,“可惜了,本以为能再做一只美人彘赏玩的。”

在林员外满意离开后,我扶着墙,难以抑止地干呕出来。
不止因为感到恶心,更是深深的悲苦。
我叫如烟,是林府歌舞坊的管事。
也是林员外面前最得脸的女孩。
从前,我也是他从外面收回来的舞女,因为经受住了虎笼考验,才侥幸活了下来,被他收作义女,取名如烟。
刚刚死的那个舞女,是我在清月坊十分要好的姐妹,春杏。
其实她还没有死,而是因为太痛昏迷了过去,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我把春杏残破的身体抱在怀里,看她睁大了眼睛,逐渐咽了气,泪如雨下。
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的姐姐枝桃。
临死前,姐姐曾给我修书一封,写满了决绝,最后一句洇染了墨痕。
“枝兰,一定要活下去。”
2
曾经收容我们姐妹的林衍之,是远近闻名的慈善家。
他长得慈眉善目,总是眯起一双狭长的笑眼,年纪在三十多岁。
林员外自称天阉之人,从不娶妻纳妾,还经常布施乡里,得人人称颂。
在这个赋税繁重、饿殍遍野的年代,林府却日日歌舞升平。
林员外有三个爱好,抽水烟,养舞女,看兽戏。
兽苑里有多少奇珍异兽,后院就有多少冰肌雪肤的舞女。
舞女们吃得特别好,玉盘珍馐,逐渐让她们珠圆玉润。
但她们都不知道,被养肥了的代价。
等到主人和客人玩够了,身子有了残,就会被丢到兽笼里,任由那些女子被野兽撕咬致死。
而林员外喜欢听着她们的惨叫声,拍手称快。
舞女身份只是我的掩饰。
我是被清月坊培养出来的兽女,专门为这些喜好看兽戏的达官贵人准备。
兽女,不仅仅要满足主人观兽戏的喜好,更要在夜里做放得开的暖床婢。
林员外素日最爱一头吊睛白额的斑斓猛虎,取名阿蛮。
我求遍驯兽师,终于寻到了能让老虎镇静止狂的药丸,在第一次为林府表演的时候,悄悄喂给了老虎。
果然,见阿蛮乖顺如犬,林员外十分惊奇,问我赤身裸体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到的?
我徐徐跪地,一滴香汗滴落。
“奴以体香为饵,才能伏虎作犬,在员外面前献丑了。”
他非常高兴,凑近嗅到我身上如兰的体香,当场就收了我做干女儿。
从此,我成了林府最得脸的管事。
白日里,负责给林员外表演兽戏,驯服各种野兽。
到了夜里,又要让我伺候那些达官贵人,夜夜承欢。
亦包括林衍之自己,他最喜让我在床笫上唤他义父。
一开始我并不听话,他便带我去看其他舞女的下场。
她们有的被做成了美人彘,浸泡在酒缸中供他的友人赏玩;有的被砍去双腿,做成花瓶姑娘,放在地上为那些贵人服务。
直到这天,我终于在林衍之的地下冰窖里见到了姐姐。
失踪的姐姐竟然已经被他分尸两截,做成了冰雕!
姐姐浑身伤痕遍布,但肌肤仍因冷冻而饱满苍白,犹如生前一样,跪在地上。
另一侧则是姐姐的头颅,双目紧闭,嘴里被一枚颀长的玉器塞满。
林衍之轻轻环上我的腰身。
“你瞧,她叫枝桃,从前她其貌不扬,但是现在,像不像最精美的艺术品?”
“许多贵人们慕名来观赏,都交口称赞,这是一件极品的名器……”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已经将掌心掐出了血,强忍着泪水不能坠下。
姐姐自小和我生在田野间,长大后,她成了豢养家畜的农家女。
那时候我生了肺痨,姐姐为了凑钱给我治病,去林府当了驯兽师。
然而,当亲眼目睹和经历林衍之的残暴下流后,姐姐终于恍然大悟。
所谓慈善家的表象,不过是他人面兽心的伪装。
姐姐不堪受辱,带领着十几个女孩反抗,在一个侍寝的深夜,把喝醉的林员外五花大绑在了床上,企图勒死他。
可慌乱中,姐姐将布条系错了死结,没能缢死林衍之,被赶来的府卫制止。
后来,林衍之恢复后,给老虎喂了春药,竟活生生让阿蛮将姐姐凌辱致死。
我隐忍了三年,终于来到了林衍之身边。
直到我伺候客人时,偷听到他们的谈话,才知道林衍之是当朝皇后的族亲。
心顿时更冷三分。
所以他才能在普天之下,如此无法无天。
既然这世道,没有人可以为我们主持公道,何不逆天而行?

3
听说江南水患频发,许多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
林员外决定亲自下一趟江南,给地方捐款。
他摸着我的脸庞,叹息,“如烟,看着那些花朵似的女孩子面黄肌瘦,吃不饱饭,我真是心疼。”
我心中一沉。
琅县水灾,林员外捐出黄金百两,恩德载入县志。
他没有别的要求,只想去看看那些受灾的可怜百姓。
果不其然,一趟慰问过后,林衍之又带回来了新的女孩。
这个女孩柔柔弱弱的,名叫浮萍,不过十三岁,家境贫寒。
听说林员外愿意收她为干女儿,让她读书识字,学习歌舞,还给了她父母一两金。
她的父母还以为是遇到大善人,拉着女儿,哭着跪在地上。
“浮萍这辈子能受到员外的大恩大德,真是几世修来的福气!”
林员外淡然一笑,温良恭俭让。
“无妨,等到了适合的年纪,我就把她许配个好人家嫁出去,你们也可安心了。”
可林员外带走浮萍后,她的父母转头就拿着钱,和弟弟喜笑颜开。
“谢天谢地,没想到那个赔钱货这么值钱……这下耀祖就有钱置办宅邸,娶媳妇了!”
我站在一侧目睹,只觉悲凉。
毕竟在这个饥荒年代,易子而食都是寻常。
我奉命把浮萍带回了林府,妥善安置。
由于相貌出众,在林员外的评判里,浮萍跟我一样。所以,他没有让浮萍跟那些女孩们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华美宽敞的单间。
我引她去了绣楼上一间名叫青荇的雅室。
没有人知晓,在这间看似雅致的室内,藏着极其残忍的工具。
无论是雕花床柱四周的挂钩,还是藏在床底的绳结,软鞭、特制的香花烛台……
当初我就是在这间雅室内,被林衍之残忍地收集了处子之血。
林员外崇尚邪术,搜罗各种山人道士,觅求长生之法。
以处子之血炼药,就是他的嗜好之一。
浮萍还茫然不知,她感激地看着我,说林员外真是个大好人。
“姐姐等我一下,晚间我随你一同去向父亲请安吧?”
我刚想对她说些什么,看到窗外的黑影一闪而过,抿了抿唇。
“好,我等你。”
见面请安,一切都相安无事,而林衍之也仿佛真是那个慈祥的大善人。
到了夜里,浮萍刚一开始沐浴,有人就冲进了她的浴房。
那一夜,我听到浮萍的惨叫。
可远隔在后院的歌舞坊里,没有人能听到这方动静。
翌日,我奉命去看她,发现地上有一杆带血的水烟壶。
浮萍的下身红白污浊一片,惨烈异常。
林员外让我找郎中医好浮萍,她却浑身发抖,跪在地上,求我给她一个痛快。
“祖母还在等我回家……姐姐,请你替我告诉她,汴州的花太美,我回不去了。”
我心中不忍,扶起她时,贴在她耳边轻声说:
“或许,你想过逃走吗?”
浮萍绝望的眸子里终于燃起卑微的希望。
我压低了声音,“你安心养病,趁下个月员外府过寿宴,届时看管的人手不够,我便悄悄放你走,切记不要回家,逃得越远越好。”
她眸光闪烁,“那姐姐你怎么办?”
我摇了摇头,宽慰她不用担心我。
“我跟了林员外很久,对他忠心耿耿,他不会杀我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4
到了寿宴那天,后院忙得一团乱,我悄悄将浮萍引到一个无人知晓的狗洞,送她出了府。
林员外好兽戏,远近闻名。
又因为是贤名远播的慈善家,来祝寿的人络绎不绝。
大宴开始之前,由我作为第一个节目开场。
我用口技模仿出鸟鸣,带着训练好的上百只百灵鸟和白尾鸢,给他在天空中排成了一个“寿”字祝寿。
鸟鸣啾啾,十分清脆悦耳。
而后,我又在虎笼中逗引白虎,白虎怒吼着抢夺我手里的食物,最终在我的抚摩下驯顺如犬,引得在场宾客惊叫连连。
我朗声道,“白虎阿蛮,为主君献寿,愿主君龙行虎步,寿比南山。”
林员外含笑饮了一口鹿血酒。
“吾儿有心了。”
当宴会开始,一个个脂粉滑腻的舞姬在台中央翩翩起舞时,有人却给他进献了礼物。
那人是汴州巡抚,竟需要给林衍之献礼,足见林家的势力滔天。
那献礼不是别的,竟是一头异常雄壮的雄狮。
巡抚笑吟吟说,这是西域来的异兽,要进献到皇宫里的,先给林员外尝个新鲜。
随即他拍了拍手,一众驯兽师带着几头母狮上前。
狮子们接二连三钻跳过火圈,热浪席席。
林员外因兴奋而目不转睛,连连拍手叫好。
没想到,表演才刚到一半,那狮子竟然兽性大发,捉住了另外三只母狮,挨个发泄起来。
在场带孩子的宾客连忙捂住了孩子的眼睛。
它显然比一般的公狮都要更加凶猛,不消两刻钟,母狮们竟一个个哀嚎抽搐,倒地口吐白沫。
林员外见状,拊掌大笑不止。
“这雄狮竟比阿蛮还要雄壮三分,真是我见过最精彩的兽戏。”
宴席结束,他多留了狮子一夜,说要在月色下赏玩狮子的皮毛色泽,定然别具风味。
一天的喧嚣结束,他喝了几壶鹿血酒,余兴未尽,来到了我的暖阁。
我不声不吭,如常打来了温泉水伺候他沐足。
林员外已经发现,新来的舞女浮萍失踪了,他正在派人去寻。
我思量着时间,此时,浮萍应该早已乘着我安排的马车出城很久了。
沐足结束,我跪在地上为林员外捶脚。
他半眯着眼睛,吸了一口水烟袋,忽然捏起了我的下颌。
“我听说,是你把江浮萍放走的。”
我心头震悚,后背顿时冒起了冷汗。
果然,这府里四处都是他的耳目,即使我如此小心,还是被他发现了。
我卑躬屈膝地伏在他的身下,乞求得到他的半分怜悯,以蒙混过关。
“奴也是见她可怜,她以死相逼,倘若出不去府,就要咬舌自尽呢,何必枉了一条性命?”
林员外闷闷的笑了,笑声在空寂如水的夜晚,格外回荡。
“如烟,你坏了规矩。”
他伸手,慢条斯理剥开我虚拢的衣带。
林府的下人都是不被允许穿亵衣的。
紧接着,玉扳指狠狠掐住我的肩头。
我疼得倒吸一口冷气,颤抖着求饶。
“……如烟知错了。”
林员外不语,而是一把将不着寸缕的我打横抱起,一步步向外走去。
可令我更恐惧的是,他走向的不是床帷,而是后院关着狮子的铁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