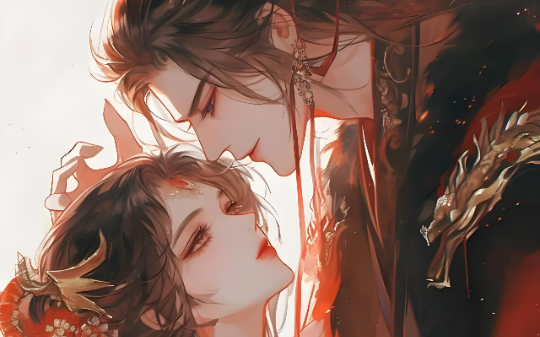父皇寿辰当夜,我的驸马段恒之,亲率兵马杀入皇宫。
将爱我如掌上明珠的父皇母后太子兄长,乃至阖宫上下屠戮殆尽。
只因太子妃是他多年爱而不得。
太子妃不堪受辱,于东宫决然自戕。
为泄愤。
段恒之将太子妃血淋淋的脸皮贴到我脸上。
我被割掉舌头、斩断四肢,制成一瓮不死不活的人彘。
若有来生。
若有来生……
我定叫他也尝尝,这锥心刺骨之痛!
01.
「不要!!!」
我尖叫着醒来,入目便是刺目猩红。
被做成人彘的痛苦、怨恨、恐惧,犹如附骨之疽让我生不如死。
「公主,公主!」
耳边是隐隐约约的呼唤。
拼命推开试图拥我入怀之人,下一瞬,我看到了让我恨之入骨的段恒之。
「滚开!!!」
我尖叫着,一巴掌正中段恒之的脸。
从我被制成人彘,贴上太子妃嫂嫂的脸皮。
他每每看向我的眼神,便既痴迷又厌恶,痴迷于嫂嫂的模样,却厌恶我的本身。
周遭的声音越来越嘈杂,模糊的视线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影。
捂着头痛欲裂的脑袋,我口中不断发出哀嚎、尖叫。
「出了何事?蕴儿如何了!」
忽然。
一道我以为此生不会再听到的声音,挟着焦急与担忧涌入我耳中。
我僵硬而迟缓地抬起头,终于看清来人的瞬间,强忍多年的眼泪霎时犹如雨下。
不顾旁人的目光,我挣扎着扑进对方怀中,拼命攫取对方的温度。
想要说些什么,喉咙却又像被塞了铁块般,只能发出呜咽哭声。
兄长,兄长。
我竟然真的回来了……
02.
我重生了。
重生到了我与段恒之大婚当日。
铺天盖地的红中,身着嫁衣的我抱着失而复得的兄长失声痛哭。
「好蕴儿,不哭,不哭了。」
兄长轻抚过我的发梢,说话时却带了哽咽。
直哭至力竭,我方依依不舍松开环着兄长的手臂,旋即,便看到了另一双忧心忡忡的眸子。
是太子妃嫂嫂。
「大喜之日,公主万不可再哭了,当心哭坏了身子。」
嫂嫂心疼地在我身旁坐下,用帕子一点点为我拭去脸上泪痕。
想到前世。
段恒之率军攻破皇城,扬言要将嫂嫂据为己有时,嫂嫂抵死不从,于万军阵前把簪自戕。
我忍不住再次泪雨滂沱。
「到底怎么回事!」
兄长发了火,厉声质问刚挨了我巴掌的段恒之。
「你口口声声说会照顾好蕴儿,不让她受半点委屈,这便是你所谓的好好照顾!」
一侧的段恒之捂着脸,若非我一直不着痕迹地盯着他,怕是就要错过他看向兄长时,眼中一闪而过的怨毒了。
但他佯装得很好,即便被质问了,也只是满眼深情地将我望住。
「臣今夜的确不够周全,只因唯恐怠慢诸位皇亲大人,以致冷落公主独守空房至此,还望太子殿下恕罪。」
这人还真是惯会避重就轻乃至祸水东引。
我本就因非要下嫁段恒之热得朝臣百姓非议不止,如今他这话一出,岂非坐实了我胡搅蛮缠?
03.
原本喧嚣的喜房,因着段恒之一句话。
霎时落入一片死寂。
涉及皇亲与朝臣,兄长自是不好继续追究。
只听一声冷笑,兄长意味深长道:「如此,倒是孤等的不是了。」
「殿下!」
段恒之惶恐跪下。
「罢了。」兄长不悦地摆摆手:「到底是蕴儿的大喜之日,你如此做派,倒像是孤在借故生事。」
段恒之俯身磕头,再不敢多言一句。
见他这般,兄长未再理会,只转向我。
「蕴儿,你如今虽已成婚,但你终究是我大盛朝公主,一切皆有孤与父皇母后为你作主,你可省得?」
听出兄长话中深意,我倚在嫂嫂肩上,轻轻点了点头。
见状,兄长眉眼间露出满意之色,而后端详伏地的段恒之片刻。
领着众人呼啦啦离开了婚房。
喜庆的红色中,顿时只剩了我与依旧跪地不起的段恒之。
又来这套,故意在我面前卖惨装可怜,只为挑拨我们兄妹关系,让我落入众叛亲离之境,天下仅剩他一人可以依仗。
可眼下,我多瞧他一眼都觉得无比恶心,又怎会对他心生怜爱。
「公——」
「我累了,」截停段恒之的话,我身心俱疲地唤来婢女为我更衣,顺便将他打发出去:「你自去忙吧。」
段恒之面露惊讶望向我,眼中划过叫人心悸的浓烈愤懑。
前世我被做成人彘后,他便说,最恨我平日里总在他面前颐指气使的蠢样子。
那我如今便叫他瞧瞧,何谓真正的颐指气使。
04.
翌日。
前一夜吩咐婢女不准驸马进房,时隔五年,我总算能睡个安稳觉。
「公主。」
早起梳洗,为我梳头的婢女细声细语。
「驸马从昨夜起便一直守在公主房外,想必已是知错了,公主若不气了,可要召驸马进来?」
丹凤眼睨过去,想是我过去对这些与段恒之私相授受的东西太过放纵,以至于叫他们以为能拿捏我了。
不露喜怒地笑了声,我问她:「知错了?那你说说,驸马何错之有?」
像是没料到我会这样说,婢女登时怔在原地。
不过转瞬,她便拿准了我就是在跟段恒之使小性般,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
「要奴婢说,驸马也真是的,明知公主在房中等着他,竟还没完没了在外面同人饮酒,公主便是生气也是应当的!」
这话说得。
字字句句向着我,却又字字句句替段恒之开脱。
「翠绯。」
我唤了声,自小侍奉我左右的翠绯立刻应声上前。
前世,在我身边所有宫女太监,都无休止在我耳边替段恒之说好话时。
唯有翠绯,几次三番劝我慎而重之,结果却被我误以为她心怀不轨,成婚不久便不顾母后阻拦,将本该是大宫女的她发卖了去。
挥开意欲再说的梳头婢女,我吩咐翠绯。
「送回宫里,叫邓嬷嬷重新教导。」
那婢女登时瞪大了眼,还未等她开口辩解,翠绯先是一脚踹在她膝弯,待她失衡扑跪在地上后又狠狠一耳光掴在她脸上。
「不知所谓的东西,公主如何行事是你这贱蹄子能置喙的!」
干脆利落做完这一系列事,翠绯便一言不发退回原位。
骤然挨了打。
婢女捂着红肿脸颊,眼眶含泪却一滴都不敢落下,只瑟瑟发抖跪在地上。
05.
翠绯掌掴婢女之事。
未到晌午便传进了段恒之耳朵,他气势汹汹带着那告状婢女寻了我来,言之凿凿要我收回成命。
「我早先便屡次劝谏公主,纵使下头的人再有错,也不可随意伤人,公主明知我不喜你如此跋扈,却还要再犯,莫非从未将我放在过眼里?既如此,你我不若早早和离,倒也省了公主瞧着我烦心!」
段恒之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那婢女望向他时,当即便带了七八分不合时宜仰慕与羞怯。
「另外,那打人的宫女也实在不像话,若公主非要送人回宫重新交代,我看倒不如将那动辄便打人耳光的宫女送回去吧。」
我心中却只想冷笑。
他哪里是在为这婢女出头,不过是想借机拿捏我罢了。
可惜上一世我眼瞎心盲,竟从未看出他是如此居心叵测之徒。
我懒懒问他:「驸马可还识字?」
段恒之不悦蹙眉。
「公主此言何意?我当然——」
「既识字,就该知晓府门外的牌匾上,刻着的是『公主府』三个字,莫说掌掴个婢女,便是打杀了她,只要本宫愿意,谁又能奈我何?」
我冷声道。
他既说我跋扈,那我便索性跋扈到底了。
「来人。」
一个嬷嬷并两个侍卫应声而入。
我睨了眼趴在地上脸色煞白的梳头婢女,厌恶道:「多嘴多舌的东西,拖下去,杖毙,以儆效尤。」
「公主,公主饶命!」婢女跪在地上「砰砰」磕头,得了吩咐的嬷嬷二话不说,直接扯着她的头发就要将她拖出去,婢女被扯得生疼,自知我心意已决,当即便又向段恒之呼救:「驸马!驸马救我!驸马——」
不等她说出更多,我已然嫌吵让嬷嬷捂了她的嘴。
段恒之脸色铁青难以置信望住我,大约是在奇怪,怎的之前无往不利的话术,今日却起了反作用。
06.
大婚头一天便杖毙了个婢女。
不过三天,此事便在京城闹了个沸沸扬扬。
恰逢我回宫省亲。
御史台的折子就雪片似的送进宫里,个比个言辞激烈参我这个公主嚣张跋扈,将人命视作草芥。
若是前世,我自是想不到这事会与段恒之有甚瓜葛。
我一深宫长大的公主,便是娇纵了些、任性了些,但到底与民生社稷无碍,朝臣和百姓何苦总盯着我。
如今看来,我声名狼藉的背后,怕是少不了段恒之暗中推波助澜。
宫中。
母后忧心忡忡问我。
「杖毙婢女究竟怎么回事?怎就闹得这样大了?」
我瞧了眼一脸怒气的兄长与表情无奈的嫂嫂,出言安抚母后:「没什么要紧的,父皇若实在为难,女儿愿意受罚。」
「受什么罚!」
兄长压不住火了:「我看这事儿保准跟那段恒之脱不了干系!大婚当夜就惹得蕴儿痛哭不止,若非我那日亲自去了,谁知他还要叫蕴儿受多少委屈!」
「什么?」母后震惊,心焦地拉着我不住地上下打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无奈瞧向兄长,他自知失言,讷讷闭了嘴不再说话了。
母后哪里能容他避而不谈,当即便追问起来。
耐不住母后再三追问,兄长便将成婚当天的情形,三言二语告诉了母后。
07.
眼见母后也要动气,我赶忙继续安抚。
「那事儿怪不着驸马,是我当时想着小憩片刻,结果被梦魇着了。」
「当真?」
母后明显不信我。
我只能再三保证,到最后不惜指天发誓。
「蕴儿,你自小那样乖巧,从不叫本宫同你父皇操心,怎的如今同驸马成了婚,反而……」
母后疼惜地望着我,手掌轻抚过我脸颊,未尽之言在场几人皆心知肚明。
「我苦命的儿啊……」
瞧着母后就要泪如雨下,我同兄长嫂嫂好一番劝,才总算止住了母后的眼泪。
这日,为了叫母后安心,我在宫里一直待到宫门即将下钥,才乘坐马车回了公主府。
谁料刚进门,就瞧见堂屋里端坐着个满身绫罗绸缎的银发老妪。
段恒之坐在这老妪下首,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话,若非我早知段恒之母亲早逝,倒还真当得一句母慈子孝。
这又是何人?我上一世竟从未见过。
「恒之。」
见我进来,那老妪不起身不行礼,反而摆着架子叫了段恒之的名字。
「这便是你那刚过门的公主媳妇?」
段恒之点头称是。
老妪吊着眼角挑剔地将我从上打量到下,期间还不断发出不满的「啧啧」声。
终了,老妪握着龙头拐杖,提起来往地上重重一杵。
「既已嫁为人妇,纵使你贵为公主,也该遵从出嫁从夫的规矩,试问世间哪个做人妻子的,直到如此深夜才归家?」
「恒之脸皮薄,不好同你个女子计较这些,我既作为他的长辈,自当——」
「放肆!」
得了我授意的翠绯当即喝道。
「哪里来的乡野老妇,见了公主不跪不拜,简直放肆!」
老妪一句话被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又咽不下去,生生憋红了眼。
我睨向段恒之,戏谑:「本宫早闻你生生父母皆已离世,家中更无叔伯姑舅,不知这又是哪里来的长辈?」
08.
段恒之压下心头不快,不疾不徐信步上前。
「公主有所不知,这位是我族中一堂叔的母亲,你我该唤一声叔祖母的,公主万不可对叔祖母不敬才是。」
此言一出,先被憋红了眼的老妪,立时扬眉吐气,重新摆起了不知从哪借来的长辈款。
翠绯面无表情往前一立。
「驸马慎言,天底下,可称公主长辈的唯有陛下与皇后娘娘,便是宫中各位妃嫔、贵妃乃至皇贵妃,见了公主也是要行礼的,遑论这位不知从何而来的所谓叔祖母。」
「本朝律法,见天家如有不参拜、不行礼,除天家赦免者,一律与谋逆论处。」
摆着长辈款的老妪,被翠绯一句话吓得三魂没了七魄。
满是沟壑的老脸哆哆嗦嗦转向段恒之:「恒、恒之,你先前可从、从未说过这话啊!」
约莫没想到我会如此不给他脸。
段恒之蹙着眉,在老妪惶恐的眼神中还试图拿捏我,苦笑一声便开始动之以情。
「公主如今即为段家妇,便该尊我段家长辈,当年若非堂叔与叔祖母照拂,莫说有幸得娶公主,怕是连科举入仕都步履维艰,公主便是为了我,也不该纵着身边奴婢对叔祖母如此不敬!」
感情一切祸端的根儿在这儿呢。
看来经过杖毙一事,段恒之心怕有所变故,这才急不可待地请了家中长辈来。
妄图以「孝」之名迫使我低头服软。
上一世之所以没见过,大约也是因为我对段恒之无有不依,故而也用不着如此要紧人物出面。
09.
仗着段恒之的理所应当,那老妪又挺直了摇杆。
我暗暗失笑摇头,有些人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翠绯,请李嬷嬷来。」
翠绯应下,脚步匆匆去了。
我再不理会那不知所谓的两人,提步于上位落座,好整以暇等着李嬷嬷到来。
这一番以不变应万变,反倒让那两人再度慌了神。
老妪气焰嚣张:「你这般不尊丈夫、不敬长辈的媳妇,放在寻常人家早犯了七出之条!是要被丈夫休弃,被邻里唾骂的!」
她说她的,我兀自饮茶,不与傻瓜论长短。
眼见我无动于衷,段恒之也不再急吼吼要我如何,只不动声色审视着我。
不一会儿,翠绯同李嬷嬷来了。
「见过公主。」
李嬷嬷先行礼,随后才转向仍旧坐着的老妪。
「大胆乡野老妇!你一非驸马母亲、祖母,二非当朝诰命,不过区区旁亲尔,骨头没有二两重竟也妄想与公主平起平坐,简直放肆!」
话音未落,脾气火爆的李嬷嬷,当即上前二话不说扯着那老妪的衣襟「啪啪」便是两耳光。
「敢同公主同坐,此其罪一也!」
「啪啪!」
又两耳光落下。
「敢不向公主行礼,此其罪二也!」
「啪啪!」
又两耳光落下。
「敢以公主长辈自称,次其罪三也!」
10.
六个耳光甩出去。
趁着那老妪头昏眼花、段恒之震惊非常,李嬷嬷直接把人拖拽下来,按到我面前「咣咣」磕起头来。
与此同时,李嬷嬷还不忘「教导」她。
「看在你教养过驸马的份儿上,今日便对你小惩大诫,再有下次,老奴便回了陛下与皇后娘娘,将你这老妪直接拖去菜市场砍了头!」
光鲜亮丽的老妪,在李嬷嬷的磋磨下几乎没了人样。
满头银丝蓬杂、锦衣华服揉乱、环佩叮当也掉了满地。
瞧着着实可怜至极。
「宁蕴儿!」
段恒之气急败坏,直呼我大名。
「你竟敢——」
「啪!」
他话未说完,横空而出的一条裹着黑衣的手臂,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旋即,一道黑影眨眼落至我身前。
「竟敢直呼公主名讳,放肆!」
这是父皇为护我安危,特意安排在我身边的暗卫。
前世段恒之起兵叛乱之日,这些人也一如父皇圣意,未曾退却一步。
然敌众我寡,十数名暗卫最终为护我战直力竭,全部惨死乱刀之下,连一具完整的尸身都未曾留下。
暗卫的力量自不能与李嬷嬷同日而语。
仅仅一耳光,生生将段恒之打了个下巴脱臼。
看着狼狈难堪的祖孙俩,重生以来,我头一次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痛快。
11.
老妪乘兴而来凄惨而去。
只留下一个被打歪了脸的段恒之。
遥想当日初见。
段恒之青衣白马,面如薄粉,不知虏获了京城多少闺阁女子的放心,而我,便是其中之一。
之后,他假作对我一见倾心,几次三番次邀我出宫私会。
我对他,也由起初的贪图新鲜,直至最后情根深种,非君不嫁。
回想前世种种愚蠢行径,我恨不能一刀结果了当日分不清是非、辨不明黑白的自己。
「公主,你、你如今怎么……」
段恒之摆出凄楚面孔,难掩震惊的双眼中,倒映出我面若桃李的模样。
「本宫如何?」
我柔情似水看向他:「不是恒郎说的吗?本宫嚣张跋扈、视人命为草芥,本宫爱恒郎至深,怎好叫恒郎失望?」
段恒之瞳孔猝然一缩,继而便如先前每次哄骗我那般,望向我的目光中盛满了失望。
「我如此爱重公主,怎么会这般玷污公主清白!定是有人见不得你我恩爱如初,便污我清白,公主万不可信了小人之言啊。」
「是与不是,本宫与你皆心知肚明,恒郎何故攀咬旁人?」
段恒之讷讷再不能言语,只满目惊惶把我望住。
前世,只因我爱他、信他,沉溺于他为我编织的温柔陷阱。
为免他自轻自贱,甚至胡搅蛮缠为他向父皇讨来了守卫京畿重地的要职。
可最终呢?
他与我那早被皇祖父削去爵位,扔到封地自生自灭的四皇叔沆瀣一气、里应外合。
不仅亲手斩杀了父皇母后,将太子兄长施以极刑,还将他们的头颅与血肉模糊的尸体,高悬于宫门外用以震慑朝臣百姓。
重活一世,我又如何能放过他?
父皇寿辰当夜,我的驸马段恒之,亲率兵马杀入皇宫。
将爱我如掌上明珠的父皇母后太子兄长,乃至阖宫上下屠戮殆尽。
只因太子妃是他多年爱而不得。
太子妃不堪受辱,于东宫决然自戕。
为泄愤。
段恒之将太子妃血淋淋的脸皮贴到我脸上。
我被割掉舌头、斩断四肢,制成一瓮不死不活的人彘。
若有来生。
若有来生……
我定叫他也尝尝,这锥心刺骨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