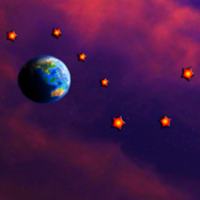文丨曹旭

枯枝无数,却隐喻于垂柳之间。这广场河边的两棵古柳,逢读书者,在其侧仰望,正有夕阳在怀。一群孩子仿佛知道这周末的静谧,静谧中的自由,便在周围,在越发彤红的夕晖之中,追逐嬉戏,远来又去。如此这些孩子的所为,是生理底蕴的作用,那么为祝中秋国庆的广场花坛,尚未彻底归正,乱草之中的虫子,知道夕阳之短,晓得秋意正散,在某个夜晚,就开始唤醒自己的什么一样,清歌吟咏,让一个人或很多人,想到了往昔的秋叶中,他们年复一年的演唱和轮回死生。
这是可以知道的,但又有多少是晓得的呢?年少时,望到野外的坟丘,推测它形状的缘由,是要拢起一堆土以标识?但标识为何不用方形或其他的形状呢?它定是最早的一个人,先妣过世,要铭记思母之恩,便于奶乳之状,来承载生育的深情。然而,几年过去,近日方知佛教徒传入之后,在野外坐化之高僧,被门徒发现,便起周围土壤,渐掩坐姿而逝的先师,掩蔽了,正好成了今天坟丘的模样。佛教盛行天下之后,这一切作为推广,也许此即坟丘的由来吧。
这是可以知道,但正如秋虫的鸣叫,实际上是他们的肢体摩擦而发出声响一样,也许万物根由,尚可推之下去,或基因般的因果长链吧,那样的推理已失去了它的含义,或者成为专家研究的学科了,常人知其相又知相因,足矣!人,心满意足,而且同类交流,识破万象,去生存,去在场,去活道的条件已足够了。
这仅是秋光中的一星,虫吟的一调。当我们面对自然,面对斜阳垂柳枯枝,哪怕荒草丛坛时,沉静,平和,以无欲般融化于一体的大欲望便在场了,即海德格尔的“在场”和“澄明之境”,是一切场的一部分。广场外那纷乱的车声,和场内焦虑的嬉闹,是那荒原般沉寂心灵之外的一抹或者另一抹灰尘。

午睡后沐浴的洁净自不必提,这时肌肤的青春气息仿佛返回,又逢周日的的午半,该是怎样的富足和慵懒。此时,不是夜宴到来之前的奔赴,甚而不知是否有朋友的相邀。家中无人,中午的余酒未醒,鱼缸因上午未及的更水,最大最美的那条鱼的夭亡,切切种种,浸出何等的悲意啊。
也许这只是一个读书者才有的悲情,亦或是读者也非,仅类似而已,在无尽的因为情愫的不能宁静而悲愁。也许只是,仿佛知道,恍惚之间,不是活在世上,是在非人的梦间,谁能了解。最当此时,以为不够,就是那不能宁静。想起那些关于激动的一切情事,关于人性可以矛盾悖行,又或者着并列向前的人情,让人多么悲切啊。
这些直白的夕阳的光辉,这些失恋一样的陈述。这些中秋去、冬将来的落寞。只有温柔婉儿的国人,才能含蓄的表达,不是这端的直接陈述吗?这些燃烧的焦虑,不,这些对青春对真美的渴望,内涵在灵魂的深处,只可袅袅升起的烟雾般的消散。一点儿的,稍微一点儿。
什么理想,什么工作,什么名利,在此之时,咸为身外之物,只有一情在,只存有对人的思念,却又不能张扬,无法摆脱的思念或想念在。这是人的幸福和不幸,这是人的不幸和幸福。这秋虫之鸣。

几天来,不可能是工作太劳累,或许是这段时间的饮酒无度,休息不好,所以下午开始头晕。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开始或者一种警告。走在午后上班的途中,看到地上落满黄叶,便听到了秋声,从周围苍翠的乔木和灌木丛中,沙沙的传来,不比午休梦中或昨夜梦中的惊恐,却另有一种特别的肃杀,含流其间。不再是梦幻,真的是生命正在凋残的颓势,在我的心扉和额头一点点的渗出,一线线的流失,像自杀者流走的鲜血吗?像一个割开血管,静候死亡者,观看者,感受者,消亡者。
几年来的当中,此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吗?还是得失并存的一年?得到生命特别的实践,是痴心工作的半年,亦因此失去了对诗情的追索,对于所谓词意的吟咏。像今天的日记,已是酒醉五天后的反省,而且没有五天中的任何生活的痕迹,那几乎是死亡的五天吧,疯狂的五天,精神病院患者治愈后的痛苦。
内心不怕这些死亡和痛苦,却愧疚着生活的流逝,愧疚所做的几件事,羞于启齿,尚有廉耻的一点自觉吧。秋声因此而来,正如虫儿白天隐匿,秋夜吟咏而来,告知我的怯懦和羞愧。因此下午这不经意的一撇,这微乎其微的一丝微光 ,照亮了我内心的黑暗。看到死,窥视到生。
此时的傍晚,正是我忧郁的天空,却又想起你梵高的麦田,那飞起的鸟雀,阴暗的天色,是关于死亡,却又成熟的闪耀的麦田,是我们的生命,那起伏的有些错落的田野。是一只秋虫的吟诵------今岁的消亡,明年的再生。

☆ 作者简介:曹旭,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教师进修学校干部,笔名陈草旭变,近年来有数百篇散文、小说见散文在线、红袖添香、古榕树下、凯迪社区等文学网站,合著有人物传记《那年的烛光》。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