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忆胡文彬先生
甄道元
2021年5月1日至今,转眼间胡文彬老离开我们将近三年了。
回忆与胡老交往的日子,到了夜间他常兴致大发,谈的很多内容至今记忆犹新。从山东逃难到东北,拿着打狗棍讨饭之类的生活琐碎,到李朝时期的朝鲜使者来华采风所记载的《红楼梦》传抄乱象,再到70年代《红楼梦》校注组时期,与周雷先生同住一个单身宿舍,二人常常讨论至下半夜,又到87版《红楼梦》的拍摄,以及为同好的校对提出建议……其兴致勃勃之态,历历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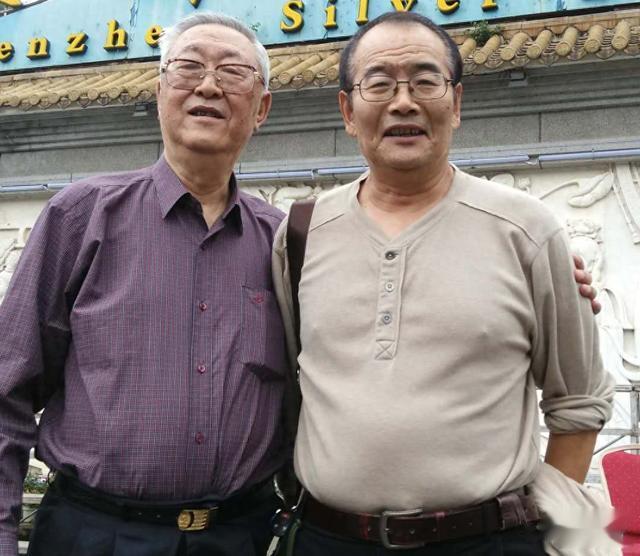
笔者与胡先生的合影
我自幼爱红,阅读中既有陶醉也有困惑,并做了不少的笔记。后来产生了一个想法:整理出笔记来,把自己起初读红时遇到的问题,告诉给初读者。这就要选一个好的本子,在这个本子上解读、评点。但发现,没有一个本子是我理解的那个样子。这时,胡老建议我重新校对一个本子。这才走上了研红之路。
胡老据我的兴趣,给了我三个题目。
一个是有关后40回的性质,让我捋一捋这一问题。他认为,“后四十回有曹雪芹的文字。”这是他对后40回的基本观点。
胡老说的很艺术,既不说后40回是曹雪芹起草的,也不说是曹雪芹在他人的稿子修改,只言有曹雪芹的文字,让人去想。我当时理解,胡老应是意在曹雪芹是上过手的。也即,不管它是曹雪芹起草的,还是曹雪芹拿来他人的,但曹雪芹摸过了,经过手了。现在想起来,胡老说到这个程度上,是在设置个开放的话题,留足了研究的空间。我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应是为这一立论找到支撑,或者证明这一判断不能成立。
一路研究下来,发现胡老的感知力极强,后40回中既有与80回五次增删前的底稿相衔接之旧文,还有新添加的、要替换掉旧文中那些与〖悬崖撒手〗相冲突的文字。换言之,旧文是个〖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白首双星〛的尘世结局,曹雪芹是要改写为〖悬崖撒手〗的出世结局。那些被留在后40回中的旧文,当是与出世结局不冲突的文字;而被替换掉的,则是与出世结局的新构思相冲突的章回。这类文字如〖花袭人有始有终〗,我们已无缘再见到了,但能意识到与新的构思不符。既然〖花袭人有始有终〗了,这便与〖悬崖撒手〗难以摆布;既然〖花袭人有始有终〗了,第5回的判词处的画面上,又预设了〚一床破席〛,这便把贾宝玉置于了不仁不义的地步。甚疑,〖花袭人有始有终〗是《风月宝鉴》的旧文,是构思〚一床破席〛之前的故事。换言之,〖花袭人有始有终〗之文、〖狱神庙慰宝玉〗之文、〖芸哥仗义探庵〗之文、〖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以及史湘云“拾煤渣”、宝玉沦为“击柝”之人等,有可能是与〚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贫穷难耐凄凉〛为同一时期的旧文。
而且,这样重新构思过的后40回,好似与80回增删前的底稿,统过稿。后40回与前80回中那些“毛刺儿”之矛盾的次要方面相合,反映出了这一问题。
2021年5月1日胡老匆匆谢世,当时的研究进展,仍处于专题形式。为纪念胡老,匆匆忙忙将专题整理在一起,名《红楼梦底稿探索》付梓了。胡老只见到过那些散置的专题,未能见到《红楼梦底稿探索》一书。
但这项研究是有意义的:胡老是在从外证的角度,否定张问陶的外证和程高续书的可能;这里是从内证的角度,来解决不是曹雪芹之后的人续书之问题。

第二个是批语的混入。胡老告诫晚生:“批语混入正文要注意”“120回混入批语太多,当细心甄别”“前后皆有”!
对于这个题目,很长时间内我转不过弯来,情感上接受不了“前后皆有”这四个字。因为,“前后皆有”包含着太多的信息量,意味着后40回同样混有批语。
胡老生前,我发给他剔除批语的草稿,印象中是200条上下。胡老看后说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让我加上一句“供同好讨论”。我在想,这是否在提示应当谨慎,是不是冒进了?但另一句的意思是,“还有!”这又似在说,工作仍不细致,批语没有剔除干净。至2021年10月出版《红楼梦批语混入与脂批分析》时,又剔除了几十条,共计280多条。
这套书将出第二版,第二版中累计剔除大几百条。估计很多人一时难以接受这个数字。胡老讲他幼时讨饭的情境,不但能产生共鸣,而且深受启发,更坚定仔细厘剔的信心。那个时代与今天的城市生活不同,乡下的苦孩没有发言权,只有两只眼睛向上,盯着大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份,来察言观色,品味人情世故,揣摩哪些话是当说的,哪些话是什么人什么场合才可以说的。书中第74回抄检大观园,王夫人盛怒审凤姐,安在凤姐头上的那些反问、那些教导长辈的口声,没有出自凤姐之口的道理,这是起码的人情世故。这些反问、教导应是旁人所批。否则,他便不是曹雪芹。学校读书时念了逻辑学,第37回安在探春头上的〚他想林姐夫〛,也不可能出自探春之口,否则必要追打不放,没有风平浪静这样的逻辑。如若只图阅读上的酣畅痛快,那么《红楼梦》的功能便锐减许多,便成看热闹的本子。在剔除过程中,还发现后40回也存在着批语混入。如第107回一段文字:
〚贾母听了,又急得眼泪直淌,说道:“怎样着?咱们家到了这个田地了么?我虽没有经过,我想起我家向日比这里还强十倍,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没有出这样事,已经塌下来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据你说起来,咱们竟一两年就不能支了?”〛
中间的49字便是批语,应当剔除。当作【夹混:我虽没有经过,我想起我家向日比这里还强十倍,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没有出这样事,已经塌下来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参《后40回中的批语混入》链接)。
既然后40回中混有批语,那么高鹗续书说便不攻自破。
因为,这不得不去继续追问:后40回中为什么会混有批语?是什么时候混入的?倘若如人们所言的是高鹗续书,那么他应当是一边续写,一边安排摆印。而不会是一边续写,一边被人拿去传抄,并且还有人评批,且传抄中还将批语混入了正文,然后再拿回来摆印。能混入批语,是要需很长的传抄链条的。这便从内证领域,否定程高续书说。
胡老的“120回混入批语太多,当细心甄别”“前后皆有”,不得不为其远见折服。

第三个是版本间的混抄杂合。胡老认为,版本间的混抄杂合十分严重,这也是人们感觉到书中文字混乱的原因。他认为,在以盈利为目的之传抄中,既存在听读式传抄,也即一人持书朗读,多人听写的传抄方式;也存在着目抄中将本子拆叶、多人分抄的方式。这与李朝时期朝鲜来华采风者所观察到的,是一致的。
晚生的研究还认为,在商业为目的的传抄中,还存在着两种本子同时拆开、分抄、混装的状况。装订时只顾及到了回次的衔接,而没有考虑两个本子分属的系统。这种传抄现象,倘若到了下一个的传抄团队,反复下去,则无法再以整本来论系统,甚至以章回来论系统也不现实了。但在支撑的例证上,比如在表示“全”之含义时,杨藏本常用“多”字,而他本常用“都”字。他本偶有一处用了杨藏本的“多”字,或杨本偶有一处出现“都”字,这并不稀奇,只表明一种本子窜抄了另一种本子。但是,如若恰恰在某一处,杨本用“都”而他本又恰用了“多”,也即二者在同一处发生了对调,这等巧合之事,只能解释为两种本子同时拆开并混装了。但由于在例证的典型性上,师生二人尚未达成共识,“混抄杂合”这个项目,一直没有完稿付印。
胡老去世后,我又依据自己的兴趣,启动了“成书过程”这项研究。此研究是胡老从未示意过的。研究的结论是:成书存在着主题上质变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江浙地域的家败、淫乱故事;第二阶段是民族主义者和对朝廷不满的人士,利用了第一阶段的题材,添加了排满主题和碍语;第三阶段才是曹雪芹的增删改写,净化了性事升华为情事,滤掉了碍语,并揉进了曹家事和北京元素。也即,成书的第一阶段,是江浙形成的。
这一观点出来后,红学家方晓伟先生告知,胡老当年在扬州师范的讲座,提及到:《红楼梦》最早就是在你们这里形成的。胡老的这一观点,从未对我提起过。没想到,师生二人竟然又想到一起去了,研究来研究去,仍未跳出胡老的圈子。胡老的这等眼界,着实令人钦佩!
今生能遇到这样一位恩师,实乃万幸之事!
甄道元于暨大羊城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