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一直对我的农村出身耿耿于怀,言语间常常流露出轻蔑。她总觉得我高攀了她儿子,配不上这个城市家庭。我默默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有一天,父亲察觉到了我的委屈。
“她又在说你是乡下人了?”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带着一丝心疼。
“没事,我习惯了。”我强忍着泪水,望着厨房里忙碌的婆婆。她正在择菜,动作粗鲁,菜叶被她摔得啪啪作响,仿佛在发泄着什么不满。
“等着,爸爸有办法。”父亲语气坚定,这让我对他的“办法”充满了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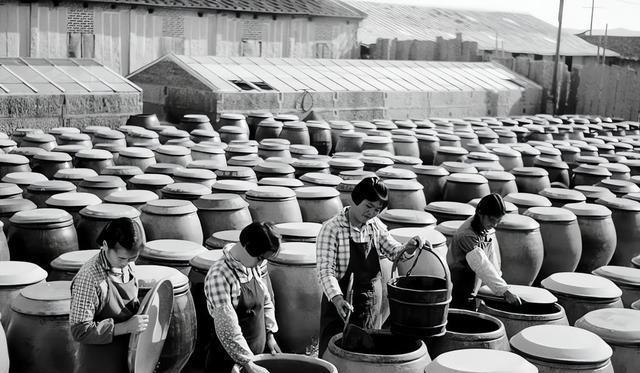
几天后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我站在十八楼的阳台上,看见父亲推着三轮车来到了小区门口。他穿着褪色的格子衬衫,衣袖高高挽起,开始麻利地支起了简易的塑料棚子。棚子上摆满了新鲜的蔬菜:青菜、茄子、土豆、西红柿……它们在晨曦中显得格外诱人。
婆婆也发现了楼下的父亲,她立刻跑到阳台上,语气里充满了不满:“这成什么体统?让人知道咱们家的亲家在楼下摆摊,我的脸往哪搁?”
我没有理会婆婆的抱怨,继续注视着父亲。我知道,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爸爸以前不是干这个的。”我轻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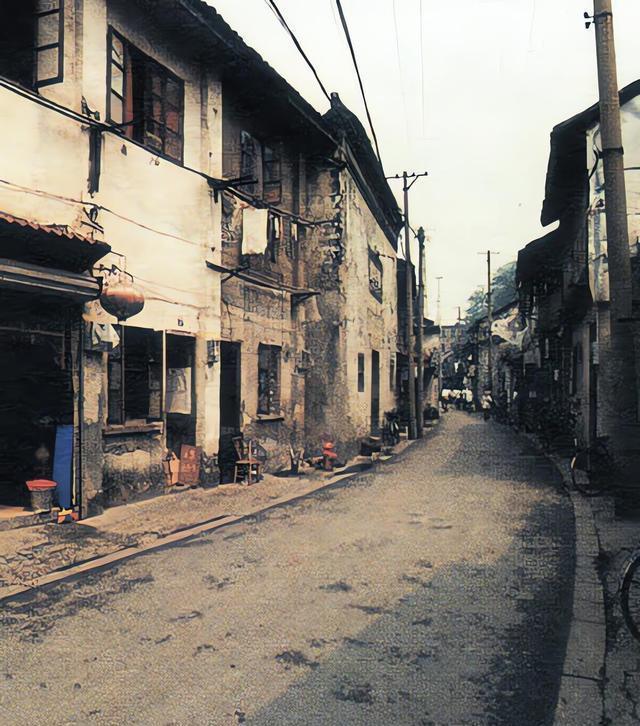
“那他是干什么的?种地的?”婆婆的语气里充满了讽刺,仿佛认定了父亲的身份低微。
我正要开口解释,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惊呼:“张老师!真的是张老师!”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跑向父亲的摊位,他激动得声音都在颤抖:“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您77级的学生,李德生啊!”
父亲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笑容:“德生啊,你这身子骨怎么样了?上次摔伤的腿还疼不?”

“张老师,您还记得啊!”老人眼眶湿润,“那都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转头看向婆婆,她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陆续又来了几位老人,他们都亲切地称呼父亲为“张老师”,有人带来了热腾腾的包子,有人拿来了保温杯,还有人搬来了折叠椅,让父亲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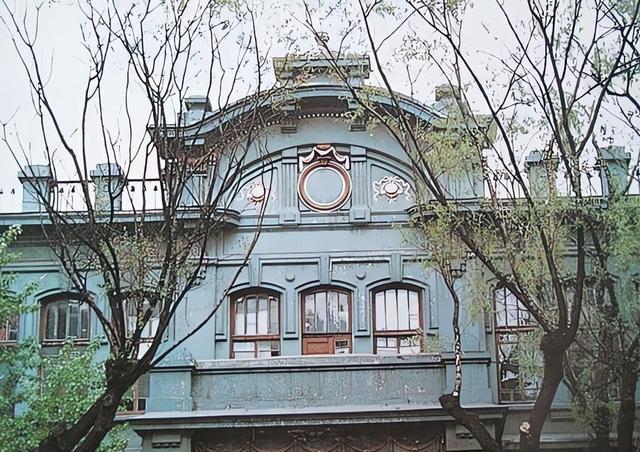
“张老师,您在这摆摊怎么不说一声?”
“是啊,您可是教了我们十五年的物理老师啊!”
“要不是您,我哪能考上大学?”

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都过去了,现在我就是个卖菜的。”
“张老师,还记得那年您给我补课的事吗?”一位穿着朴素的老太太问道。
“记得,你叫马兰花。”父亲说道,“那时候你家住得远,每天走五里路上学。下雨天我总怕你们几个女娃娃走夜路不安全,就留你们在教室写作业,等雨小了再送你们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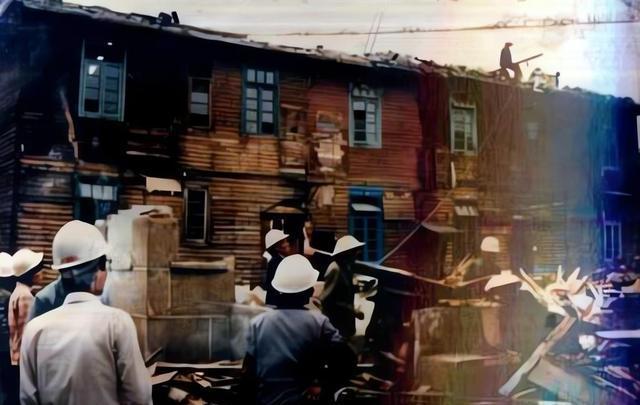
听到这里,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马兰花,正是她的闺名。
“老师……”婆婆的声音颤抖着,她一步步走下楼,等到了菜摊前,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原来,三十五年前,父亲是镇上最好的中学物理老师。那时候学校条件艰苦,没有实验器材,他就自己动手制作教具。婆婆正是他的学生,还是班上物理成绩最好的女生。

“张老师,对不起……”婆婆哽咽着,“我、我真的不知道……”
父亲笑着摆了摆手:“都过去了。你现在是我亲家母,跟我还这么生分做什么?”
从那天起,婆婆对我和父亲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给父亲买了个结实的遮阳棚,每天变着花样给他送饭,还特意去学了父亲爱吃的几道菜,红烧肉、葱花饼、韭菜盒子……

“你爸最爱吃红烧肉。”婆婆一边切肉一边跟我说,“那时候学校伙食差,他总把自己的肉偷偷夹给我们女学生,还说‘女孩子要多补补’。”
我好奇地问婆婆:“您以前真的不认得爸爸吗?”
婆婆叹了口气:“认得,怎么会不认得。但我总觉得……总觉得张老师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让女儿来做收银员呢?后来才知道,是我太势利了。”
几个月后,父亲的菜摊成了小区最热闹的地方。老人们总爱聚在那里,一边买菜一边和父亲聊天。他们谈天说地,从过去聊到現在,欢声笑语不断。退休的老教授会带着手写的物理题来请教父亲,退休的老医生会给父亲把脉开方子,退休的老厨师会教父亲新菜的做法。大家都说,在张老师这儿买菜,不光能买到新鲜蔬菜,还能收获快乐。
有天下午,我下班回家,看到父亲的摊位上多了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今日特价:小白菜2元/斤,西红柿3元/斤,韭菜2.5元/斤。”那熟悉的粉笔字,工工整整,一笔一画都透着严谨。我忽然明白,为什么父亲总说卖菜比教书简单,因为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他的教育事业。
教育不只在课堂,也可以在生活的点滴之间。他教会了老人们如何挑选新鲜蔬菜,教会了年轻人如何精打细算,更教会了我的婆婆,如何放下偏见,真诚待人。
每天傍晚,夕阳西下,我总能在阳台上看到这样一幅画面:父亲坐在婆婆给他买的藤椅上,周围围坐着几位老人。他们聊着过去的事情,笑声在晚风中飘荡,与菜市场的各种味道交织在一起,却让人感到格外温暖。
婆婆会在这时候,端着她新学会做的糖醋排骨下楼,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张老师,您尝尝我做的。保证比学校食堂的强。”
父亲接过碗,笑着说:“兰花啊,你的厨艺真是越来越好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切,心中感慨万千。夕阳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仿佛要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那里有轰鸣的火车,有黑板上刚擦掉的粉笔印,有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少年。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并非一定要在这里摆摊,他是在等,等着那些曾经的学生,等着那个曾经的马兰花,等着让所有人明白:在真诚和善良面前,所谓的城乡差距,不过是一道可以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痕迹。
那么,您觉得父亲的“办法”究竟高明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