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爵制度中,内外封爵存在显著差异。对内封爵主要面向国内臣僚,而对外则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境外政权。对内封爵包括正一品王、从一品嗣王和郡王,其中正一品王的地位最高,授予宗室、外戚等群体。对外封爵则更为复杂,常使用国王、四平王等特殊称号,主要用于册封朝贡国君主或有一定实力的藩帅。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对内封爵与唐代“二典”所载并无太大差异,而对外封爵则体现了宋代独特的政治需求。

对内封爵的体系相对稳定,从宋代初年就已确立,而对外封爵则随着外交政策的变化而调整。特别是宋代强化中央集权后,境内藩帅的封爵逐渐减少,但西平、南平两王仍用于册封夏州李氏和交趾等政权。此外,宋代在册封甘州回鹘和于阗时,使用了可汗王、黑韩王等特殊称号,这些称号在对内封爵中未见使用,反映出宋代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灵活策略。

宋代对命妇封号有明确规定,王的妻子被称为“夫人”。根据《宋史·职官志》,曾祖母、祖母和母亲分别被封为国太夫人,妻子则被封为国夫人。然而,这一规定的具体实施时间并不明确,学者龚延明认为它可能是另一道诏令的内容。从实际案例来看,宋初已有王妻封夫人的实例,如太宗符皇后在建隆初被封为汝南郡夫人,后进封为楚国夫人。同样,太祖次子德昭的妻子王溥女也被封为韩国夫人。

宋代命妇封号的国名和郡名繁多,且分为大、次、小三等。即使是国夫人,也能细分为大国、次国和小国夫人。进封和改封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明堂、南郊大礼、新帝即位以及去世后追封等。例如,英宗第四子益王頵的妻子王氏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经历了多次进封,从嘉国夫人到潭国夫人,最终进封为越国夫人。这种封号的进阶不仅体现了宋代命妇制度的复杂性,也反映了皇族内部的等级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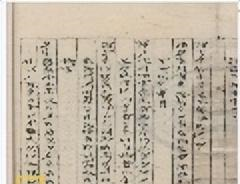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彰显尊贵,宋代命妇“兼封”制度逐渐兴起。所谓“兼封”,即封号中同时包含两个封国名,如益王頵的妻子王氏去世后被赠为魏越国夫人。这一制度不仅应用于高级女官、皇帝乳母、外戚等群体,还涉及到公主、宰相母妻以及同姓王夫人。通过兼封,宋代皇室和贵族试图在封号中体现更多的尊荣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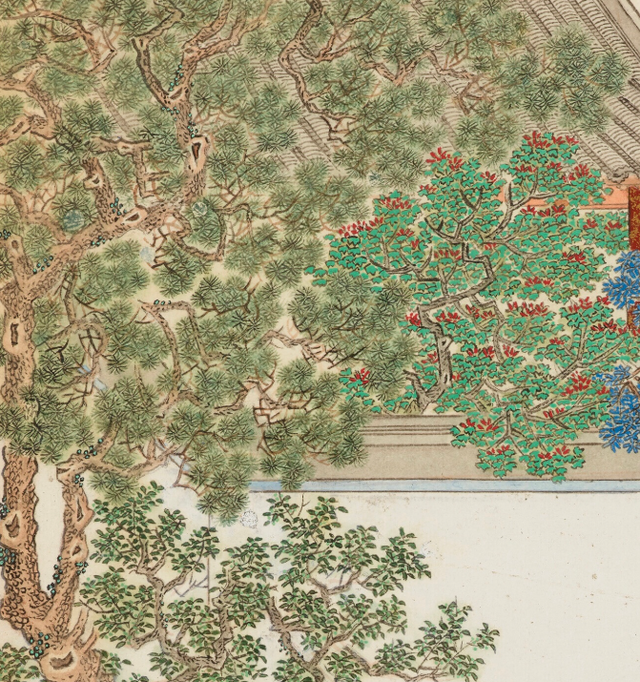
在宋初,妃号的使用非常谨慎,尤其是皇太子妃和皇妃的封授。与唐代不同,宋代皇太子妃并不属于命妇之列,而国夫人则属于命妇。真宗在位时,曾有意降低仪制,因此并未正式册立皇太子妃。直到钦宗时期,宋代才出现了第一位皇太子妃朱皇后,这距离唐代皇太子妃的册立已有三百多年。这种谨慎的态度反映出宋代皇室对妃号的高度重视。

宋代四位宗室出身的皇帝——英宗、孝宗、理宗和度宗,在处理尊崇本生父母的问题上采取了特殊的封号制度。他们的生父被封为王,生母则被封为王夫人,兄弟则被封为嗣王,奉祀生父。这种尊崇方式不仅体现了孝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宗室内部的权力关系。例如,英宗在位时曾通过“濮议”讨论尊崇其父母的方案,最终确定了称亲而不追崇的策略。南宋孝宗时期,仿照英宗的“濮议”,最终确定其生父子偁为高宗兄,追封为秀王,生母张氏为秀王夫人。

从唐代到宋代,封王之妻的封号经历了从“妃”到“夫人”的演变。宋代命妇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反映了皇族内部的等级秩序,也体现了对外交政策的灵活应对。尽管唐代前中期王妻封妃是主流,但宋代普遍采用“夫人”封号,并通过进阶、兼封等方式进一步彰显尊贵。这种制度的变化,既是对历史的继承,也是宋代政治文化独特性的体现。

汉朝军队北抵瀚海而还
中国汉字的总数有四、五万个,然而大多数人,在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面的生字表,学习到的汉字,只有两千多个,这只占汉字总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好在这两千多个汉字,都是生活当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常用汉字,因此,并不太妨碍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的阅读和观看,令人奇怪的是,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里面,为什么没有生字表,为什么不教初中、高中的学生,学习更多的汉字,照这样下去,除了在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面的生字表,学习到的两千多个常用汉字之外,其它大多数的汉字,恐怕会渐渐失传,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熟练的,掌握和书写出几万个汉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