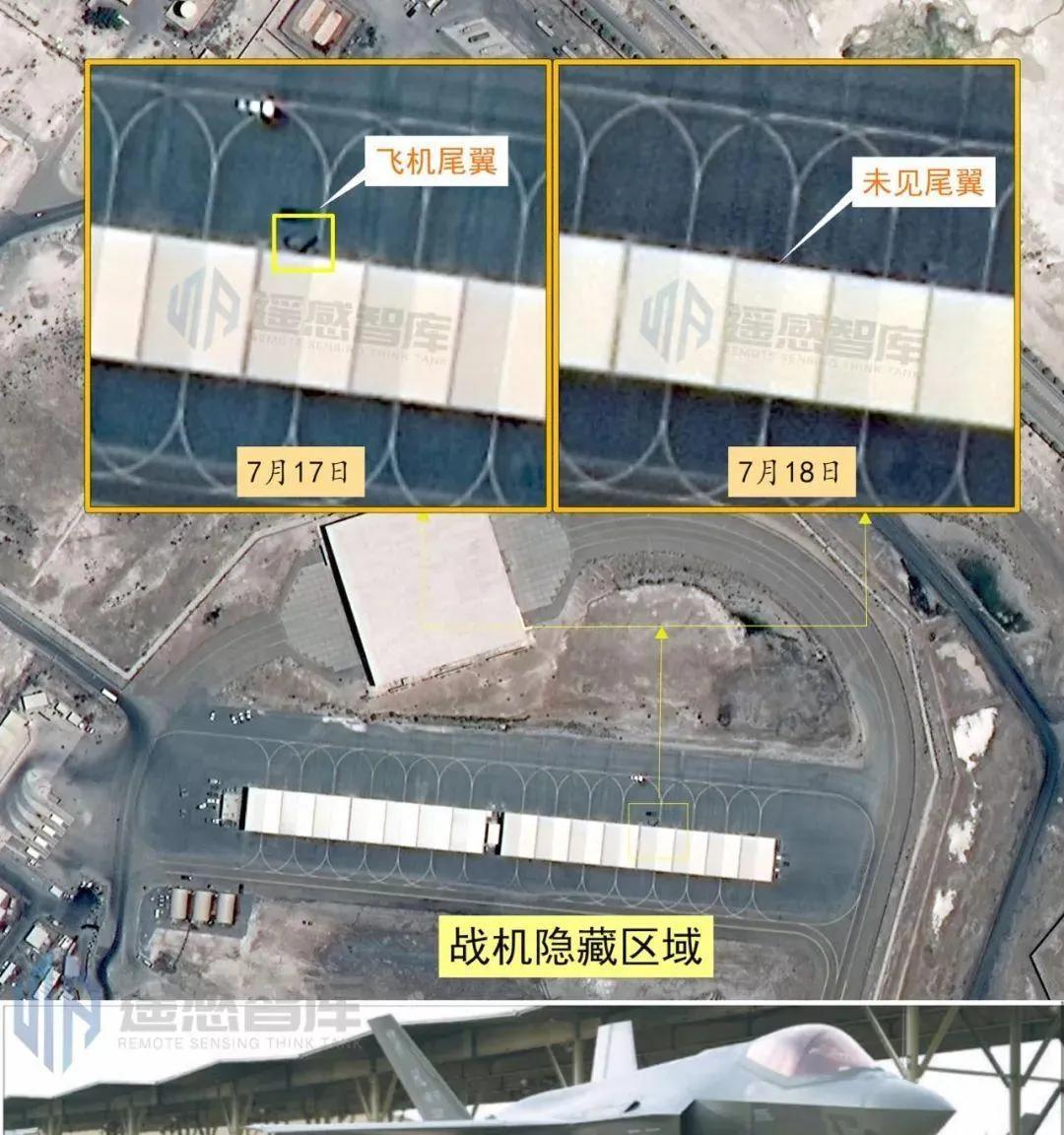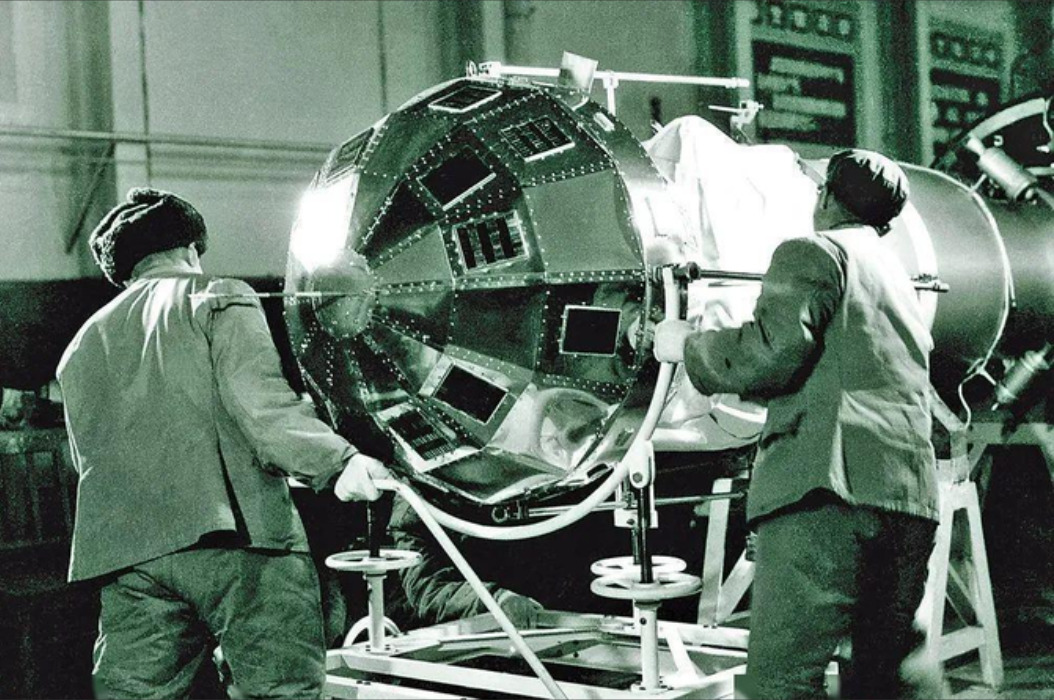2006年,以色列坦克大举进攻黎巴嫩,在路过中国维和工兵营时,突然袭来几枚火箭弹
2006年,以色列坦克大举进攻黎巴嫩,在路过中国维和工兵营时,突然袭来几枚火箭弹,竟当场将军营值班室摧毁,3名战士炸成重伤!营长罗富强冲进弥漫的硝烟,看到扫雷参谋周峰右肩的伤口深可见骨,弹片只差一点就穿透胸腔,另外两名士兵的脸上、额头上也满是血痕。这已经是半个月内营区第三次遭袭,之前的炮弹总落在附近,这次却精准砸向值班室,联合国承诺的战况通报始终没到,战士们只能躲在掩体里猜测下一次爆炸的时间。更让人揪心的消息从希亚姆哨所传来。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中校所在的观察站,被以色列战机投下的炸弹直接命中,废墟下还埋着另外三名外国观察员。34岁的杜照宇本可以撤离。冲突升级时,联合国缩减哨所人员,他把唯一的撤退名额让给了女同事,自己留下继续记录交战双方的火力数据,最后通话里说要让世界看清真相。以色列战机投下的炸弹像长了眼睛,精准命中飘扬着联合国旗帜的哨所。印度维和士兵冒着炮火冲进废墟,发现杜照宇的蓝色贝雷帽被鲜血浸透,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观察报告。我国多次要求归还烈士遗体,以色列却以“战场混乱”为由拖延,直到四国联合施压才松口,嘴里还念叨着“误炸”,仿佛那面醒目的蓝色旗帜是透明的。营区里的伤员刚能下床,杜照宇牺牲的消息就传开了。战士们默默擦拭着被弹片划破的五星红旗,防空洞里的灯光映着他们通红的眼眶,没人说话,只有墙上的维和誓词格外清晰。不久后,扫雷排爆小组接到任务,要为联合国车队清理道路。装甲车刚到纳古拉港口,就遭到不明武装扫射,子弹打在车身上噼啪作响,他们还击后才得以继续前进。白天,战士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烈日下排雷,汗水顺着头盔往下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晚上就在防空洞里整理地图,标记出安全路线,供后续部队通行。冲突结束后,杜照宇被追记一等功,他的照片被挂在营区最显眼的地方,旁边是那面带着弹孔的联合国旗。罗富强每次路过都会驻足,想起那个把生的机会让给别人的年轻人。回国那天,运输机穿过云层,战士们抱着杜照宇的骨灰盒,看着下方渐渐远去的黎巴嫩土地。曾经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地方,此刻只剩下断壁残垣和未爆的地雷。多年后,周峰肩膀上的疤痕还在,阴雨天会隐隐作痛。他给新兵讲起那年夏天,总说维和不是简单的站岗,是明知危险还要站在炮火里,为和平撑开一把伞。就像杜照宇日记里写的:“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见证战争,是为了让更多人不用经历战争。”这句话,刻在每个维和战士的心里,也刻在黎巴嫩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