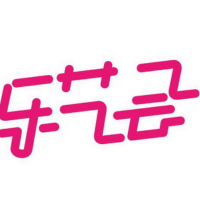复活的南宋妙馔
沈嘉禄
近年来,闽菜馆在魔都不声不响破圈而出,品味闽菜(民间也叫福建菜)在吃货圈里已是一个时髦的“小确幸”。闽菜主要是指福州菜,包括厦门、泉州、漳州、潮州等地的风味,后来也融入了一些客家菜。上海的闽菜是外来移民在一百多年前带进来的。福建商人驾着大福船乘风破浪一路北上,最终在十六铺登陆,带来了砂糖、靛蓝、木材、洋酒等等,从上海运走了棉花、丝绸和瓷器。企业家有商务酬酌,就必须打造消费场景,闽菜的兴盛与福建商人在上海的作为有关。民国以后,闽菜馆在上海多了起来,因为被时代洪流淘汰的外省士绅官僚纷纷来上海租界避乱。身处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少不了吃吃喝喝,闽菜馆的设置也是为他们服务的。陈伯熙在1919年的出版《老上海》一书中说:“闽菜馆之名大噪,士大夫商贾之请客者,意非此种菜馆不足以表盛馔。每筵之价,需十金以外。”最早开张的闽菜馆是汉口路上的小有天。著名诗人、书法家李梅庵(清道人)寓居上海期间大请三六九,小请天天有,便是小有天的常客。话说某天喝高了,大笔一挥,为店家写了一副对联:“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有了清道人的加持,小有天便“生涯大盛”。此后还有别有天、受有天、新有天和中有天。当时官场文苑请客,新派的吃西菜,老派的吃闽菜。新闻界老前辈严独鹤先生在《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社会调查录之一》一文中说:“中有天设于北四川路宝兴路口,而去年新开者,在闽菜馆中,可谓后进。地位亦颇偏仄,然营业甚佳,小有天颇受其影响。其原因由于侨沪日人,多嗜闽菜,小有天之座上客,几无日不有木屐儿郎。自中有天开设以后,此辈以地点关系,不必舍近就远,于是前辈先生之小有天,遂有一部分东洋主顾为中有天无形中夺去。”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有点意思,侨居虹口一带的东洋人是闽菜的粉丝,作为“后浪”的中有天生意大盛,小有天就被推倒在沙滩上。1927年定居上海的鲁迅先生也是闽菜的粉丝,他搬到景云里的第一天晚上就携亲友团去中有天吃饭,庆祝乔迁之喜,后来他在中有天经常请朋友吃饭,或受朋友请吃。上世纪三十年代,闽菜居然也吸引了杜月笙的注意。吃惯本帮菜的他也特地去小有天涮了一顿,大加赞赏,想必小费给得十分海派。1949年后闽菜馆在上海已经难得一见。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黄浦区饮食公司在南京东路组建了一家闽江饭店,招牌菜式有佛跳墙、红糟肉、闽生果、八宝布袋鸡、淡糟墨鱼梳、炝煎鱼条、生炊芙蓉蟳、七星鱼丸汤等。数十年来在南京路当国际饭店陪衬的金门大酒店(在我小时候改名为华侨饭店),以粤菜、潮菜为特色,兼营闽菜,他家的红糟鸡、焗沙茶鸡、豉汁牛蛙、白炒响螺以及佛跳墙别饶风味,值得一尝。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去吃了,不知道他家的闽菜还有没有。国庆节前我应高文麒兄的邀请去华润万象天地的闽和南·欢席试味秋季菜。闽和南是福建石狮绿岛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绿岛海鲜酒楼在东风浩荡的潮涌之际创立,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条件下,筚路蓝缕,孜孜以求,终于获得“穿在石狮,食在绿岛”的良好口碑,也很快成为全球500家最佳特色餐馆中国绿色餐饮名店,在《舌尖上的中国》《城市一对一》等专题片中亮丽出镜。闽和南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在深圳、福州、南京、上海都设有不同主题的分店,上海的主题是“精致闽南融合菜”。闽南菜是闽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了泉州、厦门、漳州等闽南地区的菜肴,与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菜肴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当天的晚餐由总厨周金水主理,冷菜有蒜椒汁沾八爪鱼、安海土笋冻、石狮五香卷。此前我在台州菜馆吃过八爪鱼,想不到闽菜中也有,蒜茸与辣椒的加持,使小海鲜的鲜爽清脆更加突出。让不少上海食客望而却步的土笋冻也换了一件马甲,调味后冻成一方块的“大理石”,切片装碟,蘸着自制酱料吃,比传统的小碗装更易为人接受。石狮五香卷经油炸后外脆里酥,色泽金黄,香气十足,喜欢炸猪排的上海人一吃就会上瘾。









沈嘉禄,《新民周刊》主笔、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作品曾获1990年《萌芽》文学奖,1994年《广州文艺》奖,1996年《山花》奖,1991年、1996年《上海文学》文学奖。2004年出版《时尚老家具》和《寻找老家具》,展现经典老家具的不朽魅力,引领读者在古典与时尚之间穿梭往返,开启了西洋老家具的文化鉴赏之窗,成为那个时代喜欢西洋老家具人们的必读之书。他也爱好收藏,玩陶瓷与家具,但他更愿意被人当做一位美食家,以一名上海老饕自居。

沈嘉禄绘画作品

沈嘉禄绘画作品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图文均由作者提供
特别鸣谢老有上海味道公微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