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丹东开往平壤的国际列车驶过鸭绿江时,我特意把脸贴在车窗上。对岸新义州的稻田里,十几个穿着灰布衣裳的农民正弯腰插秧,他们身后是整齐排列的稻草人,这一幕像极了三十年前我老家插秧季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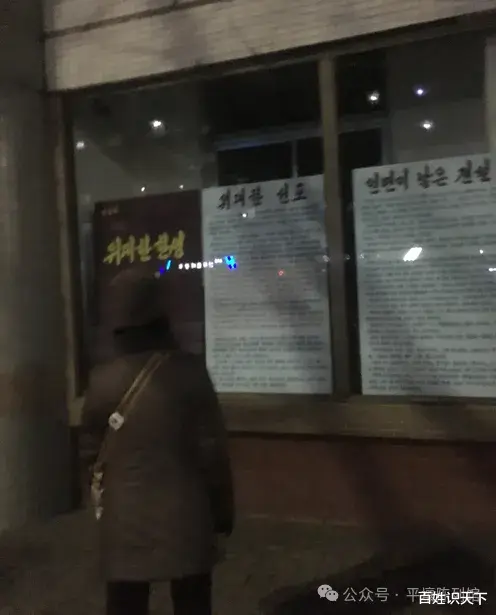
"每个生产队都有任务指标,超额完成就能多分口粮。"朝鲜导游金同志用流利的中文介绍时,我恍惚看见父亲在煤油灯下拨算盘算工分的画面。那是1982年的冬天,我家堂屋里堆着生产队刚分的红薯,母亲把最大的几个偷偷埋进灶灰里,等夜里烤给我们兄妹解馋。

朝鲜农村至今保留着这种集体劳动模式。清晨六点,村口的大喇叭准时响起《金日成将军之歌》,男女老少扛着锄头走向田间。合作社的会计会记录每个人的劳动量,年末按工分分配粮食。平壤郊外的顺安合作农场里,60岁的朴大爷告诉我:"去年我们队超产15%,每人多分了30公斤玉米。"
但当我问及年轻人是否愿意留在农村时,朴大爷沉默了。他身后的土墙上,"用我们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语已经褪色,墙角堆着的化肥袋上印着2008年的生产日期。

在开城郊外的村庄,我意外发现了朝鲜农村的"财富密码"。村民李大姐悄悄把我拉到屋后,掀开草帘:二十平米的菜地里,辣椒、白菜长得油亮,竹笼里还有三只肥硕的母鸡。"这些都能拿去农贸市场换钱。"她压低声音说,眼角却带着笑。

朝鲜政府允许每户保留30坪(约100平方米)自留地,这片小小的土地成了农民的钱袋子。凌晨四点,平壤统一市场的摊位上就摆满了带着露水的蔬菜。我亲眼看见一位阿妈妮用两筐西红柿换了三卷卫生纸和半斤猪肉,又用剩下的钱买了孙子想要的铅笔盒。
这种物物交易让我想起八十年代老家镇上的"黑市"。父亲曾用攒了半年的鸡蛋票换回一台二手收音机,被奶奶骂了三天"败家子"。如今朝鲜农民也在相似的夹缝中寻找生机,有人甚至发明了"移动菜摊"——把自家产的泡菜装在背篓里,沿着铁路线叫卖。

从新义州到平壤的铁路沿线,每隔几公里就能看见持枪士兵把守的检查站。"没有通行证,农民连隔壁村都去不了。"导游的话让我想起父亲锁在抽屉里的那叠介绍信。1985年他第一次去省城,村委会开的介绍信上盖了七个红章。
在平壤火车站,我遇见一群戴着头巾的农村妇女。她们像三十年前进城卖山货的母亲们那样,紧紧攥着粗布包袱,蜷缩在站台角落。开往南浦的列车进站时,人群突然骚动,有个妇女的包袱散开,滚出几个煮鸡蛋——那是她带给城里亲戚的礼物。
朝鲜的户籍制度比我们曾经的"农业户口"更严苛。农民想获得城市户口,要么考上大学,要么参军提干。沙里院市郊的崔大哥告诉我,他弟弟在部队立了三次功才把全家户口迁到城里,"现在住着国家分的公寓,但月月要给老家寄粮票"。

元山海岸的清晨,我在渔村看到了最魔幻的场景:十几个渔民踩着凤凰牌自行车,后座绑着铁皮桶,里面装着连夜捕捞的小银鱼。他们要在七点前赶到二十公里外的农贸市场,赶上海产品最紧俏的早市。
这种二八大杠组成的"物流链",恰似九十年代中国乡镇的"倒爷大军"。不同的是,朝鲜渔民交易时总要警惕戴红袖标的市管员。我在市场角落目睹过一场"猫鼠游戏":卖苹果的大婶突然卷起麻布,转眼间摊位就变成了一堆空筐——原来她望见了市管员的自行车。
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去年朝鲜修订了《农村经济发展法》,允许合作社用超产部分换取农机具。在黄海北道的谷山郡,我见到了朝鲜农村第一台私人拖拉机。主人金哲浩骄傲地说:"这是用三年攒的1500公斤玉米换的,现在我能帮别家耕地赚柴油钱。"
夜幕降临时,我站在大同江边望着对岸的乡村。零星的灯火中,隐约传来手风琴演奏的《春香传》。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长年轮。当我们的新农村早已驶入现代化快车道,朝鲜的田野上,老牛车仍在沿着父辈的车辙缓缓前行。那些在自留地里弯腰劳作的背影,那些藏在背篓里的希望,或许正是变革的前奏。就像四十年前安徽小岗村的那纸契约,谁又能说今天的朝鲜农村,不会在某个黎明破茧而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