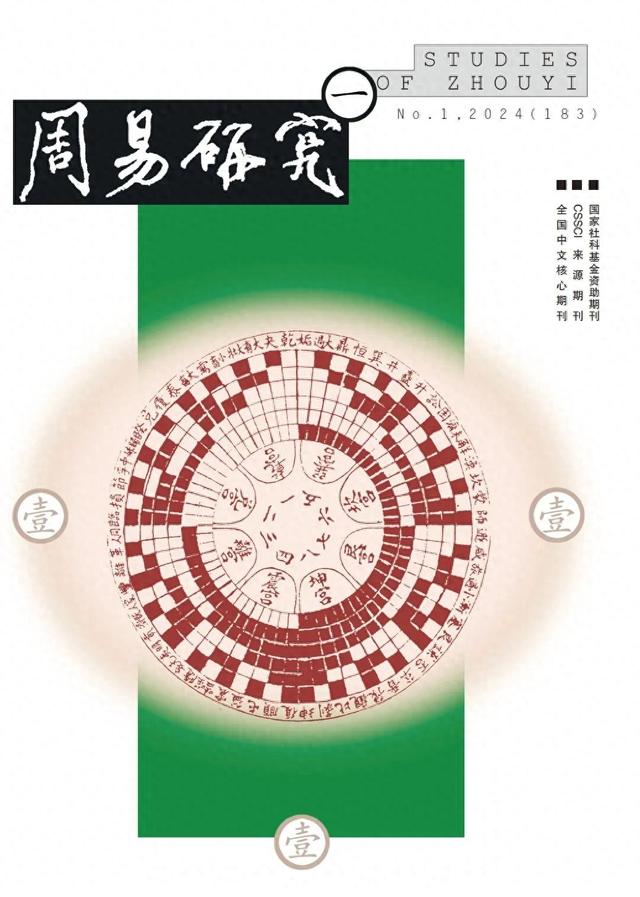
摘要:感通与视觉之辨是《庄子》的重要论题。作为《庄子》文本与义理的双重开端,鲲鹏寓言鲜明地展现了作者对视觉的抑制和对感通的追寻。具体而言,鲲鹏与蜩鸠分别代表了感通式存在方式与视觉性存在方式,扬鲲鹏、抑蜩鸠的思想旨趣在于以与物相感的共在式生存超越视觉性的对待式生存,并以基于感通的一体化思维超越基于视觉的对象化思维。进而言之,在视觉扩张的现代社会,超克视觉中心主义成了哲学家的重要关怀。在这一背景下,《庄子》的感视之辨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奠基于视觉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有助于思考并实践一种基于感通的与物共在的可能性。与物相感共在既不是宰制万物,也不是离弃万物,而是既守护着万物,又守护着自身,与物两不相伤而达至逍遥之境。此外,《庄子》感视之辨所展现的具体性以及对自身的反思与辩护对当代哲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关键词:《庄子》;《逍遥游》;鲲鹏;感通;视觉中心主义
正文超克视觉中心主义是现代哲学的重大关切,这一关切不仅是理论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深,视觉中心主义对人类命运的安置所展现的效果愈发显明:一方面,它使得人类获得了对世界的系统理知,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它使得世界不断被表象化,使得一切不能被视觉规训的东西被排除在正当性之外,从而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置于视觉的监控之下。在这一背景下,从视觉批判的角度诊断现代社会成了现代哲学的一股思潮,从“全景敞视监狱”到“景观社会”,从“视界政体”到“媒体奇观”,现代思想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并且希望超克视觉中心主义的消极性。为了实现这种超克,西方哲学家如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常常返归古希腊这一西方文明的源头,试图通过时间上的间距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并由此重思一种新的可能性。然而,现代视觉中心主义正是在古希腊思想尤其是在柏拉图思想中生长起来的,因此,通过对古希腊思想的批判性考察,能否开出一种非视觉中心的可能性始终是待定的。故而,超克视觉中心主义不仅需要时间上的间距,还需要空间上的间距,一种异古希腊思想的传统能为相关的反思提供思想上的活力。与古希腊思想不同,中国传统思想“经历了一个自觉抑制视觉、统摄听觉的过程”,进而“具有明显的味觉中心主义特征”。【1】通过检讨中国传统思想的味觉亦即感通特征,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经典世界与日常世界的思想观念,无疑能够为超克现代社会的视觉性提供理论资源与实践指引。
《庄子》思想中的感通与视觉之辨正是中国哲学“自觉抑制视觉、统摄听觉”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当下,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视觉问题在《庄子》哲学中的重要性【2】,然而,从感视之辨的角度切入《庄子》的系统研究尚且阙如。本文将立足这一角度对《庄子》开篇的鲲鹏寓言进行诠释,为系统阐释《庄子》哲学的感视之辨奠基。在具体阐释之前,需要做一些方法论上的说明。如多数学者所认可的,鲲鹏寓言的开端意义不仅是文本上的,更是义理上的。【3】不过,当下学者对开端性的解释一方面局限于由郭象、支遁之争所确立的论域,亦即局限于“心”“性”等范畴,另一方面则困束于诸如“自由”等近现代哲学的主题。由此,论者常常忽视鲲鹏寓言所展现的《庄子》所思的基本生存经验。如陈少明教授说:“尽管情节独特,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囿于文本字面信息,这小大之辩,不过就是大小、高低、贵贱、是非这些非常世俗的二元对比的价值模式的生动展示而已。”【4】在他看来,是由于郭象等人的阐发,《逍遥游》“小大之辩”才免于流俗的教诲。固然,郭象的注解有其哲学上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庄子》文本的遮蔽。因此,探究鲲鹏寓言的意趣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悬置郭象等人的阐释,回归《庄子》所刻画的独特情节,解放被历来阐释遮蔽的“文本字面信息”。本文将顺着这一思路回到《庄子》文本,着意于对鲲鹏寓言做现象上的描述,从而揭示出《庄子》鲲鹏寓言所展现的超越视觉而追寻感通的思想旨趣,并进而探讨这一旨趣的当代意义。
一、鲲鹏图南景象的非视觉性鲲鹏图南的景象如同一幅画作,展示着作者独特的视觉经验。在由观看而得的意义上,这一景象是视觉景象,就如同画作是视觉艺术。但是,《庄子》所展示的视觉经验却不是视觉性的,即它并不意指一种拉开距离使所看者对象化的旁观,相反,该景象中的诸要素处处表现着对视觉的抑制与对感通的追寻。
鲲鹏生于北冥,海运时节背负青天,以适南冥。在《庄子》的刻画中,鲲鹏栖息于由北冥与南冥、大海与天空共同构成的整体性方域,在这个方域中,“北”与“南”所意指的并不是单纯空间意义上的方向,而是嵌入在鲲鹏生存场域中的方位。方向是纯形式性的,方位则只有连接着存在者的生存才有意义,因此,在《庄子》的表述中,“北”与“南”总是关联着“冥”这一生存之域。“冥”即晦暗之色,用以指大海的色彩,其与表天空之深青色的“苍”共同凸显了鲲鹏生存之域的幽昧特征。与柏拉图洞穴喻所展现的对光明的向往不同,《庄子》强调鲲鹏生存之所并非一览无余的光明之地,相反,它幽暗、昏昧。【5】从用词来看,相比于“苍”,《庄子》更喜欢用“冥”,《庄子》中有“玄冥”“窈冥”“冥冥”“混冥”“甘冥”“颠冥”“冥山”“冥伯之丘”等讲法。【6】纵观《庄子》,“冥”意指天地的本然色调,万物居于天地之间,即是“居于窈冥”(《天运》)。“冥”之昏昧不同于“光”之显耀,万物在“冥”中生存、观看不同于在“光”中生存、观看,与后者所体现的视觉张扬相反,前者体现的是自觉的视觉抑制。【7】
如同鲲鹏景象中的空间并非纯粹的形式空间,该景象中的时间也不是纯粹的量化时间。根据《庄子》的描绘,大鹏“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庄子》又引《齐谐》【8】云:“鹏之徙于南冥也……去以六月息者也。”郭象以“息”为止息之意,云:“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庄子集释》,第6页)但结合下文“以息相吹”来看,此解恐不确。陆西星云:“去以六月息者也,与下文‘以息相吹’之‘息’同,谓气息也。人以一呼一吸为一息,造化则以四时为一息……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于后天为巽,正气动风起之时。”【9】因此,“六月”当指六月之时。“海运”“六月”标识着大鹏南徙的时间,这不是纯粹量上的时间,而是关联着存在者自身运作的生存意义上的时间。这种类型的时间有“时”而无“间”。“时”之有“间”意味着“时”可以被截断,而“时”的可截断性根植于人的主观意图。人以自身的意图来截取“时”,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做事以及人类历史所处之“时”皆有其“间”,正因为有“间”,事是一件件的,史是一段段的。在《庄子》的刻画中,大鹏南徙乃大鹏感海运之“时”而进行的自然的、没有意图的运作,其生存之“时”自不会有“间”。换言之,鲲鹏的生存之流没有间隔、没有区分,不能被截断。因此,鲲化、鹏徙皆不能被视为做事,同样,鲲鹏的运作也不具有历史性。不过,鲲鹏所处的无“间”之“时”也不能被理解为同质性的平铺,而应当被视作带有节奏的延展。天空、大海的运行有其节奏,大鹏正是感此节奏而南徙。概而言之,在《庄子》的思想世界中,“时”虽无“间”却有“节”,“时”之“节”既是天地运行的节奏,也是鲲鹏生命的节奏。
鲲鹏栖居于如此这般的方域与时节中,并在其中展开自身的生存。在鲲鹏景象中,“化”“运”“徙”标识着鲲鹏、天地(海)的运作【10】,鲲之化、海之运、鹏之徙并非不相干,而是以感的方式相连接。《刻意》篇描述圣人之行,云:“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同德”“同波”指圣人与阴阳为一体,“感而后应”即感知着阴阳的变化而有所应和,“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中的“迫”与“不得已”不应当视作迫于外部压力而屈己从人,其所强调的是圣人的行动并非出于主观意图,而是以感的方式随着周围生存境况的变化而有所行。成玄英云:“迫,至也,逼也。动,应也。和而不唱,赴机而应。已,止也。机感逼至,事不得止而后起应,非预谋。”(《庄子集释》,第541页)成玄英以“机感”释《庄子》之“不得已”虽有后世佛学意味,但无疑注意到了“不得已”与“感”的密切关联。就此而言,“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不同于《庄子·天下》所论慎到“推而后行,曳而后往”意义上的“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后者完全抛弃自我,前者只是拒斥对象化的自我。在《庄子》的视域中,惟其如此,自我才能处于本真意义上与物相感共在的存在状态,是为圣人之行。《刻意》所描绘的圣人之行与《逍遥游》所刻画的鲲鹏之行在实质上相通。褚伯秀云:“‘怒而飞’者,不得已而后动之义。‘怒’犹勇也。为气所使,勇动疾举,有若怒然,非愤激不平之谓也。凡物之潜久者必奋,屈久者必伸,岂厌常乐变而为此哉?”【11】《刻意》“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的讲法是概括性的,《逍遥游》“怒而飞”“海运则将徙于南冥”的讲法是对《刻意》讲法的具体化,两者都指向了基于感通而行动的精神旨趣。
在《庄子》中,感通与天道相连。《刻意》将圣人“感而后应”的生存方式刻画为“天行”,即基于天道而行动。《逍遥游》开篇称“南冥”为“天池”,“汤之问棘”一节又称“穷发之北有冥海者,曰天池”,即又以“北冥”为“天池”。从修辞上说,前后互见的文笔有助于避免平铺直叙。从内容上说,“南冥”“北冥”都为“天”所规定。“天池”之“天”不是天空意义上的天,“天池”不是天上之池,在这里,“天”是形容词,用以刻画北海、南海以及栖居于此的鲲鹏及其运化的本然的、非人为的特征。“穷发之北”一语也表明了这一点,“穷发”意指辽阔荒远之所、人际罕至之地,同样突出了鲲鹏生存场域的非人为的天的维度。
感通总是意味着多者之间的相感,在这个意义上,感通标识着共在。感通式的共在不同于视觉性的对待。前者是合乎本然之天的运作,后者是人为创制的结果。正是在共在的维度上,《庄子》反复谈及鲲鹏生存中尤其是大鹏南徙时的那些相伴的要素,比如《齐谐》中谈到“水击”“抟扶摇”“六月息”。这些要素都不应被理解为大鹏南徙的限制性条件,而应理解为大鹏运作的本质性要素。对大鹏而言,这些要素不仅不是南徙的阻碍,所谓“莫之夭阏”,而且恰恰是这些要素使得南徙成为了可能。在以上所列举的三要素中,“息”的意义格外重要,“息”即气息,它具有使生物以感通的方式相沟通的功能,所谓“生物之以息相吹”。“相”突出的是生物感通的交互性,正是这种交互的特征提供了共在之中的平等、齐一的可能性。
二、随鲲鹏而思:对视觉性认知的拒斥在刻画鲲鹏南徙的同时,作者或直接或间接地随着鲲鹏而思,这些思考如同鲲鹏图南的景象一样展示出了非视觉性的特征。视觉性的认知重旁观、重形式、重精确、重实证,《庄子》所示范之思则不同,这些思考立足于感通,强调思者与所思的一体性,反对确定的形式,反对精确的量化,有意营造出不可实证的境况。换言之,这种思考不以对象性的认知为目标,其所追求的是对以相感共在为特征的生存的领会。
《庄子》对鲲鹏之大的描写展现着对精确性测量的抵制。作者极力描写鲲鹏之大,两言“不知其几千里”。这既凸显了鲲鹏及其栖息之地的广大,为下文“小大之辩”张本,同时对“不知”的强调意味着人有限的视觉经验无法窥测鲲鹏的形体,更无法絜度天空与大海的体量,而且就鲲鹏之生存而言,其形体及生存之域根本无需测量。【12】
拒斥实证性追问的意图则着重体现在《庄子》对《齐谐》的引用上。成玄英认为引《齐谐》是为了证实鲲鹏之事,云:“庄子引以为证,明己所说不虚。”(《庄子集释》,第5页)但《庄子》明确指出“《齐谐》者,志怪者也”,如果是为了证实,何以强调其离奇的特征?因此,真实情况应与成玄英的理解相反,引《齐谐》并强调其“志怪”是为了指明鲲鹏之事乃是怪异之事,是寓言,故而不能以实证的眼光去求鲲鹏之实,此即钟泰所谓“曰谐曰怪,明其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欲读者之忘言而得意也”【13】。从这个角度讲,郭象“鲲鹏之实,吾所未详也”“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庄子集释》,第3页)的论断不离《庄子》之义。要之,《庄子》描绘鲲鹏景象不是为了让读者探求一种客观的、实证的关于鲲鹏的知识,而是要让读者以感的方式对寓言之意有所领会,要随寓言而思。在《逍遥游》首章中,从“天之苍苍”至“而后乃今将图南”的内容可以视作《庄子》对这种思的具体示范。
从“天之苍苍”至“亦若是则已矣”是《庄子》之思的第一层示范。《庄子》对深青色是否是天本身的颜色有所疑问,他设想大鹏在九万里高空向下看是否能够解答这个疑惑,这个设想的本质在于想象自身处于大鹏的处境。在《庄子》看来,对于这种超脱人类经验的问题,想象也无法解答,“亦若是则已矣”表明大鹏大概也有如此这般的疑问。因此,对待这类问题,阙疑是必要的态度。
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至“而后乃今将图南”是《庄子》之思的第二层示范。此处要思的是大鹏为何要飞至九万里而后再向南迁徙,《庄子》解答的基本思路是联系日常经验,同时仍然尝试通过想象置身于大鹏的处境之中。这里面有两个信念:首先,一个存在者显现于外的存在特征总是与其生存处境有关,理解他者的生存离不开对其生存处境的追问;其次,不同存在者的存在特征不同,但在基本经验处总是相通的。基于这两个信念,《庄子》相信通过对自身经验(人之舟与水)的反思能够理解他者的生存(鹏之翼与风),理解的关键在于,既要联系自身的基本生存经验,还要以想象、移情的方式体会他者的生存境况。这种理解意味着接纳,意味着承认他者存在的合理性。
概而言之,《庄子》所示范的运思不是视觉性的,不是对象化地追问关于鲲鹏的客观知识,亦不是将鲲鹏看作异己的他者加以事不关己的旁观、审视,《庄子》之思奠基于感通【14】,其目标在于领会鲲鹏的生存,表现着对他者的宽容与接纳。基于感的运思,重视基本的生存经验,重视想象、移情,重视感知不同存在者所处的不同境况,并且相信万物在生存上相感相通,相信领会他者的可能。这种运思与蜩鸠之思形成鲜明对比。
三、沉默与言说:蜩鸠的出场及其与鲲鹏之别除形体外,蜩鸠在何处不同于鲲鹏?向秀、郭象认为二者性分不同,后来学者多认为二者心境不同,这些解释自有其义理旨趣,但其中已经夹杂了后人的“心”“性”目光。因此,探究蜩鸠与鲲鹏之异,应当直面文本。
回到文本,蜩鸠不同于鲲鹏的要点在于两者的在场方式不同。鲲化、鹏徙是自然地转化、运作,即以感的方式与他者共在,在运化与共在中,鲲鹏保持着沉默,并且无情、无思、无知。蜩与学鸠则不然,蜩鸠以哂笑与言谈打破了鲲鹏的静默,哂笑指向其轻蔑的情态,言谈意味着有所运思、有所认知。因此,与鲲鹏之沉默及无情、无思、无知相反,蜩鸠不仅主动地言说,而且有情、有思、有知。进而言之,沉默与言说之别指向了天人之辨。
在《庄子》的视域中,天不言而静默,《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静默并不意味着没有声音,而是说没有人的言谈与议论,人之“言”“议”“说”根本上不同于自然之声。《齐物论》讨论人言与鷇音是否有别,云:“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虽是疑问语气,但从上下文来看,《庄子》明确认为人言不同于鷇音。此外,《庄子》中涉及对道的言谈时,常常表示真正的体道者并不言谈,言谈者即使是阐明大道之人也已经落于下乘,如《知北游》“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章,知分别问道于无为谓、狂屈、黄帝,无为谓“不知答”,狂屈“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黄帝则答知之所问,但在黄帝看来,只有无为谓才是真正的体认天道者,狂屈近似,而其自身终与道相远。因此,在《庄子》中,天之静默与人之言谈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区别,由此反观《逍遥游》鲲鹏之沉默与蜩鸠之言谈,不难看出,这里面的分别既不是性分之别,也不是心境之别,而是天人之别。
更为具体地讲,在《逍遥游》首章的语境中,天人之辨表现为感视之辨。蜩鸠云:“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在“汤之问棘”一节中,斥鴈云:“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这里的关键是两次言谈中都出现的“我”,“我”是蜩鸠与斥鴈观看大鹏南飞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其运思的关键。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我”并非一般性的人称代词,而是指处于物我、人我等两两对待关系中的自我。【15】从感官的角度来说,“我”突显的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视觉性的存在方式。在《庄子》的视域中,这种对象化、视觉性的“我”是非本真性生存的根源所在,故而《齐物论》有“吾丧我”之论。
蜩鸠、斥鴈皆固执于“我”,试图由“我”出发去认识“彼”。在“我”的视觉性生存中,“彼”与“我”拉开了距离,进而与“我”相分离,既成为了认知上的对象,也成为了生存上异己的他者。“我”只能远远地观看、审视,却不能感“彼”之生存,既失去了感通的兴趣,也失去了感通的能力。故而,蜩鸠困惑于“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斥鴈困惑于“彼且奚适也”。实际上,蜩鸠、斥鴈的困惑,《庄子》在上文已经给出了相应的回答。大鹏向南飞翔,乃是感时节而动,并不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大鹏之所以高飞九万里,乃是因以大鹏之形体,必至九万里方能南徙。在《庄子》看来,唯有通过想象、移情之感思方能领会大鹏的生存,蜩鸠、斥鴈所进行的出于“我”的外在式的观看必然无法理解大鹏。因此,蜩鸠、斥鴈的困惑固然与它们有限的形体相关,但根本来说,乃是其视觉性的存在方式所造成的。
对于无法理解的异己之“彼”,“我”遂加以哂笑、嘲笑。蜩鸠、斥鴈之“笑”与《老子》第四十一章“下士闻道,大笑之”之“笑”相似,都是一种精神姿态,其所表现的是“我”的不以为意的轻蔑之心以及对所嘲笑者的生存上的拒斥。在这个层面上,蜩鸠、斥鴈之“笑”也就是《秋水》篇的鸱之“嚇”。鸱不能理解鵷鶵的生存状态,遂把鵷鶵看作对自己生存构成威胁的他者,故而采取“嚇”的方式以守卫自己的腐鼠。蜩鸠与斥鴈同样无法领会大鹏的生存状态,在其眼中,大鹏之行是异于自己之行的怪异之举,只有在精神上拒斥大鹏的行径,才能在现实中安于“决起而飞”“腾跃而上”,方能心安理得地固守“我”的生存。在视觉性的生存中,一旦“我”与“彼”拉开了距离并且“我”不能理解“彼”,就常常会导致对“彼”的蔑视与拒斥。《逍遥游》末章里,惠施把对自己无用的大瓠视作废物,损害之,抛弃之,所谓“为其无用而掊之”,在精神层次上,惠施之“掊”如同蜩鸠之“笑”。
对于蜩与学鸠基于“我”而外在地看“彼”的做法,《逍遥游》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其云:“适莽苍者,三湌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在这里,《庄子》并没有对“适莽苍者”“适百里者”“适千里者”进行价值评判,其所要表达的仅仅是每一个存在者都有各自的生存境况,境况不同,则外在的生存表现也不相同。仅是基于自己的视域,外在地对比不同存在者的生存表现,并不能领会他者的生存。具体而言,如果仅仅外在地对比“三湌而反”“宿舂粮”“三月聚粮”,就不能真正理解他们为何这么做,只有理解他们各自“适莽苍”“适百里”“适千里”的处境,才能理解他们的行动。这里的论述与上文《庄子》所示范之思是一致的,都表达了对存在者生存境况的重视。而蜩与学鸠基于“我”的视觉性运思与此正相反,因此其不能理解这番道理,故而《庄子》感叹“之二虫又何知”。
四、小大:形量、认知与生存《庄子》感叹蜩与学鸠之无知后,便进入到小大的话题,提出了“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命题。一般认为,“小知与大知之异本质上是时间量级的不同,时间量级的不同造成了生存论视野的不同层级”【16】。这一论断的关键在于将“小知”与“大知”、“小年”与“大年”的区别仅仅理解为量上的区别。然而,如果这里涉及的仅仅是量上之别,那么小不及大其义显豁,《庄子》又何必曰“奚以知其然”并加以解说呢?更为重要的是,《齐物论》云:“大知闲闲,小知间间。”成玄英云:“闲闲,宽裕也。间间,分别也。”(《庄子集释》,第57页)《外物》云:“去小知而大知明。”郭象云:“小知自私,大知任物。”成玄英云:“小知取舍于心,大知无分别。”(《庄子集释》,第928页)显然,《齐物论》《外物》两处涉及“小知”与“大知”的对比,都不指量上的分别,“小知”不仅不是“大知”的初级阶段,而且“小知”阻碍着“大知”的显明,所以《庄子》的态度不是扩大“小知”以至于“大知”,而是批判、超越“小知”,从而让“大知”自然显现。
实际上,在“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表述中,《庄子》对“小”“大”的讨论从形量上转进到了认知与生存的领域,“小知不及大知”侧重于认知,“小年不及大年”侧重于生存。《逍遥游》对两句的具体解说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首先,就知的层面而言,朝菌、蟪蛄之“不知”对应着上文“之二虫又何知”的“何知”。也就是说,朝菌与蟪蛄不知晦朔、春秋如同蜩与学鸠不知大鹏之行。根据上文的分析,不知是立足于“我”以求“彼”的对象化认知的产物,这种知的状态才是《庄子》所谓的“小知”,也就是成玄英所强调的根植于心的分别之知。值得注意的是,与朝菌、蟪蛄之不知相对,《庄子》没有正面提及冥灵、大椿之知的问题,实际上,这正与鲲化、鹏徙之无知无思相照应,冥灵、大椿只不过是依照天道自然地展开生命而已,这种无知无识才是《庄子》所谓的“大知”。【17】
其次,就年的层面而言,《庄子》以朝菌、蟪蛄为“小年”,其中确实有量的维度,但《庄子》没有直接称五百岁、八千岁为“大年”【18】,因此,“大年”不应局限于年量之大,其具体含义应联系“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来思考。彭祖以长寿而闻名,众人希望如彭祖一般长寿,是谓“众人匹之”,这种“众人”就是《刻意》中“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的“养形之人”。通过对形体的保养来实现生命的延长,是典型的外在对象化的养生之法,即视觉性的养生之法。但在《庄子》看来,彭祖之寿与冥灵、大椿相比是如此微不足道,在后者年寿的映衬下,“养形”的“众人”效法彭祖的做法显得非常可悲。合道的做法不是“匹之”,不是“养形”,而是《刻意》所说的“不导引而寿”,即不通过外在修炼形体的方式而实现生命的自然生长,这就是《庄子》多处强调的“尽其天年”(《人间世》《大宗师》《山木》)。因此,真正的“小年”不应仅仅指年寿之短,更多地应该指“匹之”“养形”的做法,真正的“大年”也不应是年寿之长,而是“尽其天年”的状态。如果说冥灵与大椿亦可称为“大年”,其所强调的不过是两者各尽天年而已。
无论是“取舍于心”的“小知”,还是基于“养形”的“小年”,都是视觉性在世的表现,与之相反,“大知”“大年”所指向的是感通式的与物共在的存在状态,其存在特征是无知无识地各尽天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强调“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从思想上来看,这里的讨论深化了上文关于鲲鹏与蜩鸠的对比,但其核心旨趣是一致的,都指向了感通与视觉之辨。因此,《庄子》最终将上述的讨论都归结为“小大之辩”。
五、《庄子》感视之辨的当代价值从感视之辨的角度来看,鲲鹏寓言的意义在于对照蜩鸠视觉性的生存方式,刻画了以鲲鹏为代表的感通式的与物共在的存在图景,在这一图景之下,空间、时间、历史、行动、言说、认知、情感、自我、他者等一系列生存要素都被置于新的论域,从而能对之进行非视觉性的反思。在鲲鹏寓言中,这些反思还较为初步,有待《逍遥游》后文以及整部《庄子》加以充实,不过,《庄子》拒斥视觉而追寻感通的思想旨趣已经在“此小大之辩也”的论断中展现出来了。就此而言,鲲鹏寓言所敞开的论域足够广阔,所确定的旨趣足够深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鲲鹏寓言不仅是《庄子》文本的开端,也是其义理的开端。
鲲鹏寓言所展现的感视之辨不仅对系统理解《庄子》全书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其所敞开的论域与所确定的旨趣为超克现代视觉中心主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哲学根源上说,现代社会的视觉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视觉中心主义,西方哲学家在不同问题域内都谈到了这一点,如德波以“景观”来界定现代社会,进而谈到“景观是西方哲学规划全面虚弱的继承者,这个规划是受观看类别支配的对活动的理解”【19】。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哲学所展现的对视觉的拒斥与对感通的追寻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重视视觉的传统。因此,若能创造性地转化、阐发《庄子》所展现的感通传统,《庄子》将会在现代社会展现出新的活力,为当下的理论与实践提供相应指引。
首先,《庄子》所示范的基于感通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奠基于视觉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对象化思维将所思看作与思者无关的他者,注重所思的形式,注重没有思者参与的事物的客观本质。因此,在古希腊传统中,数学与几何学被视作知识的典范。在鲲鹏寓言中,作者强调了鲲鹏之形处于变化之中且其体无法测度,这是对视觉性的数与形的明确拒斥,这一点《秋水》讲得更清楚,其云:“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对无形、无数者的追求不能再基于视觉,而需立足于感通。在《庄子》的视域中,问题不在于对象化地追问鲲鹏何以如此行动,而是置于鲲鹏之境地并随鲲鹏而思,这种基于感通的思不是拒斥思者参与的冷冰冰的旁观,而是注重思者与所思的一体性。这种一体之思不仅是领会所思何以如此,它同样包含着对所思的尊重与包容。当代社会,视觉化程度不断加深,数与形密切结合,万物被置于冷冰冰的观测与计算之中,进而被数字(数)与图像(形)联手宰制。因此,鲲鹏寓言所蕴含的基于感通的思维方式为当代人守卫自身的生活世界,避免其被视觉性思维无限渗透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与精神上的指引。
其次,《庄子》所示范的基于感通的生存方式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奠基于视觉的对待性生存方式。对待性生存以自我为中心,将原本的共在者看作与自身相分相离而可资利用的他者。在《庄子》看来,对待性的生存是视觉化的产物而不具有本原性,修道者应当通过“丧我”的实践而返归于原初的与物同在的“吾”之中。这种与物相感共在的状态被《庄子》刻画为“游”,与儒、墨、名、法、纵横诸家的游学、游说不同,《庄子》的游是无待之游、恬淡之游。游既不是为了增益自我,也不是为了改变他人,它以自身为目的,而无外在的目的性。有外在目的的行为,一旦目的达成,行为也就终止。游无目的,故而不会终止,因此,《逍遥游》倡言“以游无穷”。“无穷”不仅表示本真性生存境遇的广大无疆,而且也表示作为生存方式的游的无穷性。对在世者而言,只要生命未曾终结,那么就本然地、并且应然地处于游之中。修道者以此方式与他人、他物相感共在,不控制也不离弃,在无用之中达到两不相伤而皆有所游的逍遥之境。在视觉泛滥的当代,人与人、人与物乃至物与物都处于深度对待化的处境中,存在者之间相互工具化,相互榨取、消耗,以至于“人是目的”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就此而言,《庄子》刻画的基于感通的共在式生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为人们反思对待性的生存提供了批判的视角,而且为在世者提供了一种兼具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生存方式。
再次,《庄子》感视之辨所展现的具体性有助于推进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当代哲学研究。具体来说,《庄子》对视觉的拒斥与对感通的追寻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在鲲鹏寓言中,作者没有进行抽象的思辨演绎,而是不断返归到日常经验的深处,对在世者(鲲鹏与蜩鸠)的生存现象做出合乎其是的描绘。通过对寓言情节的精心安排,通过对日常语词的独特使用,《庄子》既刻画着又塑造着在世者的生存经验。进入20世纪,现代哲学不断展现出拒斥思辨而返归具体的趋势,近年来,杨国荣教授提出的“具体形上学”更清晰地展现了现代哲学的这一面向。就此而言,《庄子》感视之辨所展现的具体性与现代哲学重视具体而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旨趣相互呼应。因此,若能从感视之辨的角度系统地切入《庄子》,重视其所刻画的日常经验与生存现象,重视其所使用的日常语词及文本中独特的寓言情节,《庄子》将能展现出其与现代哲学的亲缘性,进而参与到现代哲学的话题之中,并且能为当代中国哲学话语的生长提供资源。
最后,《庄子》的感视之辨包含着自我反思,这有助于在当代社会重思哲学何为的重要问题。《庄子》的感视之辨并非令人从执迷于视觉转变为执迷于感通,相反,《庄子》反思了感通的限度并在此基础上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这一面向在《逍遥游》的鲲鹏寓言中尚不明显,其将随着《庄子》内容的不断展开而逐渐面目清晰。在《外物》的庄惠之辩中,面对惠子“子言无用”的批评,庄子谈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视觉总是展现出巨大的用途,万物只有经过观看而对象化之后,才能成为知性的对象与利用的工具。相对于视觉,感通总是显得无用。但是,在《庄子》看来,感通之无用为视觉之用奠基,所谓“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知北游》),对于思者来说,必须不断返归到根源性的奠基处探寻。不过,《庄子》并不认为这种探寻足以替代视觉的展开。《天下》篇刻画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状况,从感视之辨的角度来看,这一状况是春秋战国时期视觉化进程亦即理知化进程不断加深的表现。在《天下》篇中,作者历数了道术已裂之后的经史、诸子之学,并在这一背景下定位了庄周的学说。庄子之学既没有被视作通向道术未裂之时的学问,也没有被理解为一种总揽诸家之长处的学问,它仅仅被看作道术已裂而百家相竞时代的一种新的思与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对经史、百家之学的克服,但却不是简单的取代。进入现代,理知化进一步狂飙,视觉不断扩展其领地,以往属于哲学的诸多论域被越来越多的实证科学占领,重新反思哲学何为成为了哲学自身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庄子》对自身的反思与辩护对今人重思哲学何为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近些年,《庄子》研究蔚为大观,但相关讨论大多既受制于“心”“性”“自由”等超级概念,又受制于郭象、支遁等人确立的思考范式,因此,相关思考及表达所用之话语总是似庄而非庄。就此而言,若能循着感视之辨这条由鲲鹏寓言所展示的线索回归文本,重视经验与现象,解味语词与情节,《庄子》哲学定能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面貌。更为重要的是,由感视之辨切入《庄子》,不仅合乎《庄子》自身的内容与旨趣,而且能为超克现代视觉中心主义提供古典资源,进而在视觉泛滥的当代探索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可能性。
本文刊发于《周易研究》2024年第1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