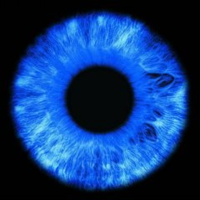“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在国际关系中被反复引用,然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结盟往往比纯粹的利益联盟更为稳固。价值观的契合能够求同存异,化解矛盾,最终实现共赢。相反,以利益为纽带的联盟,一旦利益发生冲突,轻则反目成仇,重则兵戎相见。从长远来看,普世价值观的力量远比强权更具说服力。

伊朗和以色列从盟友到仇敌的转变,正是这一论断的明证。二战后的中东局势如同中国战国时代的七国争雄,各国之间合纵连横,纷争不断。不同的是,域外大国的介入使中东诸强既是棋手,也是棋子,命运往往难以自主。沙特、以色列、伊朗、埃及、土耳其等中东诸强国皆是如此。本文将探讨伊朗和以色列是如何从曾经的盟友演变成如今的不死不休。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伊朗位于中东东部,以色列位于中东西部,两国相隔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多个国家,直线距离约1786公里。从地缘政治角度上看,他们天然应该成为盟友。首先,两国地理位置不相邻,符合“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其次,以色列无法对伊朗构成真正的威胁,以色列吞并伊朗是不可想象的,但伊朗理论上具备消灭以色列的能力。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被阿拉伯国家包围,战略态势处于劣势。尽管以色列在历次战争中屡战屡胜,但仍被迫采取“土地换和平”的策略。以色列在其巅峰时期曾控制近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为了和平,陆续向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归还了总计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历史上打了胜仗,军力上处于优势而割地求和的国家唯有以色列。


综上所述,伊朗和以色列成为朋友的需求远大于成为敌人,事实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友好期也长于敌对期。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1948年-1979年是伊以关系的蜜月期。二战结束不久,苏联曾经试图将土耳其和伊朗纳入势力范围,巴列维王朝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与美国结盟。以色列作为新生的国家,同样面临阿拉伯世界的敌视,并寻求美国的庇护。双方在共同的战略需求下走到一起,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个重要支点。两国不仅没有历史积怨,而且同为世俗国家,更容易在意识形态上找到共鸣。双方价值观相同,且有共同的利益,关系极其友好。

1950年,伊朗成为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大国。从1959到1971年,以色列所获得的80%至90%的原油供应来自伊朗。以色列则帮助伊朗发展农业技术。军事上,巴列维国王邀请以色列情报人员“摩萨德”帮助伊朗建立了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并邀请以色列专家训练伊朗军队。以色列对伊朗的情报优势,在巴列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二,其次,1979年至2003年是伊以关系的冷漠期。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霍梅尼领导的政教合一政权上台,伊朗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新的意识形态支柱,两国正式断交。然而,在两伊战争期间,双方却又展现出联系和合作的一面。整个两伊战争期间,伊朗通过第三方从以色列购买了25亿美元的武器,伊朗80%的武器来自以色列。以色列军事顾问还经常去伊朗活动,甚至到前线获取战争的第一手资料,评估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以便向伊朗提供更合适的武器。以色列还主动向伊朗提供了伊拉克军事力量部署图,以及124个可供伊朗空军打击的参考目标。为了防止伊拉克拥核,双方还深度合作。以色列提供伊拉克核设施的位置,伊朗空军首先派遣战机进行突袭,但轰炸造成的的破坏有限,于是1981年6月,以色列空军启动“巴比伦行动”,亲自出马补刀,炸毁了伊拉克核设施。三,2003年至今,伊朗以色列进入真正的对立期。萨达姆政权的垮台打破了中东地区的原有力量平衡,伊朗在失去制约的同时,也获得了扩张势力范围的机遇。伊朗积极输出什叶派革命,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抵抗之弧”,涵盖哈马斯、叙利亚政府军、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力量,对以色列构成直接威胁。

与此同时,伊朗的核计划也成为以色列的心腹大患。以色列多次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以阻止其获得核武器。双方在叙利亚、黎巴嫩南部、加沙地带等地区频繁交手,冲突不断升级。两国关系的恶化,既源于地缘政治的竞争,也源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更与伊朗谋求地区霸权的野心密不可分。综上所述,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经历了从蜜月到对立的复杂演变,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既有地缘政治的考量,也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主动恶化关系和发起挑衅的是伊朗,以色列是被动应对的一方。在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的泥潭之前,伊朗是主动进攻的一方,而以色列是被动防守的一方。伊朗通过支持代理人武装力量,例如哈马斯和真主党,对以色列进行间接打击,不断挑战以色列的安全底线。而以色列则受限于国际压力和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其回应往往局限于战术层面,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战略劣势。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场行动不仅彻底激怒了以色列民众,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由于涉及数十个国家公民的伤亡和绑架,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阿根廷、奥地利、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泰国和英国等西方世界,尤其是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的左翼力量,其影响力也因这一事件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泥潭,无力在中东地区有效发挥影响力,这客观上改变了地区力量平衡,为以色列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创造了条件。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的战略姿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报复行为,而是基于多重因素的战略选择。首先,国内高涨的民意为以色列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其次,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西方左翼力量的衰落,降低了以色列面临的外部压力。最后,地区力量平衡的变化,特别是俄罗斯的影响力减弱,为以色列提供了战略机遇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24年9月30日罕见地公开呼吁推翻伊朗教士政权,这进一步表明了以色列的战略意图。这一举动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宣示,标志着以色列可能正在寻求从根本上解决伊朗带来的威胁。内塔尼亚胡的讲话直接指向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并试图争取伊朗民众的支持,这预示着以色列未来可能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甚至不排除直接干预伊朗内政的可能性。综上所述,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虽然历史的纠葛和现实的冲突使得双方难以弥合分歧,但地缘政治的变迁和地区力量的重新洗牌也为未来带来了新的变数。以色列的战略转向,从被动防御到主动进攻,预示着地区冲突的升级和加剧。未来,双方关系将如何发展,地区局势将走向何方,仍充满不确定性,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