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叙利亚进入在美国看来都极不确定的时期。被联合国安理会列为“恐怖组织”并被美国财政部制裁的武装团体“沙姆解放组织”(HTS)成为叙利亚新的主导力量。该组织和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和包括“伊斯兰国”(ISIS)在内的武装组织对抗阿萨德政权,期间甚至和恐怖组织“东突”有着合作关系。虽然中美在中东存在地缘博弈和利益冲突,但防止被双方认定的恐怖势力借机壮大、甚至在叙利亚新政府任职,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特朗普今天说中美合作可以解决全球所有问题,其中应该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在新的地缘变局之下,为了维护地区稳定,中美可以在这方面开展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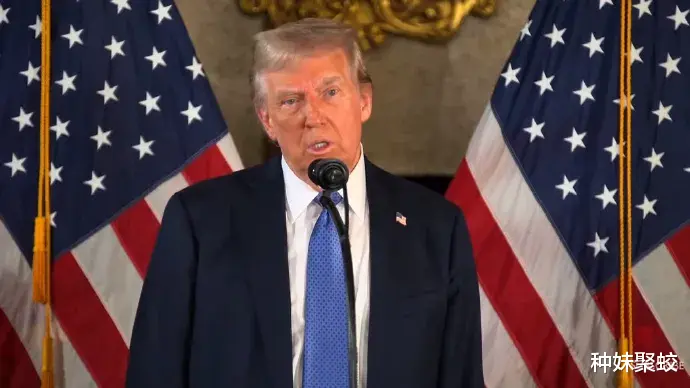
叙利亚变局符合美国预期,但阿萨德倒台的速度之快则令美国意外。即将执政的特朗普第一时间强调不介入叙利亚局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特朗普首次提到,土耳其策划推翻了阿萨德政权的行动,通过“控制”叙反对派,对叙利亚进行了“不友好的接管”。这是特朗普首次就“土耳其在冲突后的叙利亚扮演何种角色”发表评论。特朗普同时强调,叙利亚局势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目前,拜登政府的应对策略是继续强调在东北部和库尔德武装合作打击ISIS,并派出布林肯访问土耳其,影响未来的叙利亚新政府组成及政策。
针对叙利亚局势变化,王毅外长13日表示,中国对叙利亚长期奉行友好合作政策,从不干涉叙利亚内政,尊重叙利亚人民的选择。中方支持叙利亚境内尽早实现和平,落实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按照“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推进国内政治进程,通过包容性对话找到符合人民意愿的重建国家方案。未来的叙利亚应坚定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国际社会要切实维护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叙利亚的民族宗教传统,让叙利亚人民自主地作出决定。各国应当共同向叙利亚施以援手,推动解除多年来对叙利亚的非法单边制裁,缓解叙利亚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美都注重打击恐怖主义,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虽然美国主张全面对华战略竞争与对抗,但在新形势下,尤其是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双方的合作利益远大于冲突利益。

首先,中国无意在叙利亚取代其他国家在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力。
叙利亚变局的直接利益攸关方是土耳其、以色列、俄罗斯及地区阿拉伯国家。西方舆论将中国视为阿萨德倒台的利益受损者,这是一种误判。自叙利亚内战以来,中国就已经减少在叙利亚的投资。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和叙利亚和贸易与投资一直处于低位。2021年,中国企业对叙无新增直接投资。截至2022年底,中国企业对叙利亚直接投资存量仅为1324万美元。
双边贸易方面也处于下滑趋势,尤其是叙利亚对华出口微不足道。2021年,中国与叙利亚双边贸易额4.8亿美元,同比下降42.1%。其中,中方出口4.8亿美元,同比下降42.1%;进口0.01亿美元,同比下降3.6%。2022年,中国与叙利亚双边贸易额4.27亿美元,同比下降11.5%。其中,中方出口4.25亿美元(主要出口商品是织物、铁和橡胶轮胎),同比下降11.8%,进口224万美元(主要进口商品是肥皂、橄榄油和其他植物产品),同比增长74.7%。2023年1—6月,双边贸易额1.9亿美元,同比下降5.9%。其中,中方出口1.9亿美元,同比下降5.4%,进口71万美元,同比下降61.2%。
虽然叙利亚2022年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但目前尚无投资项目落地。这一方面和西方对叙利亚的制裁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叙利亚陷入内战多年,治理恶化、腐败、能源短缺、基础设施被毁,投资回报率差。虽然阿萨德政权多年来一直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伙伴,看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同俄罗斯的协同角色,但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并且及时评估和调整投资方向,降低整体风险。
其次,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稳定符合中美利益,反恐将占很大比重。
除了经贸与投资安全利益以外,阿萨德倒台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区安全局势出现的新风险。中国一直主张推动地区和解、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比如,呼吁加沙停火、促进伊沙和解和调解哈马斯和法塔赫等巴勒斯坦组织之间的分歧。如果叙利亚新政府组建不顺,各方势力填补权力真空,安全风险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影响中东地区整体稳定;二是确保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能够保障中国投资安全,包括参与叙利亚的战后重建项目等;三是反恐。叙利亚变天,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会借机发展壮大,伺机攫取权利,对地区周边安全构成威胁。12月8日,阿萨德倒台时,“东突”分子就曾发布视频,威胁袭击中国。

在三个方面,中美存在利益重合,其中反恐是最大的利益契合点。当前,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控制着叙利亚东部大片地区,被美国视为打击ISIS的合作伙伴。而ISIS的崛起和壮大则离不开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导致激进武装占领伊叙境内大片领土。“东突”分子也趁机渗透其中。美国应该汲取教训,在动用军事力量打击恐怖势力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同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等国的外交合作。奥巴马执政期间曾将打击ISIS视为中美“潜在共同利益点”,更注重合作的特朗普,理应在这方面更注重和中国的合作。
《外交政策》称,中国最大的关切是叙利亚境内的“东突”分子。在叙利亚境内的“东突”分子人数由百人至数千不等。中国可以施压新政府杜绝“东突”分子在政府机构任职,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将东突分子遣返中国。但叙利亚内战已经让该国GDP损失85%,只要叙利亚新的领导层愿意和中国重建经济关系,就应优先巩固和中国的合作,保护好中国资产,配合中国处理“东突”分子。
不过,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非常暧昧,一直有政治和舆论上的支持。比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借选举年打中国牌的背景下,撤销了对“东突”的恐怖主义组织认定。再次执政的特朗普是否会调整这一定性,值得关注。但中国必须在这方面提出诉求,寻求打击包括“东突”在内的恐怖主义势力的合作性博弈,强化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中美也可在全面战略博弈的背景下借此重构军事互信,避免误解并维持地区稳定。
最后,应对叙利亚变局,中美在地区和联合国层面也有机会合作。
就当前情况观察,被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HTS将在叙利亚新政府扮演重要角色,这就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国家同意通过相关提案,对HTS及其领导人穆罕默德·朱拉尼提供豁免,或从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当然,前提是要求该组织及其领导人与“基地”、“东突”等恐怖组织切割,摈弃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和政策意向。
另一个合作点是伊朗。阿萨德倒台后,伊朗处于决策的关键十字路口。在特朗普再次上台之际,伊朗是继续推进核项目还是和西方和解,关系到整个中东局势的走向。如果伊朗想要重构和叙新政府的关系,对抗美以,就有可能继续破坏叙利亚及整个中东的稳定。如果伊朗调整外交政策,降低阿拉伯国家对它的威胁认知,就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无论它如何做,都离不开外交上中国的斡旋和支持。
当然,特朗普身边的右翼势力不希望中国在中东议题上积累政治和外交优势,可能会阻挠这种合作。这就要看特朗普本人的利益取向和中国的外交发力。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的外交政策未必奉行孤立主义。如果特朗普想要从中东乱局脱身,避免卷入新的冲突,就离不开同地区国家及中国等大国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