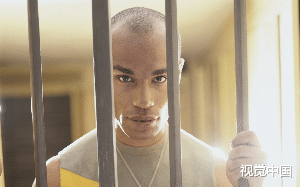我那民国出生的太爷爷,永远笑呵呵、慈祥百倍的模样。
甚至引来了电视台的人来采访他的长寿秘诀。
但是他不知道,长寿的秘密就再太爷爷身后的水井里,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千秋万代,一直一直活下去……
01
电视台的记者来古街采访,探访百岁老人裴有庆和他的老宅院。
采访画面中的裴有庆笑呵呵坐在太师椅中,隐约能窥见年轻时的意气风发,身后是青石铸成的高门大宅,写尽风霜。
“您认为,是什么能让您如此健康长寿呢,是吃什么进补,还是说……”电台记者单膝半跪在他身边,大声问道。
老年人耳朵不好,年轻人与之对话,习惯性调大音量。
裴有庆摆摆手:“你小点声,我不聋。我小时候是个孤儿,流浪,后来当兵、做生意……哪有什么好吃的补?就是高高兴兴的,放宽心,要与人为善……”
好多场面话,我在电视机前别过头去,不想看。
两个多小时后,我艰难地抱着一个骨灰盒从出租车上爬出来,再次回到这个被夕阳的暖光染成血红色的屋村。
长时间的颠簸,热辣的空气加上喧嚣腾起的尘烟熏得我胃里一阵阵犯恶心。
村口有人坐在老槐树下纳凉,听见声音,一个个的都往这边看,或坐或站,形成一幅动态的剪影。
老槐树似乎更茂盛了些,蓊蓊郁郁,盘根错节。冷眼看世人。
我跟这群人不熟,但是我想,每个村口应该都有这样一群老人吧?
他们冷眼看人来和去,这村里的任何一件八卦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和嘴。
我在一双双冷眼凝视下拉着行李箱,往记忆中“家”的方向去,远处若隐若现的老宅如同一个怪兽,枝枝蔓蔓盘根错节,像极了《聊斋》里女鬼的家。
要不是老爸一连打了十三个电话,甚至还把孝道搬出来压在我头上,我都不准备回。
“你太爷爷要不行了,你个嫡曾孙女都不出现,你这不是要打我的脸?”
我冷笑:“我要是出现,二叔三叔街坊邻居还要笑话你生不出个嫡曾孙,那不是更打脸?”
深秋的天气有些萧瑟,但四五十个男人、女人和小孩挤在一座院子里,也有些闷。
见到我,有个男人打趣:“呦!裴家大小姐回来了,赶快赶快,给人家让路!”
我不认得他,但是他那调侃的语言让我恶心。
我冷着脸,感觉自己被当猴看,偏我爹裴大海听不出好赖话,还怪我:“你这孩子没礼貌,咋不知道打招呼!”
“人家是大学生,哪看得上咱们?”
“咱村就这一个金凤凰,裴老爷子一去,家产还不都是咱们大小姐的?”
人群中传出一阵哄笑,这下连我爸都知道人家话里有话,涨红脸——谁叫他没儿子!
我太爷爷叫裴有庆,生于1910年,不光是裴宁,村里人看他,都如看古董一般。
裴家的旧宅门楣高大,雕梁画栋,只因为岁月的侵蚀而略显斑驳,更增添了厚重感,原本朱红的窗框已变成碎裂的粉红色,宾客从窗角的蛛网便能推断裴有庆晚年的寂寞荒凉。
屋里,太爷爷已经穿好了寿衣,睁着眼睛直直盯着屋内顶,唯有胸口间或往下一陷,方能看出人还活着,想要把体内的气都嘘出来。
嘘完了,人也完了。
旁边伺候的太奶奶神色悲戚,她穿着土布蓝褂,面色寡淡。
说是太奶奶,其实并不是我亲生的太奶。
她没有名字,唤裴周氏,比太爷爷小三十六岁,是他最后一房小妾,嫁过来那年才十三,花一样的年纪,当时裴有庆已年过半百。
02
前面的老婆都死得比较早,如今只她一个陪在裴有庆身边,也算是半个正室了。
裴有庆只有一个孩子,就是我爷爷,但英年早逝,留下的晚辈们跟着长辈有样学样,对无生养之恩且出身寒微的裴周氏都看做空气一般。
她如今惶恐难过,想来有一大半因老太爷离去后,她无一子半女,谁来赡养?何去何从?
我虽然同她不亲厚,但是有点同情她,挨过去轻声道:“阿太别太伤心,咱们活着的人得好好活,您岁数也大了,得保重自己身子……”
不知是不是这些晚辈从没人主动与她讲话,且说得如此贴心,裴周氏看向我的眼神里没有感动,反而充满震惊。
得,套了个没趣,算了吧。
正讪讪,忽然听见裴周氏用一种很急切的语气道:“我那边有几本旧书,都是老东西,你是大学生,可以看看,不然浪费了。”
我一愣,点点头,心想这老太太据说是不识字的,竟然还有藏书?
裴周氏提醒似的:“别忘了啊。”
我还想说什么,就被拉了过去:“还不快去看看你太爷爷!”
这老宅已荒废一半,家中其他人很少回来这里,旁的村邻也甚少来。
因为这里在特殊时期曾经做过会场,有不少人,包括我太爷爷在内都在这里挨过批斗,有几个受不住的,在厢房的梁上上吊了,我太爷爷是里面岁数最大的,那么一个又干又瘦的的小老头居然挨过了动荡的年月,而且熬过了后来的一年又一年。眼瞧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故去,心里作何感想?
然而当这老宅恢复买卖,太爷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回来,说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当年裴家就是靠这块地才兴家立业的,果不其然后来我的几个叔叔乃至我亲爹,做生意都挺顺遂。
不知是否有风水宝地的缘故?
但对这块宝地,村里人议论更多的其实是那些狐鬼传闻。
他们大多都从自家长辈口中听过关于太爷爷年轻时的传闻,随着长辈们离世,唯有太爷爷屹立不倒,那些传闻就越来越离谱,有人说他请神续命,也有人说他五鬼运财。
也有人说这里死过不少人,当年太爷爷的一位姨太太还是在这房子里难产而亡的,宅院里的女人们,怨气重。
更不必说在房梁上吊死的那些,那就是人人都知道的了。
这些传闻我打小就听,也不再害怕。二十多年不回,大约是从那件事起,我不愿意和这个名叫桃山村的村子再扯上关系。
那是我连回想都不愿意去回想的一件事,好像只要我不想,这件事就可以当做不存在。
再者,我毕竟算玄孙,便是爷爷如今已不在了,可还有父亲叔叔们在,老宅有什么事也轮不到我露面。
把骨灰盒交给二叔,他还有些不满意地掂了掂:“多少钱?”
“五万多。”
老爸作为长子嫡孙,从小被太爷爷捧在手心里长大,此刻悲不能自已,家里大小事宜,都交给二叔拿主意。
听到价格,二叔“啧”一声,“要说你们小孩子就是不会买东西,就这么个骨灰盒造价也就几百块钱,问你要几万,啧!亏死了!”
嫌弃地拿走了,也没提给钱的事。
前头老太爷还没咽气,后头因为骨灰盒谁掏钱而呛起来?
03
我丢不起这人。罢了罢了。
打小没怎么跟太爷爷亲近过,就当是尽孝。
一直到月上中天,老太爷还在榻上,忽忽悠悠喘着最后一口气,折磨得几个孝子贤孙心如刀绞,再熬下去不是办法,就由二叔做主,嫡亲的几个孙子留下,媳妇们和曾孙辈的先回去休息。
我穿过天井,却见方才一直不见的太奶奶裴周氏往东厢房的耳房里去了。
她是缠过小脚的,走路时背影颤颤巍巍。
耳房之前吊死过人,所以后来就改成了杂物间,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把陀螺掉进去,进去拿的时候还被太爷爷好一通骂。
太奶奶去做什么?
我委在东厢房,同几个女眷一起,并排躺在炕上。
月色如水般澄澈,四周一片安静,偶有秋虫啁啾,也失去了夏日的生机,变得拖拖拉拉,半死不活,如太爷爷在榻上喘息。
他这一生什么都经历过了,曾经拥有那样的泼天富贵,要离开想必舍不得?
屋子里渐渐响起了鼾声,躺在旁边的我妈妈也睡着了,她睡颜沉静,想必累坏了。
其实天还不晚,只是大家都累了。
才十点多钟,换在平时我还在加班,此刻也在工作群里看到同事们辛苦加班的背影照片,以及部门经理的单独约谈。
长长的一大条语音,我懒得听完,转文字看。
先说我工作不够积极,再说任务不够达标,核心思想就是你丫实习期没通过,被开了。
一直在担心的事有了结果,虽不是好结果,我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到底是自己毕业来的第一份工作,没有做好,难免怀疑人生,我抱着被子坐起来。
老宅的炕比较高,正对着偌大的窗户,正可以看到月色下庭院里的样子,我看到一个蓝色的背影穿过耳房紧闭的木门,不见了。
不见了!
我本来混混沌沌,现在在混沌中被吓醒,扑到窗台边细看,庭院里早什么都没有,可是那蓝色的背影确确实实如此清晰地印在裴宁的脑海中,让我觉得自己没看错,绝不是幻觉。
联想到老宅种种传闻,我赶紧缩回被子里,难道真的有鬼?
紧接着又自我安慰,这房间里这么多人,阳气也算重,鬼也未见得会来。
这么想着,迷迷糊糊就要睡着,只梦里总能听见起起伏伏的哭声,而且还是女人的哭声。
难道是太爷爷过世了不成?不对,若真的过世了,母亲必然会推醒自己,不会由着自己睡。
迷糊着眼往旁边看,我妈还躺在身边,背对着自己,鼾声均匀。
我把视线转回来,剧烈地哆嗦了一下——一个黑影趴在窗户上,正往里看。
那是一种,汗毛倒竖,寒意一瞬间从脚底直冲脑门的体验,如果有镜子,我想必能看见自己的每一根头发都吓得竖起来。
那黑影,是太奶奶裴周氏的样子。
七十多岁的她瘦,尖脸,皮肤干枯,因为过去的遭遇总是一脸苦相。她穿着蓝布褂子,隔着玻璃,整个上身和脸都贴在窗户上,就在我脚下的这一片窗户,往里看。
她离我只有一扇窗户的距离。
就像白天窗户反光,一定要贴的很近才能看到屋里陈设的那样,她往里看,浑浊的眼珠正对着我的方向,我生怕她打开窗户来捉我的脚。
04
身体猛地一震,大汗淋漓,天已大亮。
一场噩梦,我惊魂未定地坐起来,坐起来刚好可以看到院子外面围满了人,在明媚的阳光下,耳房大门洞开,就不见天日的房间此刻被阳光披上了一层令人晕厥的光晕,有什么东西被抬了出来。
刚想出门看个究竟,人群外围的老妈赶快把我推回来:“别看别看。”
“怎么了妈?”
“老太太没了。”妈妈话很匆忙。
混乱的场面,我没有见到,但“丧席”如约而至,或许这个词用得不恰当,只不过不是太爷爷的丧席,而是太奶奶的。
我也是从来往宾客的神乎其神的言谈中得知原来太奶奶吊死在耳房。
【八成是怕老爷子死了,儿女都不管她,哎呀,绝望啊!】人们这样说。
她死了,即便不受重视,但该有的丧礼也得有,何况她一死,众人忙慌慌的时候,不知谁一回头,居然看到裴有庆倚在门边上,浑浊的眼睛眼泪汪汪地往这边瞧。
吓了一大跳:“老爷子!你咋出来了!”
前一天晚上还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几个亲近的孙子眼瞧着手脚都开始凉了,此刻居然能好好地、自己走出来,靠着门站着:“我命苦……白活这么长岁数,现在她也走了,以后没人陪我……”
老人的哭声在秋风中显得格外哀戚,那些原本给裴有庆准备的丧葬品全都给裴周氏用上——算是她这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我妈和几个女人给她收拾遗物,我负责打下手,收拾一些零碎。
这位民国时期的姨太太并没留下什么奇珍异宝,古朴的木质首饰盒里只有一枚已经氧化的银制胸针,和一张黑白老照片。
照片上的太爷爷还是年轻时候,梳三七分,油头粉面,丰神俊朗,端坐正中,旁边站着的女人想必是裴周氏,很清秀。她穿看不出花色的棉布旗袍,圆脸盘,弯叶细眉。
黑白照衬得人脸煞白,照片底部有一行小字:民国XX年,时间太久了,想来是放在手里摩挲了很多遍,字迹已经看不清楚。
这张照片也被当成了裴周氏的遗照——或许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老照片拍得不细节,眼睛处是两个黑黑的洞,我越看越渗人,照片里的女人似在盯着她看。
我觉得蹊跷,但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这么些年,爸爸和几个叔叔虽然不常回家,但每个月的定期汇款总是有的,老人的村子里花的不多,就算是老爷子真的没了,对裴周氏也不可能不管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