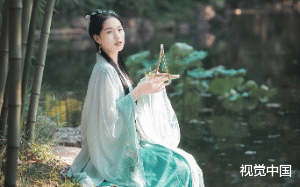我原是京都身份显赫的将门嫡女。
一封急报,将兄长与他麾下五千将士的死讯传回都城。
朝臣不问战事,只奏请天子处置兄长贪功冒进之罪。
阳春三月,圣人下令斩首冒死进谏的父亲。
此事祸及全族,府邸被查抄。
我流落街头,成了牙婆手中随意发卖的货物。
于是,那位与我定下姻亲的少年将军,花了三两银子,把我买回去做了妾。
1
三月回寒。
我亲眼看见母亲惨死中庭,烛光灯影,长廊深幽,丫鬟婆子发了疯似的逃窜。
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偌大的江府亡了。
「赖妈妈,她都这样躺了三日了,不会醒不过来了吧?」
唤作赖妈妈的中年妇人不甚在意地回道:「活着有活着的去处,死了自有死了的去处。」
她并不在意我的生死。
我本就是流放途中病重,被胡乱撇下的。
牙婆收下我,甚至没花一两银子。
我脑中混沌,接连病了几日,不甚清醒,耳边的声音愈渐清晰,可我就是醒不过来。
恍惚间,我又梦见了抄家那晚。
弟弟嘹亮的啼哭声犹在耳畔。
母亲将裹好襁褓的弟弟塞进乳母怀中,让她带着弟弟和我,逃得越远越好。
我已经十六岁了,家中除了哥哥,嫡出子嗣属我最大。
哥哥不在,出了事合该是我替母亲分忧。
于是当晚,母亲含泪让我离开。
我只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我这辈子都不会抛弃江家!更不可能抛弃你!」
然而上天狠狠惩罚了我的自以为是,痴心妄想。
我甚至不知,那时我是怎样被人从江府拖出来的。
眼前只余一片血色,鲜血自台柱门框下沿缓缓流淌、凝固。
赖妈妈说不在乎我的生死,但我活着她能多赚几两银子。
她差人每日给我灌粥,遗憾我依旧没有清醒的迹象。
2
隔日。
两个要好的丫鬟窝在这房间里躲懒,旁若无人地聊起当朝新贵周将军,说符阳县人才凋零,正有人马上举家迁往京都赴任。
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此时正身处离京都不远的符阳县。
当朝新贵周将军?
符阳县的周将军只有一位,儿时我曾唤他世伯,他和父亲早年间都是祖父手下的副将。
二人出生入死,携手抗敌多年。
父亲也是当初为救他,腿方才落下病根无缘沙场。
两家关系亲厚,我与周家公子更是自小定下姻亲。
除却我做公主伴读那两年鲜少归家,单论旁的,我和周景年也称得上一句青梅竹马、两情相悦。
我们的婚期其实早就定下了,我的嫁衣已绣好月余,我只等哥哥凯旋送我出嫁。
怎料横生变故,哥哥亡命沙场,京都家破人亡。
我同父亲一般,断然不信哥哥那样一个持重有谋略的将领会贪功冒进。
一定是哪儿出了岔子……
此前朝廷崇文抑武,致使如今武官只余寥寥几户。
圣人大发雷霆后,忽而感念江家汗马功劳,遂免去满门抄斩之罪,举家流放。
边疆战事告急,如今周家上位也算顺理成章。
可我江家枉死的性命又要如何算?
父母兄长枉死,弟弟流落在外,江家蒙受冤屈,遭百姓唾骂。
身为将门嫡女,我怎能病倒在这里?怎能在这样无人知晓的地方苟延残喘,了却余生?
我得活着!
我活着才能找到哥哥出兵中伏的真相,活着才能见到弟弟,活着才能为江家上下洗刷冤屈!
眼下,新贵周家,是我唯一的踏板。
3
又过了两日,许是我没半点苏醒的迹象,赖妈妈也不耐烦再养着我。
这日她不知从哪儿找来个胡商,要将我当尸体卖了,剥了皮,做成人皮灯笼。
我被小厮扛起,几下颠簸,让我的手脚渐渐有了意识。
小厮走出房间没两步,院里忽地冲出来一个半大的小丫鬟。
她「扑通」一声跪倒,恳求赖妈妈不要将我卖给胡人。
我的脑子依然不甚清醒。
赖妈妈拽着袖子甩开那姑娘,跟着啐了一口,随后揣着一两银子乐滋滋回了房间。
小丫鬟不知哪来的力气,死死抓着小厮,愣是被他拖到了门前。
小厮要上马车了,胡商走上前狠狠扇了她一耳光,周围百姓都围了上来,一时间议论纷纷。
小丫鬟哭喊着:「他们要带走我姐姐,他们要扒了我姐姐的皮!」
眼见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中,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少年肩宽腰窄,通身体态,丢哪儿我都能一眼认出来。
我与他堪堪对上视线,他神色一怔,立马拨开人群冲了过来。
胡商似乎也后悔花一两银子招惹了这样的麻烦。
所以他很干脆,顺理成章让周景年花三两银子买下了我。
我以为凭过往的情谊,在周家寻一方容身之所,供我回京都找到真相,为父母亲和哥哥报仇并不难。
然而我未曾想到,京都丞相府早已派了嬷嬷过来相看周景年,为的自然是她丞相府小姐和周家少将军的婚事。
江家虽今时不同往日,可说到底,我和周景年之间的姻亲还是在的。
丞相元鸿,当初就是他煽动群臣,奏请圣上下令斩首我冒死进谏的父亲。
这笔账我尚未与他清算……
4
暂歇周家的嬷嬷不知从哪儿听说周景年自坊间把我买了回来。
我与周景年定下的婚事,她也知晓。
于是就有了后头这些事。
嬷嬷明里暗里示意将军同将军夫人,我若留在周家,做个门客都是不安心的,除非……让周景年把我纳了做妾。
好像只有这样,才不会威胁到她家小姐入府后当家主母的地位。
在我看来,她是在执行元鸿的命令。
元鸿是想让我知难而退,顺便把江家踩入泥潭,狠狠羞辱。
他越这样做,越说明他心里有鬼。
元鸿如今在朝中如日中天,有江家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前,即便周将军愿为我做出反抗之举,我也万万承受不了他周家这份深情厚谊。
我大可一走了之。
可我偏不,妾又怎样?
只要随周家入京,早晚有一天,我会将元鸿拖下马,让他跪在我江家族人面前赎罪!
周将军自是相信江家的清白。
曾经我父亲对他舍命相救,甚至因他伤了腿无缘沙场。
如今为了找回江家的血脉,也就是我弟弟,他入京后不久就上奏,望圣人免去江家妇孺流放之罪。
武将无人,边疆告急。
朝臣给了皇帝一个台阶,他也就顺势下了。
我不知道弟弟的乳母是否知道赦免的消息,又是否会把弟弟带回京都。
思来想去,我仍觉得不妥,于是准备动身南下,亲自去把人找回来。
周将军长期驻守符阳县,对朝堂的尔虞我诈知之甚少。
当然,他也不屑与他们纠缠。
他觉得事情既然由边疆中伏而起,要说线索与真相,必然也只能是在战场。
他披甲上阵,许诺我定会为江家洗刷冤屈,争得公道。
5
送别周将军后不久,周景年与丞相府小姐订了亲,择日完婚。
他被留在了京都,升了官职却无实事,与待嫁的驸马无异。
将军夫人看在眼里,愁在心里。
她总来我这儿闲坐,喝完半盏茶后长叹口气,欲言又止。
明明忧心周景年的境遇,她却忽地扯上了我,兴许是觉得我的遭遇更惨,更需要倾诉。
就这样过了几日。
等不到南边来的消息,我毅然决然与周景年、将军夫人辞行,带着两名侍从驱马南下。
我与那些养在深闺的女子相似却不尽相同。
我朝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大户人家女子也会学这些。
骑射之术,她们大多只学得皮毛,我却因出身将门,自小就被祖父督促练习。
论骑射,恐怕连周景年也要输我一筹。
只是我并不精于武艺。
周景年放心不下,这才遣了两名侍从跟着我。
他本想和我一起南下。
可他要是走了,京都还不知会被元鸿那个丞相翻出怎样的浪花。
三日时间,我已路过数不清多少村落,约莫三四座城池。
其中有百姓安居乐业,但为一口吃食,将儿女贱卖至青楼妓馆的也大有人在。
夜间,街巷深处的黑色买卖更是层出不穷。
有人买下病危的妙龄女子,用小刀在其头顶活生生画上一个十字,再将水银从中灌入。
不消片刻,水银往下,自会一点点撑开少女的皮肉,先是脸,后是身躯,最后包括腿,足,外皮一并褪下。
那样撕心裂肺的疼痛,我偶然一次夜半外出查探时曾亲眼见过。
少女或许身上无病,是被拐来还是被发卖,尚待考证。
架子上血淋淋的一团,如果不是四肢被绑得死死的,我根本认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脱完整张皮的她还余了口气,只是哭也哭不出,喊也喊不出。
嗓子早嘶吼到发不出半点声响,我已经分不清她滴下的是泪还是血。
6
实在于心不忍,我给侍从使了个眼色,用银针结果了她,免去她余下的痛苦。
这样的工坊,光一座城池就有三四家。
他们大多把褪下的人皮包好,送往京都,制成人皮灯笼。
有市场,才会有人丧心病狂地做这些东西。
可京都到底是谁在购入人皮灯笼?
我给周景年去了封信,望他留意此事。
外敌当前,此时若是大安内部出了乱子,国危矣。
我对大安那些落井下石的百姓虽提不起好感来,可护卫大安,是哥哥一直以来的志向。
身为女子,游离在朝堂外,我也只能尽我所能。
我念的是家,国主若是有心,自不会让国分崩离析。
越往南走,我们见到的各类黑色买卖就越多。
身边两个侍从,几度想要动手杀了那些买卖人口的贩子。
可杀了一个,还会有第二个。
若他们真杀了人,摊上官司,不仅周家会有麻烦,弟弟流落在外的事,也会被有心之人知晓。
这天,眼见一个三四岁的孩童被拐到偏僻的角落,侍从正准备动手,我伸手拦了拦,沉着脸跟了上去。
因此,我见到了更荒诞的一幕。
房内是一个丹炉,桌上摆着各类脏器,方才拖进屋子的小孩,已经有人磨刀准备对他动手。
我忍无可忍,没法见死不救。
箭矢擦过丹炉一角,正正好刺在预备动手的那男人眼前。
他被吓了一跳,手上一松,刀具砸落在地面上。
我不敢细想,大安国境内若都是这样的恶事,乳母一个人带着弟弟,能走到哪儿去。
侍从去当地县衙报了官,想来此事有这样的规模,也免不了地方官绅放纵之罪。
报官不过是表面功夫。
7
我当即回到客栈修书一封,为周景年据此事拟了份草案。
他曾与哥哥推杯换盏,二人志趣相投,并非寻常男子不喜女子触及朝政。
心为大安之人,就无谓身份地位。
人皮灯笼、买卖脏器一案倘若上报,一方面可以让周景年特事特办,破了如今受人掣肘的僵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看皇帝对此事的态度。
毕竟我一路过来,所见所闻足以证明此案牵扯甚广,不出意外还会牵扯到堂上重臣。
圣人若弃百姓于不顾,江家的清白他又怎么可能在乎?
取证呈于庙堂,或是取证呈于年前退政还朝,如今仍留有余力的太后,只看他如何决断。
经过一番打听,我也终于从一个卖柴的孱弱少年那儿,得到了乳母和弟弟的些许线索。
辗转不过半日,我便在县城附近找到了少年所说的竹林隐居之所。
院内无人,竹叶纷落,簌簌叶片摩挲声中,我推开了紧闭的房门。
屋内毫无征兆地射出一枚暗器,我偏头错开,却仍被划下一缕发丝。
身后的侍从见此情形提刀跃起,我慌忙转身,抬手将他拦下。
竹色屏风之后,男色误人。
须臾,屋内之人穿好衣裳重新把门打开。
我闻声回头。
男人有一双桃花眼,眼角一颗小小的泪痣,乌鬓朱唇,脸部棱角分明,漂亮却又不失阳刚之气。
只是与周景年相比,这人身上似乎少了两分少年气。
想到方才的冒犯,我脸颊不免有些发烫。
无碍,好在我出行惯用男子装束。
「姑娘唐突,找在下可是有什么急事?」
他挑起折扇,似笑非笑地指了指耳垂,我不说话了。
8
卖柴的少年说,曾见过一个妇人抱着半大的孩子,坐上马车从这儿离开。
我询问男人事情原委,他倒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据他所说,是他帮了乳母一把,遣人将他们送往了骊国。
东边的骊国民风淳朴,也无战乱之忧,的确是避难的好去处。
来之前我只听说,隐居在此的是位富家公子,志趣高洁,说起来也是位乐善好施的大善人。
城中不少布匹粮食生意都经他之手。
他隐居在此,也算富甲一方。
与这样的人结交,不失为一桩妙事。左右弟弟性命无虞。
周景年亦在信中提及,他不日将率人南下,彻查人口买卖一案。
我暂时在这个小县城安顿下来。
想着张勉经手过这么多生意,手下侍从又走南闯北,关于民生民怨,尤其是人皮灯笼一案,他或许知道些旁人不知道的内情。
于是我投其所好,买了两坛老酒,意图从他口中问出些东西。
上回来这儿的时候,我没有细细打量,这会儿坐下细看屋内布局、物件,我忽然察觉有几分不对。
先前打听来的消息说,张勉是骊国人。
竹屋内确是骊国布局不错,只是他偏房里的那支玉箫,似乎不是寻常百姓家能有的。
年幼时,哥哥曾与使臣前往骊国友好交涉。
他归家时赠予我的那枚玉佩,上面带有骊国皇室的专属花纹。
骊国盛产玉石,玉制品本不是什么稀罕物件,外人一般不会留意骊人手上的玉石,即便留意了,一般也不认得上面的印记。
我有幸得哥哥垂怜,方才认得这云纹。
张勉的身份不言而喻,只是不知道他是骊国的哪位皇子?
他大费周章地潜入大安做生意,究竟是志趣,还是另有图谋?
9
「江小姐不喝?」
张勉眯着醉眼,往嘴里又灌了一杯。
看他这样子,也不像什么奸邪之人,人家好歹还救了我弟弟。
这样一想,倒像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我收起旁的心思,抿了口酒,问起他城中贩卖人口之事。
一开始他还遮遮掩掩,最后灌下一坛子酒,醉醺醺地倚在窗边,抬手指天,笑得像个傻子。
「你们大安,有人野心胜天。」
「……」
他果然知道得不少。
「说,你还知道些什么?」我有几分迫切。
我虽猜测哥哥出事与元鸿脱不了干系,但在获取确切的答案和证据前,我也不敢贸然行事。
窗外脚步声顿起,箭矢凌厉地直冲这个方向而来。
慌乱之余,我凭直觉带着眼前的醉鬼几个翻滚,幸运地躲过了那些致命的利刃。
来的这伙人蒙着面,这么大阵仗,总不会是冲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来的吧?
怎么看都像是这位皇子招惹了不得了的麻烦。
我松开手,起身讪讪一笑。
「各位兄台,误会,误会。鄙人路过宝地讨杯水喝,他就在这儿躺着,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小的就先告辞了……」
刚迈出一步,我才发觉另一只脚抬不起来。
回头一看,张勉这人竟死死抓着我的衣袍不松手。
我用力扯了两下,抬头对面前的杀手赔笑。
然而这衣袍像是长在了张勉手上,我扯不开,只好蹲下身去掰他的指头。
这群没耐性的杀手一哄而上,我只好使出了我的撒手锏。
白色的药粉一洒,我从靴中抽出短刃斩断衣袍,继而扛起张勉跳窗而逃。
为了救他,我连保命的绝招都用上了。
事后他要是不和我老实交代他知道的内情,我就把他丢进池子里喂鱼!
10
我背着张勉往山上逃,那群人追赶的声音紧随其后。
跑了不知多久,我再使不上半分气力。
前面就是一口深潭,我驻了足,也不管张勉听不听得见。
「好歹是皇子殿下,上天选中的人,气运应该比我好点。不过若是真死在这儿,这就是我们的命。」
说着我退后几步,准备一鼓作气跃进水潭潜逃。
然而下一瞬,我背上忽地一轻,腰间什么东西像被扯了一下。
我被身后之人往前一推,差点一个踉跄扎进潭里。
他又反手拽了我一把,猝不及防将我圈入怀中。
糟了,我的玉佩。
这枚骊国来的玉佩,因为意义非凡,我曾转赠给周景年。
我流落在外的那段时日,身上的旧物件早已被人搜刮干净。
进了周家后,周景年便将玉佩还给了我,以作念想。
「你的?」
张勉将手高高举起,阳光透过玉石,衬得上面的云纹更加清晰。
「见到姑娘的第一日,我就觉得这腰间的玉佩眼熟,竟是我骊国的物件。」
他低头看我,语气有些漫不经心:「话说回来,姑娘是如何得知我的身份的?」
这半晌杀手都没跟上,我逐渐回过味来,眼前的男人只怕打一开始就在装醉。
我在试探他,他又何尝不在试探我?
与知己相交,最重要的是开诚布公。
「我们算是知己吗?」张勉似笑非笑。
确实算不上,那就谈条件。
他饶有兴致地眯了眯眼,我直觉有些不妥,正想改口。
「可以啊,你嫁给我,我对你开诚布公如何?」
「什么?」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又不禁揣测,这人到底醉没醉?
11
深潭旁有水瀑,以至于我当时没有听见其他动静。
直至张勉抬起眼,一脸玩味地看向我身后。
我顺着他的视线回头。
周景年不知是何时站在那儿的,他拾剑肃立,衣袖上还沾着湿润的血迹。
原来身后那些甩不掉的尾巴,都是他处理掉的?
他上前两步,盯着张勉,面色略有些不善。
他一字未说,牵起我的手,将我护到身后,与张勉正面对上。
「不好意思,你来迟了,她是我夫人。」
周景年的眼神过于凌厉,以至于气氛变得有些剑拔弩张。
或许此时我该说些什么……
然而没等我开口,张勉忽然将视线放在我身上,眼底含着两分意味不明的笑意。
「江婉清,你哥哥只让我关照你,可从未告诉我,你已婚配啊?」
哥哥?
我一时愕然,在周景年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困惑。
「你认识我哥哥?」
张勉自怀中取出一封信,周景年正欲伸手接过,张勉抬手一避,神态自若。
「江兄写给我和婉清的东西,外人……不方便看吧?」
这两人像是杠上了。
张勉重新将信纸递给我。
周景年见状只抱剑侧向一边,别无二话。
我知道他被张勉气得不轻,可现在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一心只扑在那张泛黄的纸张上。
信上确是哥哥的笔迹。
一字一顿,一笔一画,都仿佛让我看到了他生前写下这封信时的模样。
信中,他言明在边疆驻守时发现了一些问题,恐涉及朝中重臣,这件事或许招惹不得,可他身为主将,又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他查了有风险,不查会给虎视眈眈的西南羌国可趁之机。
他为人子,为人兄长,更为一国将领,于是修书一封,望旧友留意大安朝中动向,必要时护一护江家。
只是张勉远在骊国,终究鞭长莫及,如今救下乳母和弟弟已是大恩。
12
哥哥在信中提及,日前他已将相关问题和线索理成一份册子,交由信任的人带回江家,待寻到关键证据,即可及时呈报圣上。
说到底,张勉虽然是哥哥故交,但他贵为骊国太子,终究不便让他知晓边疆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将看完的信递给周景年。
张勉只是挑了下眉,倒没再说旁的。
哥哥信中提到的册子,我从未见过。
我不知道是册子在中途遗失了,还是被父亲藏在了什么隐秘之处。
张勉又是否知道其他线索?
我与周景年对视一眼,他抿了下唇,往后退了一步,随即弯腰抱礼,放低了姿态。
张勉虚扶了他一把,两人都没说话,之前剑拔弩张的气氛已烟消云散。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张勉邀我二人回竹屋详谈。
半山腰处,跟进脏器案的侍从和去城外迎周景年的侍从两人齐齐守在那儿。
他们面前还有一位焦灼的少年。
两人拦着他,不让他上山。
我一眼认出他就是那日告诉我张勉住处的卖柴少年郎。
见到张勉,他的怒气和委屈都含在了那声公子中。
张勉与他说话,离得近,我还是隐约听见了皇子、暗杀、人没处理干净之类的话。
张勉伸手在虚空停了一下,随后回头看向我们,笑了笑。
他往我们这边走了两步,抱拳示意。
「实在抱歉,家中出了点事,我得回趟骊国,令弟我会护佑周全,只是……」
「无妨,我会保护好婉婉。」
周景年紧紧握着我的手,目光坚定。
张勉看向我。
我轻轻点了下头,他不禁摇头失笑。
这一刻,我莫名觉得张勉有点像我已故的兄长。
他曾经也这样挂怀我的安危与幸福……
13
一行人下了山。
张勉引我和周景年进了竹屋,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不知触及了何处的机关。
地面骤然出现了一个暗格,里面装着一个锦盒。
张勉将其取出,锦盒之中是一个小册子。
我心底有了大概的推测,只是不明白,这东西怎么也在他这儿?
哥哥的态度明确,断不会将国内之乱与外邦言说,即便他和张勉称得上是挚交。
「想来你父亲早做好了盘算,这册子就藏在令弟的襁褓之中。我无意窥探,亦不会乘人之危。」
我收下册子。
其上阐述了边疆军饷贪污之事始末,桩桩件件,条条框框,历历在目,骇人听闻。
正是因为这个东西,哥哥才会身陷囹圄,身首异处。
院外,我只觉得怀里揣着的小册重如千金。
这不止背负着哥哥一人的性命,更是追随他的五千将士因此而亡。
我满腹心事地翻身上马。
张勉站在院门处,扬声唤了我的名字。
我应声回头。
他将玉佩往前一掷,我伸手牢牢接住,随即蹙眉看他。
「江婉清,有朝一日,若是走投无路,你记得拿着信物来骊国找我。」
我深深看了他一眼,终究什么也没应,只留一句「后会有期」。
他虽是骊国皇室之人,但安顿了乳母和弟弟,确实帮了我江家一个大忙。
可在朝局一事上,外邦之人,终究是敌非友。
14
当晚,周景年自随从手中拿到了一封周将军捎来的信。
周将军在书信中称,边疆粮草短缺,将士们风餐露宿,哥哥之死另有隐情,或与军饷有关。
其中有一纸请命书,打开一看,至少盖了上百位士兵的手印。
这封信将军饷短缺一事,写得清清楚楚。
信件直接捎到了我前边路过的一所城池的驿站。
信件做了处理,有隔层和套封,原信纸用的也是密语,就怕军中有心之人截下此信探查。
据说在此之前,周将军已经寄出不少家书,以乱视听。
这只能说明军营里有鬼,局势不利。
说到军饷,如今的粮草押运官都是丞相元鸿的人,一个是他侄子,另一个则是他亲手举荐的学生。
当初他急于致我江家于死地,或许就是担心哥哥已经掌握了他们一行私吞军饷的罪证。
他对江家痛下杀手,又把女儿下嫁将军府,无非是为了拖周家下水。
届时周家骑虎难下,边疆存亡,不过在元鸿一念之间。
周景年连夜撰写奏折。
至于人口买卖一案,除却先前已押送回京都的几名人证,他在这所县城又抓了两个与京都那边对接的商贩。
此案疑点颇多,诡异之处也让周景年百思不得其解。
买卖人口的商贩虽多,他们对人皮灯笼一事也供认不讳,可不论在哪个工坊,周景年及其手下侍卫都仅搜寻到血淋淋的人皮,成品灯笼谁也未曾见过。
按理说,所有工坊都将人皮供往京都,京都应当是最好查获的地方。
但诡异就诡异在这儿,京都,什么也查不到。
15
我们归京时,恰逢圣上前往华兴寺礼佛。
太子年幼,如今代管朝政之人是丞相。
我也是这时才知道,离京前,丞相府就和将军府定了婚期,万事俱备,只等周景年回来。
这桩婚事过于匆忙。
不过这也验证了元鸿急于笼络将军府,试图掌握边将战局的心思。
而他之所以如此急切,定然是因为之前边疆出了差错。
他无法确信哥哥是否拿到了他贪污军饷的实证。
即便对五千将士赶尽杀绝,他仍放心不下,于是害我江家家破人亡。
要说实证,哥哥信中提及,丞相与军中副将曾有信件往来,他也曾去副将帐中查寻,奈何遍寻无果。
想来元鸿那样老奸巨猾的狐狸,为防止有人半道下船,必会留证用以威胁,做二手准备。
回了京都再往华兴寺,免不得被元鸿注意,若是被他劫了罪证,此局当真无解。
圣上礼佛不过三日,而我欲坐实元鸿之罪,那些他与副将通信的信件,便是直接与他挂钩的铁证。
扯上他的侄子、学生,他咬咬牙尚能断了左膀右臂,可只要拿到那封信上呈,他就如何辩解也不能够了。
回京后,周景年整日脸色沉得厉害,不是窝在我这梨花小院,就是往刑部大牢提审犯人。
我莫名觉得有几分好笑。
怪不得进京前他非黏着我寸步不离,都到城门口了还要一拖再拖。
院外红绸刺眼,我让小桃关了院门。
胁迫得来的婚事,哪哪看着都碍眼。
不过现下我倒是能将计就计。
大婚之日人多眼杂,那时我潜入丞相府搜寻罪证,无疑是最好的时机。
16
婚期临近,周景年仍专心人皮灯笼一案。
此案该审的都审了,只是根据商贩们提供的线索,周景年带人又扑了场空。
他一开始还以为是几人串了供,后经细查,发现几人说的确是实话。
似乎有人通风报信,提前斩断了京都这边的所有线索。
在此期间,丞相也上门请了周景年一遭,言明会竭力配合周景年,查清人口买卖相关案件。
至于其他,左右不过是些你做了我女婿,我必会好好扶持你这样的客套话。
细细想来,元鸿之言,倒更像是试探。
他是试探案情进展?还是试探周景年够不够格做他丞相府的女婿?
我一时没有头绪。
大婚前一晚,也就是圣上归朝的前一晚。
小桃进门来给我奉茶,烛光衬得她一双眼睛通红,眼角还有泪痕,显然是刚哭过。
我皱了眉,将她手上的茶盏搁在桌面上。
「可是有人欺负你了?」
我以前从没遇见过这样的事。
毕竟我是江家嫡出小姐,下人虽有自己的心思,却怎么也不敢克扣到我头上,抑或是欺负到我院内的丫鬟头上来。
可我也听说,有些年长的嬷嬷、管事惯会欺软怕硬。
即便入周家以来,几位当家的主子对我如何礼待,说到底,我在他们下人眼中终究是个妾。
赶明儿相府小姐就要入府做当家主母了,下面的人还不知会生出怎样的心思来。
他们如何看我无所谓,只是万不该欺负到我院里。
经我一问,小桃呜咽出声,却也只是抬手拭泪,一味摇头。
我抿了唇,拽起她的胳膊就要往屋外走。
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欺人。
小桃哭得更凶了,「不是的,不是的,夫人,是我姐姐……是我那个被卖了去做人皮灯笼的姐姐……」
我愣了下神,松开手,有些不知所措。
她从未和我提起过她的往事。
我一心只有江府的清白,也从未主动问过她,当初为何冒着风险救我。
我更不知她还有个身世凄惨的长姐。
17
小桃出生佃户,家中不算富裕,且近年边境战乱不断,朝廷赋税繁重。
她是家中二女儿,在她之上,有个比她大两岁的姐姐,往下,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为养活三个小的,她父亲迫不得已,将姐妹二人卖给了牙婆,想着若是能寻个好的主家,将来一家人还能重聚。
未承想,到牙婆那儿没两日,姐姐害了病,再后来,牙婆应允小桃为姐姐请大夫。
说是大夫,来的却是位胡人。
那时小桃被支走,到东街买物件,回来的时候,姐姐已经不见了。
什么人皮灯笼、皮料,她在同住的小姐妹那儿听了一嘴。
当晚她和牙婆大闹了一场,牙婆要将她发卖了去,她不肯,闹出祸事又回到了牙婆手上。
牙婆不愿意告诉她姐姐的去向,她也就一味在那儿等。
事情过去了很久,久到牙婆都要忘了她是因何留下的。
其实小桃心里也知道,自己的姐姐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执念于此,所以她才会不顾一切想要留下我。
她不想让我成为第二个被带走后下落不明的人皮灯笼。
可她今天出门,亲眼见到了那只灯笼。
我有些迟疑,问了两回方敢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她姐姐的右肩膀上,有一块红色梅花状胎记。
今日她去街上买糕点,亲眼看见有个锦衣华服的小姑娘,手上提着盏花灯。
那花灯样式精美,通体晶莹,上面的一朵淡红梅花尤为扎眼。
「夫人,我不会认错的。」小桃哽咽着,「那就是我姐姐,她死了,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