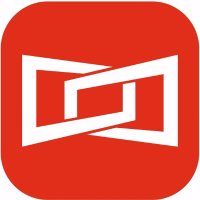界面新闻记者|尹清露
张了一和孙谈是两个漂在北京的年轻编剧,他们自认为写出了一个绝妙的剧本,于是辗转于不同的影视公司开会,从夏天改稿到冬天,直到剧本变得面目全非,张了一患上焦虑症,甚至主角从人变成一只狗,项目也没能上线。
上述的场景是国内编剧的常态,而于3月底上映的《银河写手》将之搬上了大银幕。这是一部视角颇为垂直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很多人能共鸣的“乙方故事”。主演宋木子、合文俊、李飞通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被观众熟知,却也并非大牌演员。但正是这样一部片子成为了2023年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的黑马,斩获一众好评。导演李阔和单丹丹凭借本片并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最佳编剧奖。

单丹丹是北京大学文学硕士,李阔毕业于传媒大学表演系,两人是夫妻也是搭档,大部分时间作为委托编剧,根据甲方的需求撰写剧本。也因为常年的乙方视角,他们很清楚观众爱看什么,《银河写手》的喜剧包袱和剧情转折都很丝滑,甚至丝滑得不像处女作。这也是一部粗糙但真实的作品,甚至真实到令人哑然失笑:被制片人忽悠着改稿,每改一遍制片人的署名都放大一圈;两人住进编剧扎堆的常营,幻想着下一秒片子就能拍出来;为了卖一张北影节的《黑暗骑士》电影票,张了一开微信群有奖竞答,答对“小丑的第一句台词是什么”才能拿到票。这些行业梗和迷影梗都出自导演的真实经历,电影中出现的《星际穿越》同款手表,正是单丹丹送给李阔的礼物。
在《银河写手》上映之际,界面新闻(ID:booksandfun)专访了单丹丹和李阔,从剧情出发,一起讨论了国内编剧的生态。
编剧是距离影视圈最遥远的一个工种
界面新闻:丹丹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勤勤恳恳为甲方做了十年编剧,写《银河写手》时却“抛开了一切”。为什么想到拍一部讲述编剧生态的片子?创作《银河》时的心态和想表达的东西跟以前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李阔:首先是因为上一个剧本我们做了两年半都没有做出来。主人公是一个50岁的中年男人,他还有一个18岁的女儿,这两个人物离我们太远了,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后来开选题会时丹丹导演说她有一个小说《北京有个常莱坞》,还没写完,也没有发表过,我们觉得不如就写自己,所以诞生了《银河写手》。

单丹丹:以前做委托编剧是去帮别人做一个已经确定的项目,《银河写手》是自己想表达的,不用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的真实感受最重要,我们觉得编剧的生态圈就是这样的,那这么去做就好。
其实90%的编剧都是做委托项目,它保证了一份收入,也就是10%的定金,编剧拿着定金回家创作写大纲。但是原创项目是给自己负责,需要把剧本完写完再去找资方。表达自己听上去是蛮爽的,但是要承担的后果就是剧本或许无人问津。所以,除非有一个特别想表达的作品,或者是有过作品的大编剧、对市场有精准的把控,才会去做原创剧本。
李阔:十年了,也确实到了需要检验自己的地步。总觉得没人给自己机会,那到底要不要继续干这行?如果觉得自己能打,那至少得上一次擂台。这次属于孤注一掷了,做完才知道自己是没有才华,还是没有机会。

界面新闻:电影的主线是“改剧本”,两名年轻编剧从夏天改到冬天,直到放弃。这种做不出作品的状态在编剧中有多常见?还有观众认为,《银河》像是北京工友互助文档里影视行业的具像化。比如谁都能改一笔自己的稿子、制片人署名编剧、因为改不出剧本患上焦虑症。
单丹丹:非常常见。今天有杂志邀请我们拍摄,说可以一起邀请其他5个编剧朋友参与进来,最好是有影响力、有代表作的。我们翻遍朋友圈,发现身边的朋友都没什么影响力,只好问杂志方,没有作品能不能也来拍一次?对很多编剧来说,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样一个杂志愿意采访他们,听听他们的故事。杂志方听了也挺感动,说那就拍小编剧吧。但是前面这些年大家都没有闲着,编剧是一个需要大量学习积累的工作。
李阔:季节的跨度也取材自真实生活。我们经常沉浸在写作里,写很久也不下楼,也完全不看微博热搜,某天下楼扔垃圾拿外卖,突然发现花开了草绿了。所以就通过艺术加工放到影片里——明明在家还吃着西瓜,推门一看下雪了,恍如隔世的感觉。
单丹丹:在我看来,编剧是影视圈里距离这个圈子最遥远的一个工种。编剧不像其他工种可以在剧组里工作,他每天只面对一个电脑,偶尔平时跟策划和制片人开个会,如果哪天能见到导演和演员了,那就是天大的好事,说明项目推动起来了。

界面新闻:这一点在片中也能看出来,孙谈和张了一住在影视从业者扎堆的常营,平时不用去公司,所以把某咖啡馆当做“单位”,把某餐厅当做“食堂”,每天有很多人在这里谈几百万的项目。我就住在那附近的青年路,常营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你们对这里抱有怎样的感情?
李阔:常营是一个很接地气、很平实的地方。从这里的标志性商场就能看出它的定位,青年路的朝阳大悦城里有些轻奢品牌和艺术空间,构造上七拐八拐很不规则。但是常营的长楹天街没有这些,而且它是一个直来直往的大通道,从东边贯穿到西边,永远不会让人迷路。
之所以常营成了影视从业者的聚集地,一是因为附近有很多影视工业园区,而且传媒大学就在常营附近的双桥。二是因为,常营是北漂们能享受到市区繁华的最后一站,它房租不高,交通又方便,坐上6号线就能东西贯穿北京。常营再往外是通州了,往里就是百子湾。提到百子湾,大家会想到这里的小明星和小网红,但是常营给人的感觉非常草根,这里有一个朝阳区北漂的著名根据地,也就是小区“北京像素”,光是一栋楼的一条走廊里,门对门就大概有50家住户。在《银河写手》里,孙谈和张了一为了体验生活去送外卖,取景地就在北京像素,有一个镜头是他俩看着密密麻麻那么多窗户,突然就迷路了。我们想让整个故事、地点都很真实,不想架空。
单丹丹:其实整个朝阳区都遍布着影视从业人员,常营住着最底层的“踝部”从业者,成功一点的就能进阶,可以搬到大学城、青年路附近。
李阔:青年路也有很多影视从业者居住,但是房租要比常营贵,说明住在那的人混得比常营好(笑)。我已经在常营住了9年,丹丹导演在这里住了5年。住惯了,所以喜欢这里,就像是问你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家乡一样,这是习惯的问题。

界面新闻:张了一、孙谈都面临甲方的折磨,但是各自的性格又不一样——孙谈选择继续在行业里熬,张了一更心高气傲,但也最先感到迷茫和麻木。可以分享一下构思这两个人物时的想法吗?他们有多少是自己的真实写照?
李阔:这两个人物参考了我们,以及编剧之一的高群老师。孙谈在大学是学地质勘探的,电影结尾时,他说自己知道一个位于内蒙的鸡血石坐标,这些都是高群的真实经历。上一部剧本流产之后,我们仨都很难受,坐在一个包子铺,高群就提起了鸡血石的事,说要是实在不行,咱就去把这个石头打开,看看有没有钱赚。当然不可能真的大动干戈,于是就把这个情节放到了电影里。
孙谈参考了高群的性格,他是一个老好人暖男。张了一参考了我身上的特点,比如我很喜欢诺兰,有时很笃定自己的才华,有时又陷入怀疑退缩之中。
单丹丹:但是李阔导演和高群导演都不喜欢改,都喜欢坚持自己。我是愿意尽量按照甲方要求修改的,片中的周可可也参考了我自己。
界面新闻:虽然这是一部讲述创作者困境的电影,也并没有一边倒地吐槽甲方,而是呈现出双方的视角,比如制片方的女孩看似挑剔,但她会直言自己的职责就是规避风险。这一点跟《年会不能停》中,最后打工人们迎来胜利的结局很不一样。可以讲讲在设置这部分剧情的想法吗?
单丹丹:刚开始拍的时候,李阔说不能把甲方写得那么坏,以后还要在圈子里混饭吃(笑)。不过这只是个玩笑,其实对于编剧来说,最痛苦的不是甲方不靠谱,这样的话我们直接走人就可以了,心里只会有嘲笑和讽刺。最痛苦的是,你觉得甲方的建议蛮有道理的,他也是为了项目好,这时压力就给到了编剧,不接受的话就成了罪人,接受了就要阉割自己。
就算是那个看似很坏的制作人贝勒,老是提不合理的要求,还把自己包装成了总编剧,他失业以后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滴滴司机,甚至还很热情地跟张了一他们说,剧本的男主一定得改成40岁,还在坚持当时的意见。在他的认知里,他真心认为这样对剧本好,并不是魔改或者胡改。
电影中的那名女性策划也很真实。我们发现,公司里的策划绝大多数都是女孩,因为看剧本的工作需要细致和耐心,而且很多人在学校里学的就是电影,他们为了以后做编剧,才在公司里做策划磨炼经验。所以在片中,张了一骂她“有本事你当编剧”,那女孩就哭了,因为她其实也很想当编剧。所以面对这样的甲方,你恨他也很不起来,爱他也有点无力。

好莱坞大片失灵是因为大家猜出了套路
界面新闻:片中的神来一笔是用短视频解构《救猫咪》的“节拍器”,有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出色的编剧要既遵循又好像丢掉了节拍器”。《银河》就体现了这句话——把“出场人物”“情节”“人物成长”等字样直接嵌入影片中,但中途又解构了它们。编剧对套路的普遍看法是怎样的?又爱又恨吗?
单丹丹:爱和恨都谈不上,但节拍器的确是个工具,它指的是15个故事节点,漫威电影都是严格按照这个规则、掐着分钟准确呈现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好莱坞大片失灵了?因为大家都能猜出套路了,但是如果故事没有铺垫、低谷和高潮,观众又不喜欢。所以好的编剧既要遵循基本的叙事套路,又要通过细节的编织、让观众感受不到套路。所有的好编剧都在努力突破这个问题,我们也一样。
李阔:虽然漫威电影式微了,但是如今最受欢迎的电影还是《银河护卫队》系列,评分也高,就是因为它是漫威里唯一努力做出创新和尝试去反套路的。“救猫咪”是行业里的葵花宝典,它是这样一个理论:无论主角有多讨厌,只要他在开场救了一只流浪猫,那他就是个可爱的人物。救猫咪和节拍器都是讲编剧行业绕不开的东西,但是为了让行业外的观众也能get到,我们就想到用抖音讲电影的方式来呈现。
抖音讲电影那些人会把120分钟的电影剪成3分钟,因为他们就是卡着节拍器的点来的。这类短视频永远不会讲过程,只讲故事推进的重要节点,比如谁出门了,马上就拿刀捅了别人。我们平时也会看短视频,同时对此也很无奈、很深恶痛绝,所以不如就用这个方式来调侃一下短视频,也“致敬”一下他们。
界面新闻:周可可的角色也很有趣,她更能适应高压的工作环境,即使工作分配不合理也毫无怨言,最后也最先拥有了自己的作品,她会说“编剧就是服务业,把事做成了才能谈艺术”,这是你们直接的想法吗?你们怎样看“文科是服务业”的说法?
单丹丹:这句台词是2022年写的,其实那时候“文科是服务业”这句话还没出现。我们平时也会这样嘲笑自己,剧组的衣服上就写着“服务行业先进工作者”。
我们从入行就面临这个困境,到底要做一个改来改去的工具人,还是做一个有自己表达的编剧?这两种状态借周可可和张了一表达出来,让大家发现选哪条路都不好走,但是他俩也都在成长。

李阔:我是认同这句话的。至少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你就是要服务好甲方。我周围也有成功的编剧,他不一定能力比我强多少,但是深谙与甲方相处之道。比如,我们有时会闭门造车,憋出一版自认为特别好的大纲,拿给甲方看却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他会在写剧本时让甲方也参与进来,就算甲方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萌芽初期就把它砍掉,不会等到写出两万字了再被甲方整个否掉。另外,当甲方跟着参与创作时,他是很少会否定自己的。这就需要服务业的聪明才智,跳脱出才华去想其他沟通的方式。
单丹丹: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具备一定能力和作品的编剧,我确实希望大家把这句话扔掉,做有表达的作品。为了不让市面上都是“与我有关”的作品,就需要编剧去做多元化的东西。如果有一个很新鲜的剧本,甲方读完也觉得有点意思,那也能推动行业发展,对吧?上次在《银河写手》的北大映后环节,戴锦华老师先肯定了“文科是服务业”这是一个事实,但她还是希望所有的文科创作者学习到这点之后,一定要把这句话扔掉,不能一辈子奉为真理。
张了一就是和这句话背道而驰,他就要去撞南墙,愿意粉身碎骨,我们不能因为他最终失败了,就去嘲笑他。我在看张了一的时候,会觉得这真是一个傻瓜,可笑可叹,但是也有一点点可爱。我想,每个创作者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某一刻。
我问过一个观众喜不喜欢张了一,他说不太喜欢,因为跟自己太像了。还有观众觉得自己是周可可,认为成年人的职业规划就是要先学习再成长,而不是总跟甲方拧着来。我又问这个观众,那你愿意和张了一交朋友吗?他说我愿意,因为他做到了自己做不到的坚持——如果他说一个剧本一定要让姜文来拍,肯定会觉得他很可笑,但是七八年后他还这么说,那可能会请他吃顿饭吧,因为世界就是被这样的人改变的。
界面新闻:电影多次强调“现实不像故事,它就是没有铺垫的”,比如害虫(李飞饰)毫无征兆地被女友背叛,演员毫无征兆地自杀。它也一反人物成长的弧光,认为“人物没有成长”,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一点?影片最后,两人本来绝望到要回老家,却想出了另一个剧本——于是又回到了刚开始的状态。这也是编剧的某种写照吗?
单丹丹: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当编剧第一天开剧本会的时候,放下书包就听到大家在聊:人物这样做的合理性是什么?于是我才知道,原来编剧写人物行动一定要先把心理铺垫完,这样观众才能get到。但是往往当我们想出一个很棒的点子,说完就陷入了沉默,因为要给他不断地找原因和动机,这个过程让我很痛苦,这也一直是悬在编剧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既然要写这个职业,就要把这个职业的苦楚给写出来,最起码编剧看完是认可的。
至于“再次出发”是不是编剧的一个循环,我觉得当然是。对于编剧来说,当一个项目失败了,能让我们真正站起来满血复活的就是投入下一个项目。人生不也是一样吗?大家都知道身上有些弱点,但又很难改变,不断地让自己突破某些极限,但可能永远都突破不了,这可以小到生活习惯。比如我爱喝冰拿铁,我妈一直跟我说这样湿气重对身体不好,这些道理我当然知道,但就是改不了。
李阔:人物要有成长、剧情不能有bug、人物线要清晰,这些都是我们开会时听到的高频说法,所以“人物没有成长”纯粹是个人的小叛逆和小趣味,观众以为张了一终于开始成长和反思了:也许贝勒不是那么好的制片人,我也不是那么好的编剧,我应该谦虚一点。没想到过了一会,张了一还是谁的话也不听。
去年在西宁FIRST电影节放映以后,很多观众说好喜欢“人物没有成长”这句话,我们发现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又共鸣,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坚持和保持初心就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界面新闻:你们会担心反高潮的故事设定会削弱它的张力吗?尤其是当大家更爱看有“爽感”的片子?
单丹丹:说实话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毕竟是新人导演,还没跟市场打过交道。现在我发现观众的确喜欢这种(爽片),市场的反应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也会反馈到我们下一部作品中去,因为类型片需要让事件的冲突更强烈一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吸引观众买一张票、走进电影院变得越来越难了。
界面新闻:我也很好奇,当“反套路”变成了新的套路,编剧要怎么想出吸引人的故事呢?
单丹丹:也不一定要特意反套路,首先还是要在情节冲突上吸引观众。第二,肯定要在最大限度上去和观众共情。
我的感受是,现在观众喜欢看的电影一定要“与我有关”,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可能也会点进去看,但是要转化成一张电影票就太艰难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商业题材的故事,那就要做到与观众共情,并且严格遵循节拍器。当然,如果有很严肃的社会议题要表达,那就不要想着强事件或节拍器了。不能既要电影很深刻,又埋怨观众不来买票,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观众的口味在电影历史上一直在变化
界面新闻:强调“与我有关”是一个很大的观影趋势,这会对你们造成困扰吗?《银河写手》讲述的是编剧生态,也跟大部分观众的生活无关。
李阔:其实观众的口味在电影历史上一直在变化。今天我们说超级英雄泛滥了,上一次类似的现象是西部片——那个年代的美国人全都在拍西部片,导致这个类型也没人拍了。至于中国的商业片从90年代才开始起步,历史比较短,没有太多经验可以遵循,但是在我看来,大家喜欢有情绪共鸣的电影也是一件好事,因为90年代最吃香的让人血脉喷张、满足感官刺激的电影,比如在高速公路上的追车戏,现在已经过了这一阶段了。
单丹丹:我们也没有那么担心,因为市场会做出选择和调整。前几年架空的喜剧很受欢迎,现在也没有人愿意看了,更喜欢现实主义。后来纯粹的现实主义也不行,还得让人足够感同身受。
这样看来,《银河写手》的确是一部很难定义的电影,它没有强类型强情绪,可是你说它文艺吧,又没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还是很通俗喜剧的。这几天有行业内的老师开玩笑说,这是一部很”稀有“的片子——老百姓看了很多与我有关的,突然看到有片子拍了编剧这么一个群体,还得到了很多人喜欢,而编剧甚至在自己的圈子里都是被遗忘、被边缘化的群体,光是这一点的意义就让这部片子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