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创刊于1950年,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办,是一份刊登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诗歌和文学评论等多种优秀作品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杂志。《北京文学》目前拥有两本杂志,原创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刊发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诗歌和文学评论。主打好看小说,聚焦报告文学,力推青年诗歌,追求清新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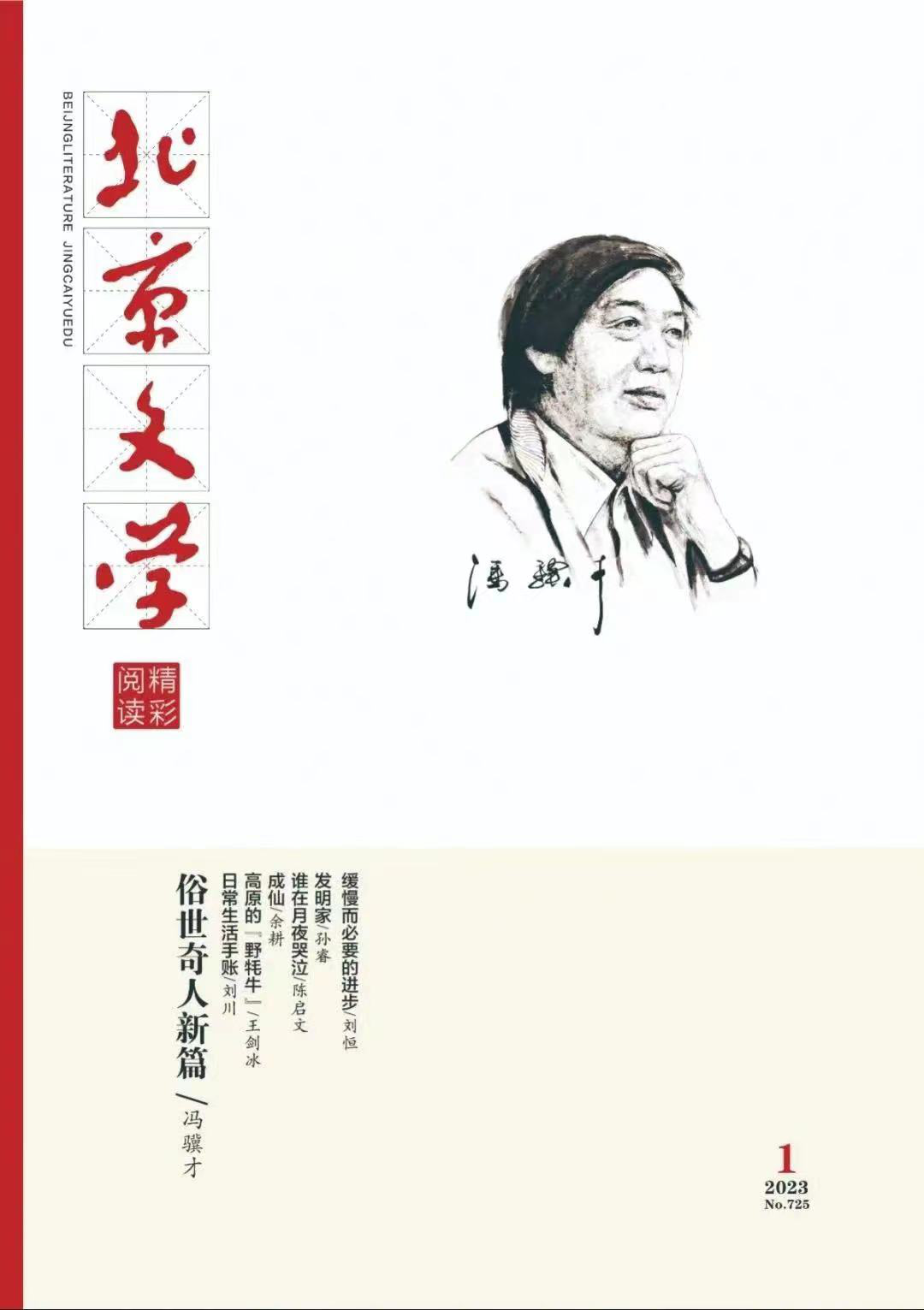
《北京文学》2023年第1期封面

宋宁刚,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博士。著有诗集《你的光》《小远与阿巴斯》《写给孩子的诗》,诗论集《沙与世界:二十首现代诗的细读》《长安诗心:新世纪陕西诗歌散论》等。曾获陕西青年文学奖、入围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现任教于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
通读2023年度《北京文学》所刊发的诗作,看到其中的栏目——“汉诗维度”分为两个常设的子栏目:一是“云汉”,每期推出几位诗人的一组诗作(少则一两位、多则七八位);二是“星群”,每期刊发十位以上诗人的诗作,每人一到两首不等。
此外,不定期地设置有一个与《诗刊》合办的“共同发现”子栏目,每次重点推出一位“新发现”的诗人诗作并配发一篇评论。2023年的12期中,“共同发现”共推出王彻之(第7期)、张小末(第8期)、贾想(第9期)、谢健健(第10期)、陈丙杰(第11期)、加主布哈(第12期)等六位诗人,并分别配发了程一身、安琪、傅元峰、胡桑、赵目珍、卢桢六位诗人批评家的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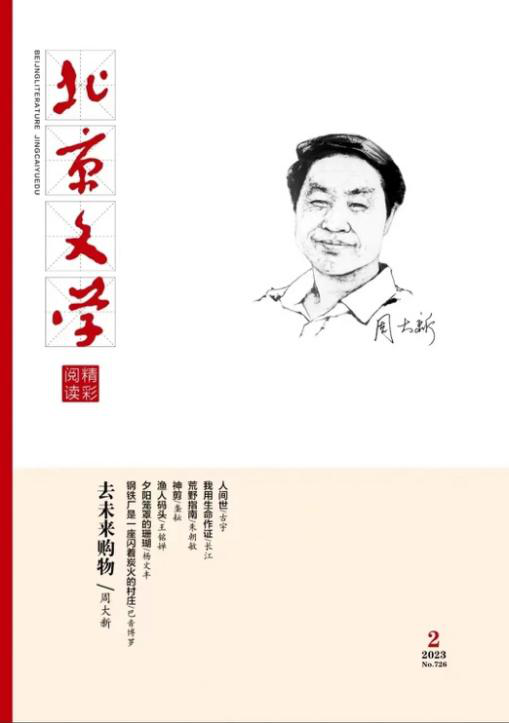
《北京文学》2023年第2期封面
“云汉”栏目在常规推出若干诗人诗作的同时,还重点推出了巴音博罗(第2期)、赵汗青(第5期)、魏伸洲(第6期)三位诗人的诗作并分别配发来自吴玉垒、钟鸣和赵汗青的评论。
以上九位诗人的诗作,可说是2023年度《北京文学》诗歌栏目中,分量最重的作品。尤其像魏伸洲这样的诗歌“圈外人”,杂志在刊发时慨然给予六个页码、刊出约30首诗,实在是极罕见的。这组诗也确如阳光下的绽放的花朵,风中摇曳着,散发出源自自然生命的灵性光芒。这样的诗不像是“写”出来的,而更像是诗思在自发的流动过程中,被原本无心的作者“捕捉”住的。如此见真心、见本性的写作,在张小末诗中也表现得比较突出,虽然有些诗行尚有稚气。
另一个极端则是赵汗青和王彻之的写作。赵汗青的《1997年冬,赵汗青致卞之琳(组诗)》,其中大多数诗作,都是与前人对话的“致敬诗”,对象包括卞之琳、李香君、王希孟、鱼玄机、张国荣等古今人物。王彻之的《佛罗伦萨来的明信片(组诗)》,在异域与本土、状物与写人、时间与空间、往昔与现在等多重交错中展开。其稳健叙事,以及相对的长句与长篇(13首诗中,大半都在20行以上),都会让人想起臧棣的写作。
两相对照(王彻之与赵汗青/魏伸洲与张小末),可以看出后者有将写诗日常化的倾向。也即,诗当然是“捕捉”到的,但也是“写”出来的,是在心神的高度沉浸之中,摹写心绪与神思的幽微流动,仿佛意识流小说那样,更需要工匠精神的苦心经营(或许这也是程一身称王彻之有“大师气象”的原因之一)。
谢健健的诗也多是“对话”,与古人、与朋友、与地方等等,仅从诗歌题目即可见一斑,如《紫云湖夜游,兼赠诸友》《渴水少女——兼赠柳越》《入藏行》《嘉峪关往事》《看,兼怀常书鸿》等,只是谢健健的写法,相比上述王、赵二位,更直抒胸臆,也更好读一些。

《北京文学》2023年第5期封面
九位被重点推出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是青年诗人,有更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前辈或同龄人为之写评、推荐,是极好的奖掖、扶携新人的方式。此种做法很值得推广。只有这样,文学的发展才会更加良性、更有温度,也更持久。
在“云汉”栏目中,我们看到从“40后”到“90”后,从叶延滨、孙文波、小海、刘川、胡亮到张二棍、吴小虫、左右等,代际丰富、写作风格也极为多样的诸多诗人的身影。从“星群”中看到的诗人面孔更多,特别是“90后”与“00后”等年青的新面孔,占比很高。虽说年青,“90后”和“00后”诗人的作品,却不乏细腻新鲜的表达和深湛宽广的思考。

《北京文学》2023年第6期封面
总括来看,一年当中,“共同发现”栏目共推出诗人6人,“云汉”栏目共推出诗人约40人,“星群”共推出诗人逾200人,“汉诗维度”全年共推出诗人超过250人。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学期刊,《北京文学》刊发的这个数量实在不能说少。上述三个不同的子栏目,共同构成一个金字塔状的形态,既突出重点,也兼顾发掘新人、展示当下诗歌写作现场足够的多元性与广阔性,甚至饱满的可能性与无限性。
2023年度《北京文学》所刊发的诗中,有相当一部分以组诗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我们可以比较充分地从一组诗中看到一个诗人的写作倾向;另一方面,从组诗中也可看出一个诗人怎样从一个主题开掘,进而展开写作的可能性,在情感和智性的表达上也更具完整和系统性。
所刊之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行各业,不仅身份多元,更来自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显示了《北京文学》极大的包容性与含纳力。许多写作者,一如魏伸洲《舞者之诗(组诗)》的前面所写,“也许我不是专业的文学从业者,但我热爱文字等同于舞蹈,甚至更多”。由此也可见,刊物作为一个载体和舞台,所展露出的无限活力与生机,在给予诗人和诗歌机会的同时,也收获着更为宽广的作者与读者面。
从所选诗歌的写作话题与内容来看,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也算是2023年该刊物在诗歌选发方面的特色。
一是诗人与作为精神资源的诗及诗人之间的对话。
除了前述赵汗青、王彻之、谢健健等人的写作,在2023年《北京文学》所刊出的其他诗人诗作中,也多可见。如曹文军在《诗经的草》中所写:“《诗经》是每个人的无名地块/一百七十八种植物,如果不翻译/我至多认出三五种”。关于《诗经》内容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草”上,角度独特。也可见出,一个诗人对作为汉语诗歌源头的《诗经》有意识地学习,并将其转化为自己写作的资源。
史迎凤在《你好清照》中,全诗直接以“你”为倾诉对象,直到最后诗人直接表达自己对李清照特有的情感:“你好清照/你是世间所有女儿的骄傲/有人说字里行间我有你的影子/君莫笑人将老我想做千年后你的知交”。
刘崇在《直言书致李白》中同样是直接对“你”诉说仿佛李白就坐在诗人对面,两人促膝长谈,“你与大唐对坐/看鹦鹉的翅膀埋在细软的石沙/有马车轰隆驶过梧桐遍布的山峦”。
伽蓝的一首诗的题目直接就是《马致远》。在这首诗中,同样可以看到对诗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一诗的“引述”与化用——“夹杂着枯藤、病树,黄昏/像一面响亮的锣敲响绕膝的尾音”“他说,马是瘦了点,人是天涯了点”“他说肠断,黑夜就在晚霞的绚丽处/泼墨,搅动一阵风云变幻的天籁”。
吴小虫的《老舍故居门外,读其诗》,以一个现代作家的一首诗,作为自己书写与“对话”的对象。
这类诗所写,并非对已有的诗歌内容和诗人风格的“复述”,而是基于诗人长期的阅读和积累,从个人的情感倾向出发,直接表达写作者对自己所关注的诗及诗人最真实的尊重与喜爱,至少是后者对自身的触发。这样的“对话”,使诗人有意识地反观中国传统诗歌以及诗人的创作,并非单纯的复古、崇古,而是在盘活利用传统的诗歌瑰宝,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同时,也扩展了当代诗的创作可能性,使其在与传统精神资源的互文中,得到滋养和丰赡。另外,也如前所说,使得诗的写作更加日常性和可持续性。

《北京文学》2023年第9期封面
二是诗人不约而同所触及的亲人主题,也即写到亲人的生与死。
生与死的戏剧每天都在上演。可是从2022年底到2023年初,死的意味更为深痛。那时,国人刚从三年封控中缓过身来,遭逢大面积的感染病毒,很多人排着队、结着伴,甚至相互挤着猝然死去……
诗人刘川在第一期的第一首诗中就写到了“死亡”。《日常生活手账(组诗)》,在很平常的生活状态下,想到自己那已经离世的姥爷——
“家里暖气试水/咕噜咕噜/像我姥爷/打呼噜……虽然死了都好多好多年了/每年冬天前/还会特意回来一趟/在我家暖气里/试试水/热不热”
也因此,在此后的每个冬天,诗人都会想起那个打呼噜的姥爷,这种生活化的写作与重要的人物之间形成一种联系,并且赋予简单的日常生活以诗意。
苏仁聪在《2021年最后一首诗》中更加隐忍而克制地表现了死亡的人们:“搬去天上居住的人/一直没有回来/他不再想念尘世的亲属/尘世的亲属去看他/也没有再回来……”将去世的人们写成在“天上居住的人”,巧妙地化解着死亡的沉重感,也将沉痛转化为一种更为悠长太息般一直存在的隐痛。
《吴少东的诗(五首)》中写到,“母亲最后的几年时光/就住在我的书房里/床头床尾都是/整面的书橱/那些立着的书籍/紧挨着,像她的子孙/母亲像本枯黄的线装书/在小床上早睡早起”。诗人将“母亲”比作书房里的一本书,是书房里众多书籍中“枯黄”的一本,读来令人心惊,而又温暖——暖中又带着痛——即便母亲后来去世,书房里依旧留有母亲的气息。
牛梦牛在《我的母亲,从另一个世界来看我》一诗中,写自己梦中离世的母亲的模样:“我的母亲/从另一个世界来看我/她不说话,只是站在床边看着我/一副怯生生的样子”。
死亡,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死亡并非消失,对于生者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单纯的遗忘。那些离世的亲人,像是无数散落在我们四周的尘埃,无论我们是否抬头,他们都在我们身边,甚至不用有意去回忆。关于死亡的书写,既是对死亡的安放,也是记忆的延伸,更是人类生命之链的精神联结。

《北京文学》2023年第10期封面
三是诗人自我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对话。
广义来看,所有的诗都是诗人内心与自身以外世界的对话,甚至可以说,所有的诗都是诗人情感与思想的外显。而从2023年度《北京文学》所选发的一些诗来看,不只是诗人自我情感的输出与释放,更是诗人在自我与现实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方式。这种外在结构上的关联,使得诗人的内在情感得到充分伸展。
如巴音博罗的组诗《钢铁厂是一座闪着炭火的村庄》中所写:
“我看见铁的面孔隐藏在群山之中/铁的肩膀和铁的手臂像大树/伸举向苍茫的穹空”;“在矿山,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眼睁睁看见大地的胸膛被扒开/裸露出那红彤彤的心脏/我们在古老的血液中焠炼这铁/我们的手,一律指向黑夜”;“我要打开这凤凰重生之路/是为了扔掉这枯萎的肉身”;“我们攥紧了命运,当秋天通过这阴暗的道路/暴风雨摧毁的一切如今又重新被镀亮/我们压低嗓音,收拢翅膀/仅仅为了更久远的歌唱”;“如果突然之间风沉寂下来/一定是有新的铁在诞生/如果漫漫长夜中的火熄灭了/一定是轰隆作响的钢铁厂给我们带来了黎明”……
这组诗是巴音博罗“在鞍山钢厂和矿山考察时的随想”。它的面貌和基调,与朦胧诗更为接近,诗行中将钢铁厂艰苦的工作环境、工人们不放弃、不服输的精神跃然纸上,同时也可以看到诗歌中所隐喻的“命运”,通俗易懂而又富含哲理,读来也更加朗朗上口,适于朗诵,更适于普通读者接受。
虽然当代很多诗人已经很少以这样的方式写作,但是从巴音博罗的诗来看,这样的写作方式依然有它自身的生命力。由此也可看出,刊物也像一个陈列馆,鼓励不同的写作方式,也向读者呈现各种写作样式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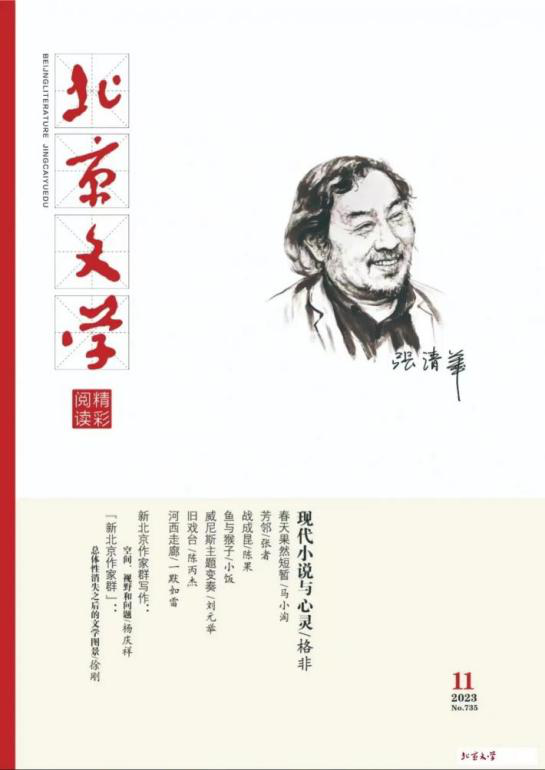
《北京文学》2023年第11期封面
除了以上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其实还可以从所选诗歌的结构、修辞、语言,以及所传达出来的情感、所表现出的意蕴等各方面稍作展开;或者,也可以从诗歌写作者的不同年龄分布以及不同的写作倾向稍作论述;再或者,有些诗相较而言比较晦涩难懂,本需要更多的批评与辩驳、对话与研究,有些新的写作倾向,也值得关注与讨论,还有一些新的尝试,需要对话与探究。此外,《北京文学》对作品与评论并重(这一点不只体现在诗歌栏目,也体现在其他栏目——从为作品配发短评的量来看,《北京文学》在国内文学期刊中堪称独步),也很值得一说。虽然这些方面,限于时间和篇幅不能一一展开,但是读者仍可根据自己的阅读,从某些感兴趣的方面试做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相信在阅读沉吟之余,读者不会否认,这些诗作绽放了汉语的可能性。
最后,感谢所有的诗人、编辑,也感谢广大热心的读者,是大家共同的合力,成就了包括“汉诗维度”栏目在内的《北京文学》——一个有着优良文学传承的刊物,不断地在四季更迭中新生与发展。
作者/宋宁刚
编辑/王菡
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