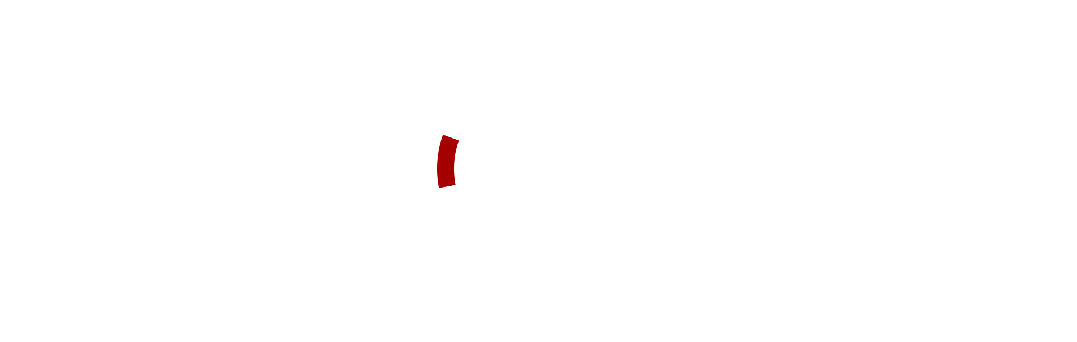
许多人阅读戴锦华老师是从她与孟悦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开始的,这本书讲述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女性如何由缄默而发声而觉醒,每一页都不乏金句和洞见,豆瓣评分高达9.5分。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本书其实有“续作”,这就是豆瓣8.7分的《涉渡之舟》,关注的是80年代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化。


《浮出历史地表》及其姐妹篇《涉渡之舟》(旧版)
这两本书都曾经一度绝版、一书难求,继《浮出历史地表》再版六年后,《涉渡之舟》终于迎来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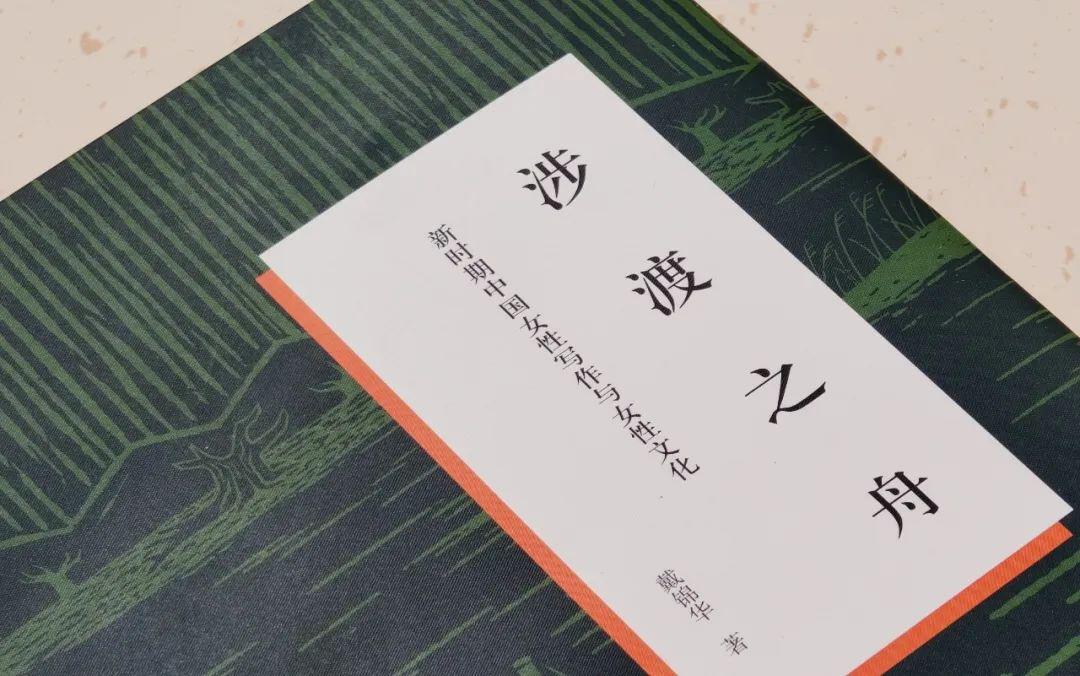
《涉渡之舟》在旧书网上一书难求
在《浮出历史地表》的绪论里,戴老师就以一种前所未见、纵横捭阖的风格,酣畅淋漓地回顾了女性觉醒的史前史:传统父系社会因控制、奴役、压抑女性而成其所是,它内在地对于女性既排斥又利用、既借助又抹煞,其结果就是女性作为空洞的能指——例如自荐枕席的狐妖美女形象、士大夫有意无意的“妾妇意识”……
女性则在这一过程成为失去自我的他者,并被父权文化缝合进既定的秩序。她提到花木兰的故事昭示了传统女性的两种出路:要么冒充男性角色“披挂上阵,杀敌立功”,要么“解甲还家,穿我旧时裙,著我旧时裳,待字闺中,成为某人妻”。

“进入秩序”是古代爱情小说中最不可少的结局,例如《牡丹亭》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就是在“情”的引领下,达成了主观与客观(父权制、官僚制和战争等)的调和,图为青春版《牡丹亭》。
在现代女性作家尝试突围的时候,她们没有任何现成的路径和语言,《浮出历史地表》从女性主义立场重述现代女性如何在“他人话语”之下寻求自我拯救,拒绝了旧式的柔弱依附角色的现代新女性,只能选择成为“不归家不卸甲的花木兰”,以男人的方式投身社会生活。
《涉渡之舟》进一步呈现了80年代女作家面对的“花木兰”式写作,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而写作的追求,在撞击男性文化与写作规范的同时,难免与女性成为文化、话语主体的机遇失之交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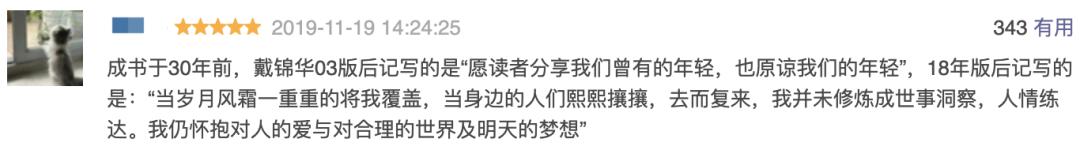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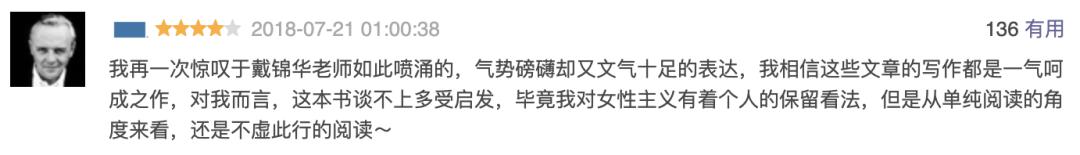


豆瓣网友对这两本书的评价
“涉渡之舟”寓意着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女性书写的跋涉,也象征着戴老师学术生命的一次转折,阐释着女性主义如何伴随她个人生命,在危机时刻提供依托和支撑。
01
走进历史的怪圈:
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写作
1949—1966
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戴老师在现代中国的整体历史文化语境中,勾勒出了现代女性写作传统的形成和展开过程。
《涉度之舟》接着往后展开:由于个人主义话语在现代的尴尬和匮乏,自叙传式的女性写作更多被视为旧社会社会文化的症候,用以指称弱者、零余者、迷失客乃至民族命运等。
于是,戴老师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历史遭遇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的身份与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女性独特的文化身份则在获得解放后“隐没”于历史视域,她们不是作为女人,而是作为共和国的战士或建设者,与男人享有平等的、无差别的地位。
如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琼花与红莲逃离了国民党与恶霸地主南霸天统治的椰林寨,跨入了红军所在的红石乡的时刻,不仅黑暗的雨夜瞬间变换为红霞满天的清晨,红莲身着的男子打扮也奇迹般地换为女装。但下一时刻,便是娘子军的灰军装取代了女性的装束。

电影画面呈现了着女装的主角和更多的、着军装的娘子军队员。
在1949—1979年间,女性写作经历了性别被忽视与被凸显的双重困境,尽管当时女作家作品被广泛关注和认可,但女性视角的表达却成为一种微妙的禁忌。
作品中的性别意识或爱情元素往往遭受批评,女性写作被要求超越女性视野与女性体验,一方面必须呈现出革命英雄形象,但另一方面还需具备独特的“女性风格”。
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女性写作的范本,呈现了“女性”作为“能指”的特殊作用,它用一个女人的故事和命运,象喻着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而后者才是这部小说的重心所在。

《青春之歌》不是故事层面上的林道静的青春之旅,而是一部知识分子改造手册,呈现了某种边缘处的中心叙事。
在50—70年代的文化表达中,女性最受主流肯定的形象仍是和男性一样奋斗的“花木兰”式女英雄,并被各种家国叙事中的经典形象层层强化,成为“女性的最为重要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镜像”。
02
历史的创伤与救赎:
超越女性写作的“花木兰式境遇”
1976—1990
1976年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与一系列社会变革,女性作为灾难的承受者的象征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她们被赋予传统弱者的形象,以历史的殉难者角色帮助完成社会的“拨乱反正”。
在这一时期,女性写作成为中国文化症候的表现形式。如伤痕文学中,女性形象往往被作为男性受难后的救赎者呈现,“纯粹女性”的形象以母爱和牺牲拯救男性,但自身却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仅作为象征性的救赎存在。

图/电影《天云山传奇》
而在反思、改革文学中,也有《人到中年》的陆文婷这样集中了女英雄、牺牲者、知识分子多重身份的超载文学符号。撑着“半边天”、将工作家庭“双肩挑”的女性的艰辛在陆文婷身上得到展现,但引起更大社会共鸣的显然是性别身份之外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并使这一小说成为“尊重知识”“科技兴国”等主流话语的先声。

陆文婷因长期繁重的工作压力,突发心肌梗死,生命垂危。图/潘虹饰演的陆文婷。
戴老师提出了“无法告别的19世纪”的概念,即当时知识分子以反叛的姿态借用了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欧洲文化资源,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启蒙与人道主义思潮。由于西方女性主义对启蒙理性的质疑与80年代的秩序重建产生冲突,这种错位影响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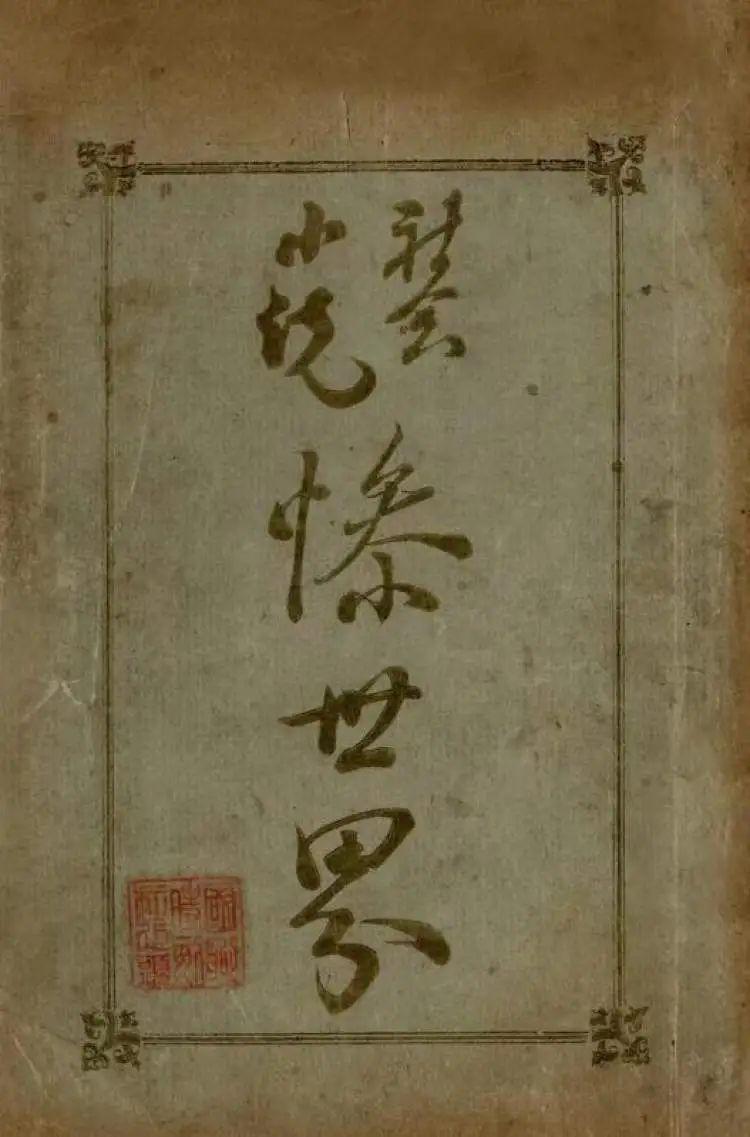
以19世纪欧洲文学的《悲惨世界》为例,十七年文学借重的是前两卷的人道主义批判,新时期借重于后两卷的人道主义救赎,成为80年代诸多宏大叙事的基本素材。
彼时,“代价论”作为一种流行历史解读,将历史创伤看作通往未来的“必要代价”,含蓄地质疑了女性解放等进步成果。女性写作则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微妙的“男女不尽相同”的话语中,试图反思历史并保留女性视角。
在微观的文本细读和宏观的语境分析之间寻求平衡,戴老师突出这一时期世界语境内的中国经验和女性生命经验的独特表达,呈现了女性写作的“花木兰式境遇”以及各种超越这一困境的尝试。
80年代前期,绝大多数女性的文学、艺术书写仍将自己的社会形象与自我想象,赋予文本中的男性文化英雄,将作为性别自我之假面的女性形象,放置在等待男性,亦即社会拯救的位置上。比较典型的,就是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塑造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形象:“执着于悲剧,并不断地把个人的、女性的悲剧经历放大、阐释为历史与现实的悲剧历程”;而爱情,尤其是婚姻之外、无法真正携手的爱情,承载着反道德的道德主义表述,成为悲剧中美丽的祭品。
80年代后期,以王安忆的“三恋”为主要标志,女性书写大多不再是“寻找男子汉”——作为女主人公的现实、社会归属与作为社会主体经验的男性假面,而是对微妙而仍牢固的性别秩序下的女性主体性的发现与展示。在“三恋”尤其是《小城之恋》中,身体、性爱取代柏拉图式的恋爱,表现出了解构爱情神话的姿态,以此改写进而冒犯了(男性)精英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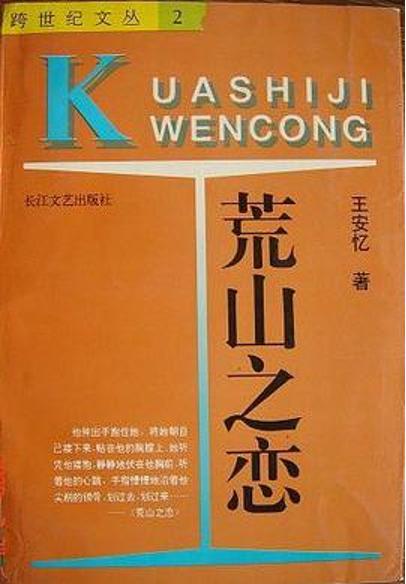
“三恋”发表后很长时间才得以结集成书。
图/《荒山之恋》(1993)。
而在池莉的“新写实“小说中,只剩对爱情神话的戏仿、质疑与拒绝,作者更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林林总总构成的”烦恼人生“,而这种拒斥了精英话语的、琐碎而踏实的物质化日常,肯定的是作为普通人的生趣,也成为即将到来的商业文化浪潮的先声。

图/首版《烦恼人生》书影
这一时期女性写作的多样化,还体现于作为“当代中国现代主义/先锋文学中的开端与翘楚“的残雪的系列作品。其作品中呈现的对于微观权力的彻悟,是难于在狭义的女性书写的层面上去做出阐释的。
03
一叶涉渡之舟:
女性书写的一份历史见证
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女性书写显示了自己的成熟与力度,同样是在这里,戴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书写也显现出一处误区与陷阱。
它通过拒绝暴力的姿态,以对中国历史场景的本质化描绘,融入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构建,而中国妇女解放的脉络与革命历史的复杂交织,却因此而再度遭到不同程度的遮蔽。
从这个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中国,是百年中国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年代,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与历史契机,而女性书写则在两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呈现出一次灿烂的绽放。
从此岸到彼岸,这一时期的女性书写艰难地托举出一只涉渡之舟。这是一份宝贵的见证与记录,历史的见证,也是女性文化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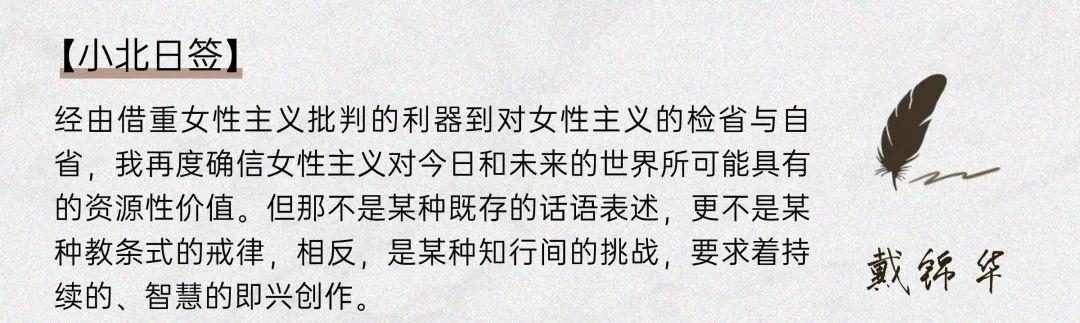

你之前看过戴老师的这本代表作吗
说到80年代女性文学你会想到什么
在留言区展开来说说
2位优秀留言读者将获赠此书
涉渡之舟:
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
《浮出历史地表》姐妹篇
呈现80年代世界语境内
中国经验和女性生命经验的独特表达
当当每满100-50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