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为《礼记》之一篇,唐前并未引起学者们的特别注意。中唐韩愈作《原道》引用过《大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大学通释》
自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表彰《大学》之后,南宋朱熹编订《四书》,将其列为首书,并撰写章句,其影响迅速扩大。
元明以降,朱熹《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教材,《大学》成为士子必读之书,不仅制约着时人的思想观念,塑造着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之后,《大学》地位骤降,人们对它的热情迅速消退。民国以后,除了少数学者在书斋里有些讨论,社会上几乎无人问津。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大学》又受到学校教育的重视,一些小学生甚至也被要求背诵《大学》,成为新时期学校教育的一道景观。
然而,《大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其主要思想是否为孔子所述,对今天的学校教育是否有积极作用,我们该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份文化遗产,这些问题,实有深入探讨之必要。故笔者不揣谫陋,略述己见,请大家批评。

《大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究竟有何价值?北宋理学家程颢说:“《大学》乃孔氏遗书,需从此学则不差。”[1]程颐说:“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2]又说:“入德之门,无如《大学》。”[3]
二程将《大学》作为孔子遗书,认为它指示了个人修身之道,是儒学入德之门,可以视为“圣人之完书”,全面评价和高度肯定了《大学》。
南宋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也参考了二程对《大学》文本结构次序的调整,甚至补写了“格物致知之义”一章,以阐释他对《大学》的理解。

《二程集》
不过,他对《大学》究竟为何书的认知与二程略有差异,他认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4]
即是说,朱熹认为《大学》是关于古代大学教育原则和方法的书。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还进行了具体论证,他说: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
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5]

《大学章句》
按照朱熹的理解,《大学》是孔子所传述的古代先王“大学教人之法”,建立于成功的小学教育基础之上。就其文本而言,有经和传两部分:“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6]
朱熹的这一理解,得到当时部分学者的支持,如汪晫编辑《曾子全书》,就将《大学》作为内篇《明明德第二》,并在首章加“曾子曰子曰”五字,在第二章加“曾子曰”三字,以表明首章为曾子转述孔子之言,第二章以后各章为曾子弟子记曾子之解说。
朱熹对《大学》的认识,元明以来被视为圭臬,虽有个别学者质疑,终究不能动摇其权威。
近代以来,学者们多从思想观念(某些核心概念)的演进规律来推断《大学》的产生年代,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如郭沫若《十批判书》、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劳榦《大学出于孟学说》皆认为《大学》属于孟子学派著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认为《大学》为荀子后学所著,傅斯年《诗经讲义稿》认为《大学》作于桑弘羊登用之后、汉武帝下轮台诏之前,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认为《大学》是秦统一天下以后、西汉政权成立以前的作品,蒋伯潜《诸子通考》、张岂之《中国儒学思想史》等则认为《大学》成书于汉代,说各有据,又都难以周洽。
近年来,由于大量出土文献面世,如荆门郭店简书《性自命出》《五行》《六德》《成之闻之》《唐虞之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性情论》《缁衣》《从政》等篇,与《大戴礼记》所载《曾子》十篇的思想有明显关联,不仅填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许多空白,而且证明了《曾子》十篇不是伪作[7],使得孔子至孟子之间的思想缺环被补上,人们对朱熹之说有了同情之理解。如李学勤便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一定是曾子所述孔子之言”[8]。

《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学勤说先秦》
尽管如此,要完全证明朱熹的论断,也仍然存在困难,因为毕竟没有直接的证据。而那些不同意朱熹的新说,靠主观臆测和逻辑推论下判断,问题就更多了,这也是利用思想观念溯源来确定《大学》产生年代何以会有许多不同意见的原因。
我们认为,朱熹意见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只是其具体结论需要略作修正。
周代学校确有大学、小学之分,而《大学》所论实为大学教人之法,而非小学教人之法。
据《大戴礼记·保傅》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北周卢辩注云:“小学谓虎门师保之学也。大学,王宫之东者。束发谓成童。《白虎通》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此太子之礼。《尚书大传》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世子入学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姓(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内则》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者,谓公卿已(以)下教子于家也。”
孔广森补注云:“《王制》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郊,西郊也。辟雍在西郊,故《诗》言‘西雍’。公宫南之左,则师保之学也。此天子诸侯同之。旧说天子小学在外,大学在内,似不然。卢注亦沿误。”[9]虽然孔广森与卢辩对小学、大学所在地点有不同理解,但对天子和诸侯均设有小学和大学的看法却是一致的。[10]
据传世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献佐证,周代官学教育存在小学和大学两个办学层次,招收不同年龄段的贵族子弟,小学“学书计”,“学幼仪”,“学乐诵诗”;大学“始学礼”,“惇行孝弟”[11]。
贵族子弟入学时间不尽相同,太子入学要早于其他贵族子弟,而同阶层子弟也因性格成熟早晚不同而有入学时间的差异,并不如朱熹所云“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至于说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尚无文献可以印证。

《大学衍义》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将《大学》分为经与传两部分,不仅与《礼记》所收均为释经文献的体例不合,也没有可靠证据作为支撑。
如果朱熹所认定的经一章是孔子所述先王之言,就应该从孔子之前的文献中寻找证据,但他事实上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如果认为经一章是孔子自己的话,孔子“述而不作”,他解释经典的话也是论、传或记,在先秦两汉儒家学者那里是不被称为经的。
且《大学》一篇首尾完整,首章为论点,后面为论证,不必以经与传来区分,韩愈《原道》引《大学》首章便直称为“传”。且《大学》首章并无“子曰”标识,反而后面有两章引有“子曰”,标明是孔子之言。
因此,朱熹说《大学》“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并非十分妥帖,不如直接认证为:《大学》是曾子弟子记录的曾子所述孔子教育理论。

清嘉庆吴氏真意堂刻本《四书章句集注》
我们说《大学》是曾子弟子记录的曾子所述孔子教育理论,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文献依据的。
首先,孔子私人所办学校是大学,而他又以复兴西周礼乐文化和学校教育为己任[12],大学教育理论由孔子所传述理所当然。
说孔子学校是大学的主要证据是: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这与《礼记•王制》所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13]的官办大学教育是一致的,而传世文献中未闻孔子与弟子讨论“学书计”、“学幼仪”等小学教育科目;《论语·宪问》载孔子与子路讨论“成人”之事,也说明孔子教育为成人教育;孔门弟子在学习期间能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可随时出仕,这自然是大学教育而不是小学教育的结果[14];《论语》记载有孔子关于教育的言论,许多与《大学》思想相关,也印证了《大学》所述是孔子教育思想(详见后文)。
其次,曾子是孔子弟子,也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病重时守护在旁,孔子逝世后庐墓三年,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为赡养父母曾经短暂出仕,后来谢绝诸侯聘请,专心授徒讲学,培养了孔伋(子思)、乐正子春、子襄、公明高、公明宣、公明仪、阳肤、沈犹行、单居离、吴起等一大批著名学生,撰写了十八篇著作[15],成为孔子弟子中最有思想理论建树的弟子之一,在孔庙“四配”中排颜渊之后,列名第二,被称为“宗圣”[16]。
《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7]这说明曾参对孔子思想的理解超过许多同门弟子。
他对教育的认识也是独到的,他说:“吾不见好学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见好教如食疾子者矣,吾不见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见孜孜而与来而改者矣”[18];“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则无闻矣;七十而无德,虽有微过,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19]

《大戴礼记补注》
其弟子子思及再传弟子孟子也是儒学发展的核心人物,由曾参弟子记录曾子所阐释的孔子大学教育理论,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当然,我们这样说,还只是一种逻辑推论,只有将《大学》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才能真正证明以上的结论。

《大学》记录的是曾子所述孔子教育理论,或者说是曾子及其弟子建构的孔子教育理论。要证明这一结论,必须先了解《大学》究竟阐释了怎样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是否源自于孔子。

《大学古本说》
《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0]这是人们常说的“三纲领”,是《大学》的核心思想,也是大学教育的总纲。东汉郑玄注解《大学》纲领云:“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止,犹自处也。”
唐孔颖达疏云:“在明明德者,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张显之。此其一也。在亲民者,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是其二也。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学之道在于此三事矣。”[21]
按照他们的注疏,大学之道是对求学者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也可以说是三大培养目标,即要求学者“章明己之光明之德”、“亲爱于民”、“止处于至善之行”。而这三项要求或三大目标相互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详细解说。
程颢、程颐认为《大学》文本有错简、有衍文,于是进行整理,各作有《改正大学》。二程的改正本排序不尽相同,证明他们对《大学》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而就“三纲领”而言,二程皆以为“亲民”当作“新民”[22],又说明他们对《大学》纲领的基本理解大体一致。
程颢说:“《大学》‘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于至善’者,见知所止。”[23]程颐说:“《大学》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24]又说:“‘新民’,以明德新民。”[25]
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说:“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眛,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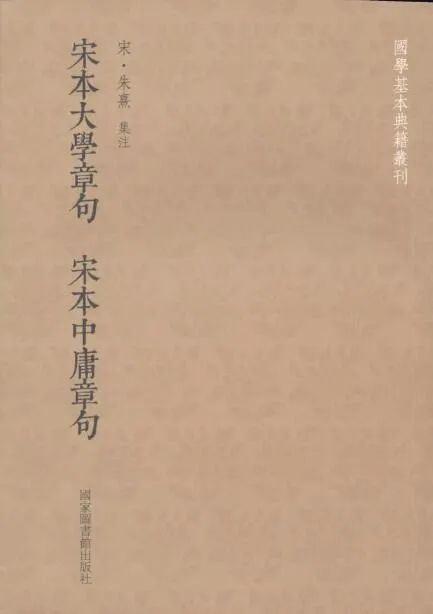
《宋本大学章句·宋本中庸章句》
在程、朱看来,所谓“明德”,就是“人之所得乎天”的“道”或“理”,也可以称为“道心”、“性命”、“天德”、“天理”,因言说语境不同而称谓有异。
因为“德”有吉凶美丑之分,所以吉德、美德可称为“天德”、“明德”,也即“天理”。“天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天地生物,各无不足之理”[27],“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28],“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29]
因此,人人皆具“天理”,人人皆有“明德”,“人皆可以为尧、舜”[30]。然而,人常为私欲所蔽,致使“明德”不明,故不能成为圣贤。大学教育就是要让学者“明”其“明德”,为学习圣贤扫除蔽障,这也是人们需要学校教育的重要理由。这一学习过程,被程、朱理学家们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

《二程全集》
至于大学之道“在新民”,程、朱实际上有“自新”和“他新”两种解说。不过,在他们眼里,“自新”和“他新”是一回事,所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因为“明明德”能够让人明白“天理”,知道物与我皆是一理,新我必须新人,新人亦即新我,于是“推己及人”,在“自新”的同时也使周边的人乃至整个社会“自新”。
这样看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和“在新民”并非两事,而是一事,“明明德”是就个体修养德性而言,“新民”是就个体与群体关系建构而言,而这是同时发生的,并非先“明明德”之后再“新民”,因为个体生活在群体之中,不“新民”就不可能真正“明明德”。不过,“明明德”与“新民”毕竟是两个不同层面、不同方向之事,所以不能相混,必须做两层来说,或者分为两项来处理,这也是它们各为一纲领的主要原因。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也同样不是另外一事,而是对“明明德”和“新民”所提出的价值标准和进德路径,同样是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一标准和路径,“明明德”和“新民”就没有了着落,学者也将不知如何下手,难免会踟蹰彷徨、迷失方向。
因此,“止于至善”也就成为大学教育的又一条重要纲领。并且这条纲领还是领起“八条目”的一个枢纽,所以《大学》接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31]
“知止”之“止”即“止于至善”。所谓“止于至善”,意为必至于“事理当然之极”而不动摇。
例如,学为圣人,就应该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榜样。

《大学或问》
至于如何才能“知止”,程、朱皆以为在“格物致知”,而《大学》没有解说“格物致知”,疑有阙文,朱熹取程子之意补充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乆,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32]
这段补传突出和强化了程、朱理学“即物穷理”的基本为学理路。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程、朱等人对《大学》的理解,明人方孝儒便主张恢复古本。
王阳明更是复古派的杰出代表,他以为“世之所传《(四书)集注》《(四书)或问》之类,乃其(指朱熹——引者)中年未定之说”[33],而“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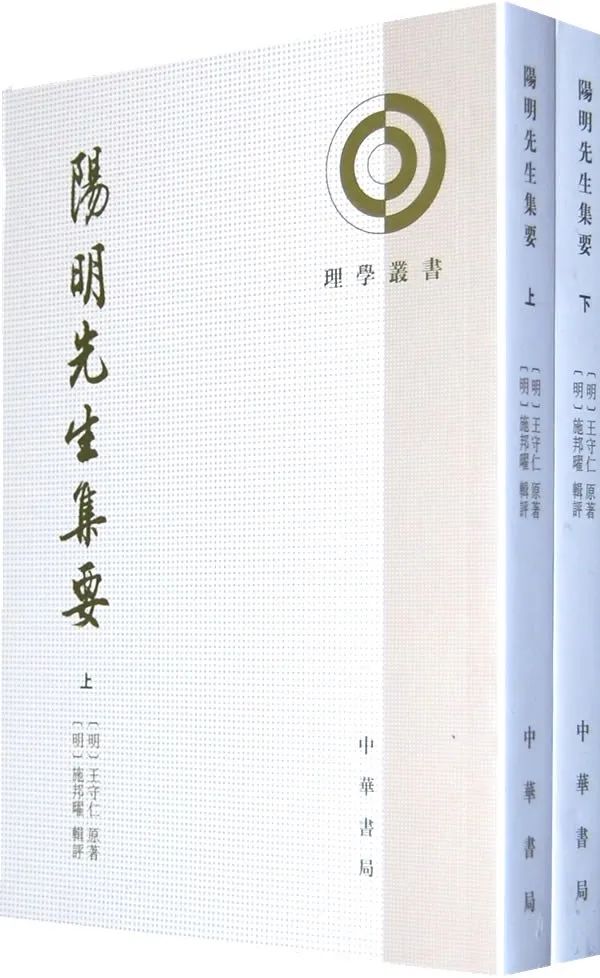
《阳明先生集要》
他在《大学古本序》中指出:“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35]
王阳明以为《大学》的要害不是“即物穷理”,而是“正心诚意”。他批评朱熹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末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36]
他认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37]
在王阳明看来,“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38]
“《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39]。

王阳明塑像
他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中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40]
他要弟子们不要相信心外有“天理”,而要相信本心有“良知”,《大学》的“明明德”就是要“致良知”,“‘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41]。
对于程、朱的“新民”说,王阳明也表示反对。他认为,此说在《大学》后文中没有照应,“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眀。
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42],因此,应该遵从古本,仍作“亲民”。

《王阳明全集》
对于“止于至善”,王阳明的理解也与程、朱不同,他说:“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43];“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44];“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45]。
而“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46];“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47] ;“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48]。
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对《大学》的理解虽然分歧明显,为学路径大不相同[49],但都以为《大学》是教育人成为圣人,或者说是以圣人的标准教育人,其主体要求是去人欲以存天理,基本方法是格物致知、止于至善。
他们所论虽然主要针对儒家学者如何为学,而事实上也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朱熹的《大学章句》在元以后为科举蓝本,更加强了《大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也从明中叶一直延续到清末。

《读经示要》
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对于他们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大学》一篇,总括六经之旨,而开端直曰‘明明德’。又申之曰,自明也。呜乎!此六经之心印也。汉、唐诸儒,守文而已,知不及此。程、朱诸师特表章此篇,列为四子书之一。朱子以‘虚灵不昧’释明德,则已直指心地,异乎康成之空泛无着落。此圣学之绝而复续也。然程、朱犹有未彻处。要至阳明,而后义解两无碍矣。启群迷而延圣慧,烈智炬以烛昏城,此恩讵可忘哉?”[50]
对于《大学》,熊氏认为程、朱有揭橥开发之功,而至阳明才解说完善,他显然对阳明的解说更为服膺。这里涉及理学与心学的评价问题,超出本文论题范围,可以不辨。然而,对于熊氏提到的《大学》与六经的联系,尤其是与孔子儒学教育的联系,确有必要讨论清楚。

通过上面的简要梳理,我们能够发现,无论是二程、朱熹,还是王阳明,他们对《大学》的解析,都是从儒家思想出发的。即是说,他们都认为,《大学》阐发了孔子的儒学思想。

《论语注疏解经》
当然,阐发孔子的儒学思想,并不一定就是孔子的思想,因为儒家后学可以创造性地发展孔子的思想。而实际上,《大学》的思想主要是有关大学教育的思想,其教育思想与孔子教育思想联系紧密,或者说就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建构,这是可以通过与《论语》比对而得到的结论。
首先,孔子所办学校为大学,实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这与《大学》的教育理念完全相同。
“有教无类”其实包括两层涵义:一是不管个人出身如何,人人都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二是不管个人天资如何,人人都能接受学校教育。
孔子之前的大学均为贵族学校,庶民子弟没有资格入学,而孔子的学校主要招收的是平民和庶民子弟,没有身份限制,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开创了中国平民教育的新时代。[51]
孔子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也。”(《论语·述而》)“束脩”本义是十条干肉,借指当时亲朋好友间相互馈赠的薄礼,而厚礼则用玉帛。孔子的意思是说,只要弟子自愿缴纳一定的学费,诚心向学,他都愿意招收为弟子,给予正式的教育。
《大学》的“三纲领”同样没有对求学者做出身份和资质的区分,反而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统一要求,其中也暗含有只要诚心向学,人人都可进入学校学习,都有达到大学教育目标的潜力。
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是十分进步的。正是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保证了中国传统教育对全社会的开放性,为社会的阶级和阶层流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次,孔子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儒”,与《大学》以学为圣人为“止于至善”的理想追求相一致。

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
孔子曾对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明确要求弟子成为“君子儒”。虽然“为君子儒”还不是以成为圣人为目标,却也隐含着成为圣人的价值追求。
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君子”自然是比“圣人”低的层次,孔子也没有要求弟子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必须首先成为君子则是肯定的,因此,“为君子儒”其实已经指示着成为圣人的方向。
《论语·子罕》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欤)?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述而》载:“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论语正义》
弟子们实际上是将孔子作为圣人看待的。颜渊便说过:“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他们以孔子为榜样,也正是以圣人为榜样,以成为圣人为价值目标。因此,《大学》的“止于至善”的教育思想的确是源自孔子。
其三,《大学》所述“明明德”、“亲民”等思想,同样可以从孔子的思想中找到源头。
“德”在孔子那儿与《大学》“明德”义同,如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他在被桓魋围困时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他教育弟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而孔子的所谓“德”,其核心是“仁”,如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雍也》)
在孔子那里,仁是可以通向圣的,仁人即是圣人。《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大学》的“明德”,二程、朱熹理解为“天理”,王阳明理解为本心之“良知”,均是与生俱来的。这一思想,其实也源自孔子。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将仁视为人人具备的美德,这是孔子教育成就人才的前提,也成为《大学》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基础。

《论语》
对于“亲民”,孔子同样有许多论述,如说:“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举直错(措)诸枉,则民服;举枉错(措)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孔子的“亲民”思想是一贯的,他认为,政治的好坏,不是由统治者说了算,而是由人民说了算。“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而“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欤)”(《论语·季氏》)。
这种“亲民”思想,无疑是《大学》认为大学教育“在亲民”的思想来源,也是中国教育中最可宝贵的理论资源。所有王阳明说:“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52]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
其五,至于《大学》中的“八条目”——“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施行“三纲领”的进路,其实也源自孔子的“为己之学”。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为己”不是只顾自己,不管他人。孔安国解释说:“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
范晔则进一步说明:“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也。”[53]即是说,“为己之学”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德行修养,真正从内心信仰儒家之道,并且身体力行;而“为人之学”则是夸夸其谈,用“手电筒”去照别人,或者想从他人的赞誉中来凸显自己。
“为己之学”是孔子赞成的为学之道,而“为人之学”则为孔子所鄙弃。关于“为己之学”,孔子有许多论述,如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不患人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
《论语》记曾参语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说明曾参深明此理。《大学》“八条目”中的“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五目全部指向自己,而“修身”既是前四目的总结,又是后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其论证后的结论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实际上是对“为己之学”的通俗解说。而天子和庶民都要接受教育,“以修身为本”,这在理论上证明了教育的普适性和公平性,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所以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54]
其六,《大学》并不止于“修身”,而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同样是孔子的教育思想。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正义》
“为己之学”不是及身而止,只强调“修身”,而是要“推己及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或者说要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孔子的“为己之学”,是以“修身”为枢纽,“修身”必须“正心”“诚意”“致知”,而“致知在格物”,“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55]
子夏所谓“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正是深得孔子思想精髓。

《程颢程颐评传》
因此,“修身”既强调了个体修养的重要性,又实际上排除了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其最终落脚点是现实的家国天下,这正是孔子开创的儒学教育的鲜明特色,也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
因此,《大学》才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6]
由格致诚正而达致修身,由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孔子提倡的“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为学路径显然是一致的,因此,说《大学》是对孔子思想的理论建构完全能够成立。
虽然我们可以将《大学》的“八条目”与《论语》所载孔子思想进行更细致比较,但以上六点,已经足以证明,《大学》的教育思想源自孔子,或者说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建构,孔子教育弟子只是随事点拨,并没有这样系统地讲说,其理论建构应该归功于曾子。

《曾子辑校》
《大戴礼记》留下的《曾子》十篇以及出土文献中的曾子著作,证明了曾子既有此思想,也有此水平,后人让其配享孔庙是实至名归的。至于今人如何批判地继承这份教育理论遗产,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一时也难有统一意见,只有留待大家来讨论了。
注释:
[1]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荆楚文库》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2]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四《伊川先生语十》,第246页。
[3]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上《伊川先生语八上》,第218页。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章句·大学章句序》,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版,第1页。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章句·大学章句序》,第1—2页。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章句》首章按语,第4页。
[7] 参见刘光胜:《出土文献与曾子十篇比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8] 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9]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三《保傅第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5页。
[10] 其实,卢辩和孔广森之说都有根据。事实上,西周学校办学地点是有变化的,周初大学、小学都设在王宫中的明堂周围,后来明堂迁至西郊,大学也随之迁移,而小学仍在王宫中。阮元《明堂论》和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均有解说,可参看。
[1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十八《内则》,《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71页。书计,原作书记,据阮元校勘记改。
[12] 参见拙作《孔子对周代学校教育的守正和出新》,《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2期。
[1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十三《冠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342页。
[14] 参见拙作《关于孔子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暨南学报》2018年第2期。
[15]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曾子》十八篇,多于《大戴礼记》所载十篇。
[16] 孔子“四配”指其配享的四个弟子,即复圣颜渊、宗圣曾参、述圣孔伋(子思)、亚圣孟轲。
[17]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四《里仁》,《十三经注疏》本,第2471页。下引本书只注篇名,不注页码,以省篇幅。
[18]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五《曾子疾病第五十七》,第108页。
[19]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四《曾子立事第四十九》,第89页。
[20]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大学》,《十三经注疏》本,第1673页。
[2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大学》,《十三经注疏》本,第1673页。
[22] “亲”与“新”,古籍常常混用。例如,荆门郭店楚简《六德》有“民之父母新民易,使民相新难”,“义者君德也,非我血气之新,畜我如其子弟”,文中“新”均应读作“亲”。
[23]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第16页。
[24] 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书篇》,第1006页。
[25]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九《伊川先生语五》,第194页。
[2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章句》,第3页。
[27]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二先生语一》,第2页。
[28]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第22页。
[29] 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河南程氏粹言》卷二《人物篇》,第1060页。
[30]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第29页。
[3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大学》,《十三经注疏》本,第1673页。
[3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章句》,第7页。
[33]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巻四《朱子晩年定论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7页。
[34]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四《答罗整庵少宰书》,第249页。
[35]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四《大学古本序》,第328页。
[36]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三《答顾东桥书》,第204页。
[37]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三《答顾东桥书》,第208页。
[38]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一《传习录一》,第36—37页。
[39]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二《大学问》,第105页。
[40]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文章编卷四《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第1008页。
[41]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三《答欧阳崇一书》,第196页。
[42]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一《传习录一》,第28页。
[43]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一《传习录一》,第71页。
[44]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二《语录》,第119页。
[45]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一《传习录三》,第97页。
[46]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三《答顾东桥书》,第215页。
[47]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二《语录》,第140页。
[48]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一《传习录三》,第75页。
[49] 王阳明《答徐成之书》云:“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得而尽诬之!”(《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四,第265页)王阳明心学正来源于陆象山(九渊),其所揭示的朱、陆分歧正是理学与心学的分歧。
[50] 熊十力:《读经示要》第一讲《经为常道不可不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51] 参见拙作《孔子对周代学校教育的守正与出新》,《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2期。
[52]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一《传习录一》,第28页。
[53]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四《宪问》注引,《十三经注疏》本,第2512页。
[54]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第253页。
[55] 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卷三《答顾东桥书》,第213页、第216页。
[5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大学》,《十三经注疏》本,第1673页。
